【這是2018年5月何春蕤為所編寫的《援助交際在台灣》一書撰寫的序,主要的論點在於指出兒少法罪罰不成比例、過度預防/預期犯罪、甚至未犯先抓的種種特質,都凸顯了保護式立法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箝制和壓迫,以及對人際互動、為人處事、社會肌理的深遠影響】
這是一本遲到了10年的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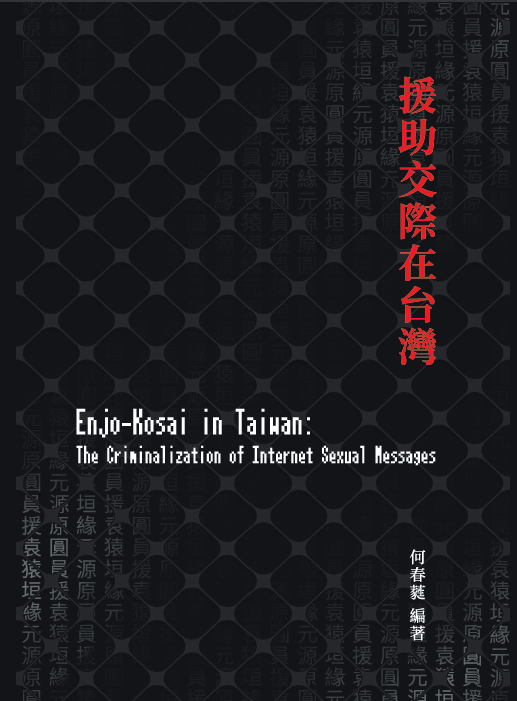
製作它,是為了記錄台灣地區針對網路性言論自由所進行的一場漫長爭戰。其中,1999到2008年之間有兩萬名網路使用者,只因為寂寞、無聊、好奇、嚐鮮、玩笑,或者有慾望、有狂想、有需求,在網路上鍵入了像是援助交際、身體交易、包養等等他們並不知道可能被視為觸法的字眼,結果被〈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簡稱兒少條例)29條拉入驚惶羞辱的司法程序,生活幾乎被摧毀,事後只能帶著污名所形成的心理黑洞,踽踽行走剩下的人生[1]。熱心網友、性權團體、人權團體在過程中不斷提出批判和抗議,迫使執法單位漸次縮減執法力度,並且還曾提出修法草案,可惜功敗垂成。今日,兒少條例雖經改頭換面,威力卻絲毫不減,繼續作為掃蕩色情性交易及邊緣性交際的推土機,也接合其他負面的性議題,為高舉性別平等和號稱保護兒少的婦女團體、宗教團體積累資源和權力[2],以鞏固台灣不分黨派最神聖不可挑戰的「行政/司法/意識形態」複合體──性別治理[3]。
這個漫長爭戰的核心〈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簡稱兒少條例或兒少法)設置於1995年[4],前身是1993年主要由基督教救援團體起草的「雛妓防治法」,在立法過程和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從救援雛妓轉變成對所有兒少進行保護式監控、對網路性言論進行嚴密規範的一個司法怪獸[5]。放在目前的性別治理格局裡來看,執法力度最大的兒少條例29條(1999年修訂),以及法理化趨勢最強的反性騷擾議題,可算是低調入世的基督教保守團體在1990年代末期台北廢娼遭遇頑強抵抗後轉向利用社會焦慮與情感來打造的反性交易新策略[6]。更重要的是,它也最早預示了其後20年性別立法/兒少立法將採用的基本論調與嚴罰精神,以及這種綿密的法理化在人際關係與社會氛圍上所形成的深遠惡果,特別是「虐」與「戾」的擴散瀰漫。仔細記錄兒少條例如何為性別治理的性管制鋪平道路,掃蕩異議,因此是本書的主要使命。
組成性別治理格局的各種性別/兒少立法,在積極保護弱者、遏止傷害剝削的崇高名義下,不但佔據「特別刑法」的位階[7],罪罰明顯不成比例,也大幅延伸法益,形成過度預防/預期犯罪、未犯先抓的偵辦傾向。
不教而殺謂之虐[8]
以兒少條例29條為例,1995年原條文為:「利用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或其他媒體刊登或播送廣告,引誘、媒介、暗示或以他法使人為性交易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黑體為本文所加)。條文的規範範圍很清楚:以重罰來防制各種性產業刊登招募廣告(包括俱樂部、伴遊、色情品生產、地下鋼管酒吧、色情卡拉OK、來電俱樂部等等)。但是後來媒體不斷報導青少女對身體和性越來越輕鬆以對,網路世界的興起也剛好帶來蓬勃的性交際機會,面對台灣社會快速變化中的性現實,保守基督教團體於是推動修法。
1999年,兒少29條被修訂為:「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散佈、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易之訊息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黑體為本文所加)。偵辦對象從此明確包含網路上的個人訊息,而且因為沒有設定適用年齡(「使兒少為性交易」),網路上所有的性協商訊息都被納入觸法範圍。新增加的「足以」更進一步延展了文字的詮釋空間[9]:虛擬世界裡高度個人化、多元化的訊息溝通,甚至成人在聊天室或討論板上的閒聊對話調情,都可能被有心人讀成「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性交易而送辦[10]。由於實際上有沒有性交易,對話雙方是不是未成年人,都不是成案的必要條件,這種積極解讀對網民形成極大的殺傷力。
「使人為性交易」是否包含網路上最常見的自主尋求有償的性交際,連司法人內部也有不同解讀和討論[11],對無數網民而言則形成「不教而殺」的實際後果。畢竟,絕大多數網民並不把網路上的調情、邀約、談條件,當成「性交易」──就一般人的認知而言,性交易是專業性工作者做的事情,網民就算想要以性換取金錢,也不會認為自己是性工作者。個人在網路上約炮,對方開出條件,或是自己因為手頭緊,要求對方提供報償,這些形式的「有償約會」(常被籠統稱為援交)只是隨著「陌生人之間的性」越來越普遍而出現的、理性的自利實踐而已。對網民而言,這與職業的性交易相去甚遠。更何況這些協商還是發生在兩個自願的人之間的文字溝通,既沒上床,也沒真正交易,難怪眾多網民在被捕時大惑不解自己到底做了什麼觸法的事。
(其實,同樣的認知差距也存在於後來有關侵害、騷擾、霸凌、糾纏等一連串性別立法中。畢竟,人際互動過程裡有著萬千個動態進行的言行舉止,互動雙方對於其中意義動機慾望後果的認知感受都可能不太一致。如果像現在,只由控訴者的個人認知感受作為定罪的判準,不問緣由地凌駕於行為人的解說之上,這種漫無邊界的執法都是不教而殺的「虐」。)
隨著被抓的案件不斷在媒體聳動曝光,個別網民求助的訊息浮上網路,什麼樣的訊息會被巡網的警察讀成指涉「性交易」也逐漸明朗(例如談及對價或使用特定字眼)。即便如此,觸法行為的疆界仍然可以隨時擴張。1999年前後,一夜情引發爭議和管制,很多網民改用剛剛進入台灣的「援助交際」作為一夜情的時髦代語,當然也有人以此招攬性交易,可是警方偵辦時完全不做區分,而是直接把援助交際等同於性交易送辦。另外,本來網路用語就慣於透過替換同音字來增添趣味,創造曖昧,迂迴表達,對不想直白邀約的網民而言,從「援」這個簡稱延伸出其他同音字的語句運用,都是委婉宣示或者裝文青的策略[12]。然而檢警在找尋案例業績時,卻枉顧具體情況,把這些都當成故意規避罪責,一股腦送辦再說,起訴率自然不高,連檢方都抱怨警方偵辦援交移送太過浮濫[13]。
在匿名的網路互動裡,沒有既存的人際關係和脈絡來確定或限縮意義,任何邀約的訊息都可能包藏著試驗、試探、曖昧、躊躇、敷衍,所有的調情和勾引都是透過建構虛設的、延展的想像來達成目的。動機與文字之間、文字與意圖之間、意圖與行為之間、行為與效果之間,充斥著蜿蜒曲折的迂迴岔道,隨機隨性進行著動態的進退攻守。然而網民們習慣的玩笑、戲謔、試探、邀約──這些在鍵入時完全未知是否會有任何閱讀或回應的張貼──在兒少29條和警方的監看下,文字意義都被輕易的具實化、統一化,構成了確定的觸法訊息。
這種意在淨化網路空間的文字獄,一方面製造了無數慘遭司法之災的網民,留下對法畏懼、對性猶疑的心靈;同時也召喚了另外一些狂熱嫉惡自以為義的道德主體,生成恃法而傲、恃正義而不仁的激情。
不仁誅心謂之戾
過去絕大多數民眾不覺得自己會觸法,認為法律要抓的應該是那些真正傷害人的壞人。但是近年為了促進台灣渴望的文明進步性平願景,進行了越來越多和性與性別相關的立法、修法或擴大執法(例如性騷擾防治法、兒少29條、刑法235條),大幅將本來不會被視為非法的行為(例如真實世界裡的調情玩笑追求,虛擬世界裡的約炮自詡求歡,以及色圖A片自拍的收集交流等等)納入偵辦移送的範圍,於是越來越多籠罩在性污名之下、滿心羞恥罪惡悔恨的小民網民在司法體系裡出現。性別/兒少立法也藉此擴張了管轄範圍,逐漸深入人民的日常生活與互動,對慾望和隱私形成積極的監控和壓抑,當然也造成意外觸法者產生心理疾病憂鬱症的現象。
兒少條例29條的綿密規範和雷厲執行,得力於20餘年來媒體搧情報導與(基督教出身之)兒保團體跟進呼籲所共同建構的兒少極端弱勢想像。極端弱勢的想像,正當化了代言和保護的必要,不但鞏固了兒保團體的任務和地位,更促發了許多因著各種不同原因高舉保護大旗的激情道德主體,在受害加害角色形象的著色之間建立起自己的有利位置。受害者越被呈現為純潔無辜弱勢,加害者就越顯得邪惡可恨,而自以為義的第三方道德主體則越有正當性可以激烈的討伐加害者,捍衛並代言神聖化的受害者,更可以戾氣四射的巡邏其他人的言論,任何異議都等同於新的加害,要立刻訴諸/呼籲法律加以懲治。為民除害的亢奮和權力感,毫無節制的從兒少議題擴散到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性糾纏,構成性別治理的激情面。
為弱勢討公道是社會正義的重要任務,但是一竿子打翻船的二元善惡思考,加上自命正義、驕而不仁的言論巡邏,卻形成危險的權力氛圍,不但在處理個案上簡化事實、漠視複雜,在更大範圍裡也傾向趕盡殺絕,容不下任何可能的「壞」因子。兒少29條在執法時就輕易的把目標從性交易訊息,擴大到所有性訊息,性騷擾議題也有類似的延展現象:現在,不但性騷擾的定義脫離了具體言行和具體傷害,而立足於範圍可以無限擴大、十分含混的個人感受之上,就連個人人格特質上的曠達不羈(例如不願侷限於一對一關係),人際互動和界限上的不拘禮俗(例如不在意男女長幼分際),都可以在強勢定罪的人言風傳中變成「騷擾成性」,被鬥臭鬥垮,甚至被投訴舉發,直接躍升為性騷擾的明確罪行。另外,個人的社交能力不足,追求手法笨拙,可欲品質不夠,或者根本錯估形勢,現在在政治正確的眼光之下,都被刻薄而惡意的讀成是道德上有嚴重問題,價值觀上徹底錯誤,意圖上全然可惡的徵兆,需要被徹底懲治。法律和風評的雙刃利劍,逐漸打造出風聲鶴唳、提心弔膽的氛圍。
不舒服、被冒犯、被敵視的感覺當然可能存在,但是從個人感受直接上綱到立法懲罰他人,從個人的厭惡不耐直接上線到定罪他人,反映了一種包裝在正義情感和語言裡的乖張驕氣。如果真是罪行嚴重,居心不良,根本就用不到以個人感受作為證據,但是控訴者或第三方道德主體卻總是從聖潔無暇的位置出發,以「誅心之論」指責他人的言行舉止造成了傷害的感受[14],也就是不問罪跡如何,僅以主觀判斷「其心可議」、「其心必異」,就此動機用心而加諸罪名,然後直接將所謂「加害者」圈入性污名和道德污名的千夫所指之下。在性別治理之下,這種強大的戾氣還可透過體制規範來強勢擴散,例如教育工作人員就被所謂性平專家敦促要提升「性別敏感度」,要在枝微末節中積極發掘任何不符性平規範的狀態,而且必須迅速通報,徹底調查,嚴厲懲治[15]。在不容鬆懈的警覺和戒備中,在道德高調與進步價值的敦促下,疏離與猜忌正在變成主導人際關係的重要情感[16]。
有法無天
台灣過去20年在性別/兒少立法上的傲人成果,其實是西方法理女性主義順著新自由主義資本國際秩序向全球各地擴散的成果[17]。這種源自基督教的「傳教/殖民傾向」,現在正透過聯合國公約、非政府組織、和西方專家學者的中介,把自命為普世價值的西方法律和政治經濟移植到其他地區和國家[18]。台灣島內則歡欣擁抱這些被視為進步先進的建制與價值,以自身在此特定國際政治經濟條件下形成的文明狀態,來確立台灣在全球新秩序中(特別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優勢地位。
不久以前,東海大學的趙剛教授在一次口頭報告中,以「有法無天的現代性」為主題發表論述。他指出,古人認為「人在天地之中,對高於自己、大於自己、自己與萬物所從出、德智美的『前提』,但又與人難解難分的那個『存在』有所敬畏,從而對自身的慾望言行有所節制」。然而,現代性的擴散卻促成了一個「以不敬為榮」的年代,像現在台灣社會的精神狀態反映的就是「天之退隱」,也因此失去了節制敬畏之心[19]。我的粗淺理解是,天與人之間的絕對高下差距有其深刻的社會意義:人對天有敬畏之心,才不會任意造次,而是戒慎自持,節制以待人,這是比法還深入人心的力量。因此,天是在法之上、深刻映照人情天理現實的原則;心中有天,就會在保障保護懲罰等判斷和措施上,抱持敬畏與悲憫之心,不會妄以為自己代表了歷史的盡頭。但是今日性別政治與兒少政治的「法理化」卻是以法代天,「有法」而「無天」,不但否認現實世界的複雜難辨,否認天理人情而只按著字面論法,對公平正義的理解和要求也變得簡單而冷酷,充滿自以為義的偏見傲慢。援助交際在兒少29條之下的境遇,以及上文分析的「不教而殺」「不仁誅心」,都是這種「有法無天」的法理化現象,其所滋養的「虐」與「戾」(還有「妄」與「傲」)也正在感染並腐蝕整體社會的凝聚力。
援助交際所引發的兒少29條苛政,標記了台灣社會性別治理馴化主體的軌跡開端。記錄這個歷史,揭露兒少保護的權力操作,也就是掀開了友善開明平權多元的遮羞布。如今,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已經在2010年被保守團體再度修法,改名為全面否定兒少自主行動力的〈兒少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也在2011年改名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更於2015年全面改版成為綿密規範日常生活和政策預算的法律。兒少保護在性別治理的羽翼下,已經成為台灣民主朗朗上口的傲人成果,正當化了一部又一部綿密設置的性別立法規範。在這樣的氛圍內,我們整理將近20年的兒少條例爭戰歷史,一方面為那兩萬餘只能在內心忍受腐蝕的兒少條例苦主留下見證,另方面也希望呈現我們集結力量與污名及惡法奮鬥的漫長過程,繼續激勵抵抗的動力。當然,「援助交際」及其騷動與污名並未成為歷史,仍然不斷展開。[21]
十餘年來,我在這個議題上收集了大量網路資料和對話記錄,因為篇幅實在太多,只能摘要列舉,無法全數呈現,因此,在這些資料和記錄的基礎上,我新撰寫了7萬餘字,分布在各章的首尾,完整分析沿著兒少議題所進行的論述爭戰及其歷史脈絡和意義,也記錄那些在過程中曾經留下的身影和聲音。在此特別感謝曾經協助收集資料的助理朱玉立、陳采瑛、林怡倩、陳思瑀、范姜松伶,也感謝當時曾經來函提供案例和新聞剪輯的無數朋友,是你們的努力使得兒少條例的效應更為清晰可見,為眾人的奮鬥添加了鼓勵和彈藥[22]。也感謝助理宋柏霖和沈慧婷在製作這本書上的大力協助。
註:
[1] 雖然現在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已經改名,惡名昭彰的29條也已修訂成為新條例的40條,但是對於兩萬多苦主而言,它將永遠是血痕斑斑的29條。本書也將圍繞著29條來記述這一系列的奮鬥。
[2] 2011年婦女救援基金會曾抨擊警方2008年放棄釣魚抓網路援交並取消獎勵金制度,使得違反兒少性交易案件銳減,網路援交猖獗。隨即以此為由,要求政府修法實施「網路實名制度」。參見〈網路援交氾濫 婦團催生網路實名制〉,《自由時報》2011年8月8日。
[3] 有關性別治理的歷史形成與操作模式,特別是它的法理化傾向和部份後果,請參見何春蕤,《性別治理》,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7年。
[4] 這個防制條例從一開始就被苦主們簡稱為〈兒少法〉。後來名為兒少的法律在數量上大幅增加,極易混淆。本書維持以〈兒少條例〉指稱〈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苦主如果在文字中使用「兒少法」,本書則保留歷史用法,不予調整。
[5] 對這個怪獸轉變過程的詳細分析,請參見何春蕤,〈從反對人口販賣到全面社會規訓:台灣兒少NGO的牧世大業〉,《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9期(2005年9月):1-42。
[6] 性騷擾近年快速法理化,應該和法理女性主義學者麥金儂的論述擴散全球有關。從1979年的《職場女性的性騷擾》開始,她就認為職場性騷擾逼迫女性以性換取生計,是把女性的工作轉化成(被迫)賣淫。沿著這個思路,性騷擾的罪行加深了嚴重性,立法防治懲治也成了女性主義理所當然的重要任務。Catharine A. MacKinnon, “How litigation laid the ground for accountability after #MeToo,” The Guardian, 2017年12月23日。
[7] 特別刑法,乃是針對特定人事時地而制定的刑事罰法,通常規範詳盡且嚴刑重罰。法學教授林山田曾批判台灣在普通刑法之外充斥特別刑法,作為統治人民的工具。參見〈民國成立至今之特別刑法〉,《國立台灣大學法學論叢》22.1(1992年12月):179-210。該文完成甚早,若是寫於性別/兒少立法大爆發的2000年代,對特別刑法的分析想必會有另外一番體認。
[8] 語出《論語》堯曰篇: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不教而殺謂之虐」就是四惡之首。本文下一節的標題「不仁誅心謂之戾」則是我個人自創的對句。
[9] 在兒少立法中另一個和「足以」一樣具有高度延展性的語詞就是「之虞」。兩者都對目標行為抱持極強的負面評價,因此傾向採用寬泛的定義和判斷來造成入罪。
[10] 例如,警方偽裝好奇,在網上詢問「真的有女生援嗎」「現在援的行情如何」,只要網民回應,就被視為意圖性交易而觸法;或者網民刊登交友訊息,註明「援交者勿來」,也被認定是講反話迂迴找人性交易。
[11] 參見本書262-264頁司法人針對這個問題的討論。
[12] 例如尋找有緣人、月圓人圓、原來是你、塵緣未了、圓夢計畫、應援等簽名檔或主旨中包含的同音字。
[13] 〈兒少性交易案 檢批移送浮濫〉,《中華日報》,2007年4月19日。
[14] 《左傳.宣公二年》晉趙盾不討伐弒君的亂臣賊子,史官將其記載為趙盾弒君,後世稱此為「誅心」之論。經過多年政黨政爭與政治脫口秀的薰陶,台灣已經很熟稔此種毫無根據就斷言他人心態動機的誅心之論。
[15] 2011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案明文禁止對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只要「疑似」發生相關案件,校內人員就必須在24小時之內向主管機關通報,否則首次處以3萬至15萬元罰鍰,再度發生則可解聘或免職。
[16] 現在有些人還鼓吹,在親密關係裡,權利/權益要成為衡量互動的唯一視角,(女方的)意願和感受更是不可不再三確認的事情。當體貼轉為警覺,熱情轉為猜忌,互動關係越來越合約化、法律化時,親密關係要以何種黏合劑來凝聚,將成為棘手的問題。
[17] 丁乃非在分析「性冷戰主義」時指出美國境內的進步思潮與境外的反共民主文化宣傳其實互為工具。參見丁乃非,〈女性主義的性論述〉,第八期「性社會學理論與實踐」研討班主題發言,2017年6月28日-7月5日,哈爾濱。
[18] James Q. Whitman, “Western Legal Imperialism: Thinking About the Deep Historical Roots,” NYU Legal History Forum, 2009, p. 310. http://www7.tau.ac.il/ojs/index.php/til/article/viewFile/727/686
[19] 趙剛,〈社會學的中國反思〉,「重新認識中國III」閉門討論會,2017年10月29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主辦。
[20] 甯應斌曾經分析台灣兒福法律的修訂過程與話語及其階級政治。參見甯應斌,〈台灣兒福法律與西方Child Abuse 話語〉,《連結性》,何春蕤編,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0。205-234頁。
[21] 這本書向國家圖書館申請出版品預行編目時提交的關鍵字「援助交際」未被採用,後來發現如此重大社會現象主題並沒有納入其主題詞表,不禁令人好奇原因。另外:中國大陸近日也有一則相關新聞評論:〈緊急!這個在西方臭名昭著的”援交”網站,竟落地中國了!〉,標題的「援交」是指西方 “Seeking Arrangement” 這類所謂徵求sugar daddy網站。由於這種徵求有錢男人為長短期伴侶的行為不能歸類於賣淫嫖娼,結果在此竟被稱呼為援助交際,顯然又和台灣與日本的使用意義有所不同,之後的建構發展猶待觀察。文章連結:https://mp.weixin.qq.com/s/cU1kwWMeVRf-oanCekeTSg
[22] 整稿時曾連絡第4章實錄的朋友們,然而過了10-15年之後,網路世界已改頭換面,大部分電郵地址不通,我只能去除個資,讓他們的案例和當時的心情能夠在這本書裡為惡法的惡果留下見證。再次感謝他們當時和我分享故事,並肩作戰。
轉載本文請保留網頁原始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