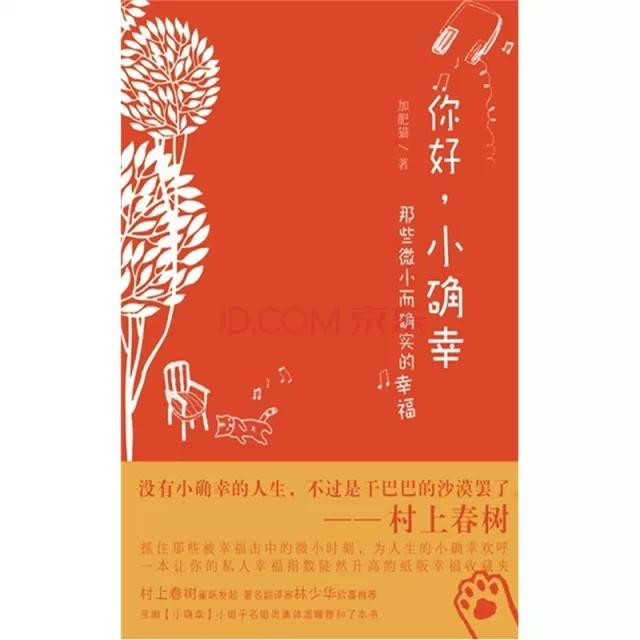「小確幸」:台灣太陽花一代的政治認同
趙剛 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小確幸」這個夾著濃濃東洋風的外來語,來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說的是生活中「微小但確切的幸福」。台灣的「時報出版社」分別在2002年和2007年出過的《藍格漢斯島的午後》以及《尋找漩渦貓的方法》這兩本插畫散文集,大概就是這個詞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的兩個載體。但這個詞來到台灣後,浸染流行,成為現在的流行語,大概也不過是這幾年的事。在台灣,人們對這個詞的掌握大概也無異於村上春樹的本意吧。我問了幾個朋友,有中年人也有青少年,他們的回答,用詞遣字雖有不同,但也不過是多灌下一些水,把原先的三個字泡開罷了。「小小的、確定的、幸福感嘍」──他們說,但這還是難以釋疑。
我會對這個潮名起疑念,想要把它弄清楚,是因為我對它有點直觀的不適,但究竟不適在哪兒,也一時說不清。是因為知識分子放不下的那種精英習氣,總是不甘心隨俗從眾嗎?有可能;我心裡頭會冒出這樣的一股質疑的原初慾望,和那個「批判習氣」可能擺脫不了干係。這樣一警惕,於是只要稍加反求諸己並推己及人,也就發現自己其實不需怎麼寬容就能這樣想:有誰不曾在生活或生命的匆忙、壓力、單調、失意或悲傷中,享受過片刻或哪怕是瞬間的安定、喜悅或滿足?站在一個大醫院的福利社門口,一個白髮老太太經過你,又轉過身來,很斯文很氣弱地請求你幫她把她手上的剛加過熱的保久乳的瓶蓋給旋開,於是你旋開了,交給她,跟她說:「您慢喝!」,然後你感到一種「小確幸」。或是,一陣帶著童年熟悉氣味的微風突然拂面而過,讓在異鄉的你驚訝感動駐足,直到那氣息與那回憶消失無蹤,於是你有了一段「小確幸」。或是,疲憊不堪的你,跳上一輛公共汽車,找到一個靠窗好座位,慢慢地一站一站地在雨季的夜暮的城市裡前進,像一個城市遊魂般,你靜靜地安全地端詳著人行道上或行或止的傘下的一張張或怔然或怡然或木然的面龐──於是,「小確幸」吧。或是,在一個冷冬鑽進一間暖暖的、嘈雜的、燈色昏黃的小咖啡館,吁吁氣、搓搓手,喝上一杯熱咖啡,拿一本平常不會看的雜誌,幾乎完全無意識地翻看著,啜飲著──「小確幸」。或是,在一個大夏天午後,走進一家便利店,吃上一個大冰淇淋,比個「V」手勢,來個自拍上傳……這些「小確幸」,如恆河沙數何止千萬,而就算這些不是你或我的「小確幸」,你或我也沒有一點資格質疑別人的「小確幸」。不是嗎?那麼,為何「小確幸」這個詞會讓我感到莫名的不安?以下算是我個人的「困而求之」吧。
「小確幸」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暗喻
的確,對待「小確幸」,不能以一種「批判知識分子」的傲慢對之直接否定。但是,是不是可以從而放到另一極端,拒絕將之知識對象化,僅僅看作古今中外無所不在的「小小的確定的幸福感」?我不認為如此。因為這裡畢竟牽涉到一個客觀的知識問題:人們為什麼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此處,台灣2013~2014),不約而同地使用了一個新名詞,來指認他們的「幸福感」?如此說來,「小確幸」應該被視為存在於一種特定歷史與社會條件下的能指,它並非「古已有之」。 「小確幸」固然是各個人所經歷的不同的幸福感,幾乎是人言人殊,但如果我們把「小確幸」僅限定於這個個人層次,那其實也同樣意味著拒絕知識對象化了。因此,有必要將「小確幸」視為一個「社會事件」或「思想事件」,在一個時代的/社會的層次上掌握其「思想意義」。是這個歷史性與社會性的提問意識,允許我從這個名詞的直觀意義中跳出,對其分疏化與脈絡化。
先對它作些概念分疏吧。如其名,它真的必須要「小」,它拒絕和任何大(哪怕是僅僅稍大於自我)的東西掛鉤。因此,「小確幸」和「宗教性」或「類宗教性」(天、道、上帝、良知……)無關。我們當代的「小確幸」與一個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家庭平日晚餐桌前的晚禱所散發出的那種「確幸」無關。同樣的,也和古代中國士大夫「無愧平生之志」的那種道德篤定感的「確幸」無關。其次,它經常遠離大自然。不論是「獨坐敬亭山」,或是「悠然見南山」,不管是「華爾騰湖」,或是「茵尼斯弗利島」之類的「確幸」,都與它無關。互聯網時代的人們既失去了孤獨的能力,也失去了在大自然中感到幸福的能力。再其次,它原則上無須以勞動或任何積極實踐為前提。我們的「小確幸」與東西方農民在稻堆麥垛疇間庭前悠然吸桿兒煙的那種(算是小的)「確幸」吧,也無關,那太折騰了!
但「小確幸」之所以高調唱「小」的最重要的原因,以我看來,是預設了對任何不輕飄的(從而不愉悅的)因素的話語排除;不但對他人的苦難憤懣要不聞,對自身的煩惱困擾也要不問,眼前的固然,歷史中的更是。說到底,「小確幸」之所以「小」,在於它否定或掩飾時空深度現實,只圖一個「當下」,只爭一個「我的」。古人說「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近人說「侵略者的炮火使整個華北擺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而這裡的「滿堂飲酒」與「平靜的書桌」指涉的既是一種對於「小確幸」的追求,也是追求者同時所深刻自覺的緊張感與不安感,因為自我的小小幸福和超越自我的、更大的、更連續的歷史與社會之間的連帶是無法斬斷的。相對而言,我們當今的「小確幸」恰恰是對這些「大」與「深」的切割與隔離,唯其「小」、唯其「扁」、唯其「平」,才能保證其「確」。「小確幸」敘事所預設的社會空間,可能就恰好符合撒切爾新自由主義的規定:「沒有社會,只有眾個人」。而「小確幸」敘事所預設的歷史時間,則是斷裂的、破碎的、當下的。「此時、此地、此我」是「小確幸」敘事的三個主要樑柱。「小確幸」是一種激進的「社會學想像力」的反命題。
因此,「小確幸」是一個「扁平現代性」的觀念產物,而同時,也反過來支撐這個扁平現代性。「小確幸」是建立在一種高度的世俗性、個體性與民粹性之上,並以商品物質性為其背景。它與任何「崇高」、「偉大」、「道德」、「理想」、「歷史」、「群性」或是「類存在」都無關。是的,就只是「無關」,它連嘲笑它們都懶得,何況批判?因此,「小確幸」所反映的首先是一種特定的主體狀態。原子化的主體頻繁地在「發現」、「發明」,以及「命名」它的某種其實很容易就流淌過的某種細小的碎片化的感覺,這當然和網絡時代的出現有關,人們表達、記錄、傳播自己的經驗感受的機會比以往不知多多少倍。好比,以前吃過一頓好早餐,也就吃過了,但今天我們可以將這個早餐類宗教儀式地對象化,拍照上傳,和別人分享我們的「小確幸」。「小確幸」常常是一種對「自我」的微笑自拍,是一種對「自我」所比的一種「V」手勢,是一種自我「治癒」。
「小確幸」的被指認與被需求,因此反而洩露了這個指認與需求主體的某種貧困與無奈。當我們把這樣的主體擺放到社會與歷史層次時,我們就更容易理解到「小確幸」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展現了深刻不確定性的年代中的一個精神現象。仔細檢視一些「小確幸」敘述,幾乎都可察覺到隱藏在它們背後的不被言說的當代家庭(或「親密關係」)、工作(或「勞動過程」)、政治(或「權力分配」),乃至道德審美領域中的某種深刻病理性。這個不被言說的後台以及拚命被言說的「小確幸」前台之間的反差,不妨讓我們如此指出:「小確幸」反映的是一種「苦中作樂」,不,其實是「苦中指樂」。這樣說好了,不必提什麼理想國,我們比較難以想像,假使在一個有很多「大」的或「體制化」的人生保障(「確幸」?)的社會裡(好比美式福特主義或日式家父長公司或西歐福利國家),或哪怕僅僅是資本主義上升期的社會裡,會出現「小確幸」這樣的一種大眾話語嗎?相對而言,當資本主義發展步向沉滯低迷,當實際工資減少、社會保障被縮遭砍,生產彈性化、超時加班、失業危機,墜落底層而無安全網時,「小確幸」就成為了一種深具無奈感的個人/大眾需求。它是這個資本主義世界中飽受不確定與無望感的青年人與中年人的挫折與痛苦的一種表達。它是一種失去理想、夢想、未來,或任何自我超越可能的「主體」的自衛/自慰性精神狀態。
於是,在商品時空中散放出來的「小確幸」,事實上透著一股資本主義發展沉滯期的霉味。難怪這個詞是從經濟長期停滯的日本冒出來傳過來的。你能想像在資本主義上升期中的社會裡,會發展出「小確幸」這樣的流行話語與流行感受嗎?那裡有的是資本家及其信徒的狂熱,以及幾乎具有同樣熱力但又有對抗的價值與希望的工人運動。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不好,但更壞的是不景氣時代的資本主義。「小確幸」恰恰就是建立在沒落或沉滯資本主義社會之上,但它不但不提供任何質疑或是反抗這個大環境的立足點,反而是一種軟綿綿的取消,像是一種沒有熱量的「代糖」,一種掩蓋無力感的「有效感」,一種「每一個人的宗教」,一種不斷自我強制提醒的「幸福」。因此「小確幸」反而倒過來支撐了這個深具問題的體制。在這個意義上,「小確幸」是一個甜絲絲的「政治學概念」,它是硬梆梆的支配性政治概念(例如,新自由主義、攫取性個人主義、多元主義、旁觀者政治,以及消費主義)的一種軟化劑與凝結劑,使這些不同的信念體系結合成一個巨大的霸權叢結。
作為一個隱藏的「政治學概念」,「小確幸」不只扮演上述角色,它還蘊含了高度敵對性。「小確幸」的「擁有」(「這是我的!」),讓擁有者不得不產生一種危機感──若是哪天連這個也都沒了,那該如何是好?這樣一種對可能威脅的恐懼,對可能敵人的焦慮鎖定,於是就成為了甜絲絲的「小確幸」的同體反面。今天美國的「全球反恐」是一個立即的例子。歷史上魏瑪共和的極右派(以及之後的納粹)也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他們所追求的即是一種當時德國版的「小確幸」,要在充滿危機的、不確定性的世界中,穩固地保有他們謂之「家園」(heimat)的「小確幸」。於是「猶太人」成為了他們的甜甜小確幸的苦苦大前提。「小確幸」於是也可能是一個妒恨或怨恨認同政治的隱喻。
這麼說來,「小確幸」遠遠不是日常的、常識的「小小的確定的幸福感」而已,而是資本主義發展沉滯期所產生的一種高度政治性的特定文化想像,是精神焦慮不安、物質前景黯淡的原子化個人企圖在當下的感受中以碎片化的經驗安慰碎片化的自我的一種小詭計──這可以說是「小確幸」的一般性考察。
但是,問題來了,有一個好朋友告訴我,其實這個詞在它的發源地日本,並不曾成為流行語。我問了一個日本通朋友,她說,對耶,我每天都看日文網絡新聞,沒看過這個詞呀。她幫我問了兩個人,一個是大陸人待了日本12年,一個是日本人,這兩位也都異口同聲確定地說「沒聽過這個詞」或「至今沒有在電視裡看到或聽周圍日本人用過」。我自己又直接問了一個日本朋友,他說他也沒聽過,他順便評論了一下,說這樣的一種名詞是村上春樹那一代的60年代日本左派後來走上虛無主義的不令人驚訝的普遍狀況。
於是,這個非常有趣的對照就自動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探索指引:要理解「小確幸」在台灣的流行,除了得在新自由主義現代性,或資本主義沉滯期的文化再現,這兩塊與日本社會的「交集」之中探索,還要在之外尋找。在之下的討論裡,我將借由「兩岸分斷」這個特定架構進行掌握,而這個架構至少包括了發展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兩岸特定歷史關係這幾個面向。我將要指出,「小確幸」是一個當代台灣版的認同政治的建構。
「小確幸」是「台派」的「文化無意識」
從1960年代到大約1980年代,台灣這個社會是不會出現「小確幸」之類的話語的。粗泛地說,那個時代、那個政權,與那個社會,進步或保守,好或不好,都浸潤在某種「理想主義」大話語中。我們可以回想50年代開始的全球冷戰對峙以及「反共大業」,60年代開始快速增溫的資本主義發展,70年代的「十大建設」,70年代的保釣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70~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80年代下半葉的解嚴與社會運動狂飆……可以說,這個時期是與「小確幸」這樣一種感覺結構在方方面面的對立。當然,這樣說,也意味著今日的「小確幸」也可能是之前訴諸的正反「理想主義」或「宏大敘事」的失落,或對其中的問題性的反動。那時,人們當然也在各個角落裡尋求他們的小小的確定的幸福感,但那和今日的「小確幸」在精神內涵、表徵方式,或是社會分析上,都是有巨大差異的:不大自戀、沒有霉味,也沒有拜物。借用許信良在《台灣社會力分析》那本書中所用的語言,那時的台灣人(當然指的是中小企業主)正「拿著007手提箱」昂然地滿世界跑。
從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中期的這十多年或可簡稱為「李扁時期」的年代裡,台灣人民也還是不會講「小確幸」或任何相近的話語,因為在經濟上,台灣的繁榮未退,大陸也還未「崛起」,而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這時又是台灣民族主義的一個前所未見的上升期,並拿著斜眼瞄著對岸,對自身民主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自滿與自信。2006年「扁政權」貪腐內瓤的破裂溢出,以及紅衫軍的反貪倒扁運動,首次讓這個自信與自滿的氣球嚴重漏氣。而同時期,台灣的經濟疲態已現、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燒煤自殺一時成風。雖然紅衫軍這個運動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真正清楚其意義與效應,但似乎無可否認的是它的話語裡並不包含「小確幸」或類似情愫。「禮義廉恥」這個被絕大多數參與者所認同的道德標竿,無言地旁證了這個運動所追求的某種「大」,以及與「傳統」或「中國性」的某種非對抗性姿態。
2008年,政黨二度輪替,「馬政權」上台。同時,「中國崛起」業已成為一個不可輕易否認的現實。在台灣,「中國崛起」被論述成只有一個邏輯可能性,那就是「中國威脅」(或「中國因素」或「你好大,我好怕」)。但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快速變成了威脅,當然也有源自於台灣社會內部的原因,那就是台灣社會多年來所積攢匯聚的底氣,由於經濟的持續低迷、政治反對運動的道德耗損、兩黨政治的無盡內鬥、社會內部的認同分裂……而消耗殆盡。在這些條件下,「小確幸」得到了滋養它的土壤,就算不曾從日本直接移植來這個字詞,本地應該也會造出一個適合表述它的字詞。「小確幸」是一個在兩岸分斷對立、台灣的發展主義走頹、消費文化持續高漲、政治無盡惡鬥與其導致的社會方向感的失落,以及親美友日的現代化文明主義等因素輻輳下的「文化無意識」。用大白話說,其主旨就是:「既然玩資本主義發展玩不過對岸,那咱就不玩了,我們只玩我們能玩的遊戲,即『綠色』路線、『文明』路線、『文化經濟』路線」。於是,「家園」、「文明」、「祥和」、「懷舊」、「禮貌」、「包容」、「人情味」等,在某一方面而言頗具「民國風」的「歲月靜好」的心理狀態,成為了台灣的一種外貌平和內在戾氣的主流文化想像。是在這種由於不知道如何面對「中國」與世界而產生的某種童稚的、賭氣的、撒嬌的,與幾乎是鎖國自閉的心理狀態下,台灣有了2014年的「反服貿」與「反核四」群眾運動的出現。
「反服貿」與「反核四」這兩個運動後頭的核心「文化無意識」就是「小確幸」,這是廣義台獨運動所必須建構的主體自尊感的第三波;第一波是「台灣錢淹腳目」,第二波則是「台灣的民主政治」。在這第三波里,我們要以我們的「小確幸」來抵抗你們的大、你們的新、你們的發展、你們的繁榮、你們的核電全球化……我們要以我們九份三峽的舊館斜陽來映襯你深圳上海的樹小牆新,以我們的「舒國治」(台灣的「小吃教主」)來訕笑你的「大魚大肉」,以我們的「捷運文化」來對照你的「人在途」,以我們的「人」──這道「最美麗的風景」──來睥睨你的暴發戶與煤老闆。當基本教義老台獨派仍然浸淫在他們的「黃昏的故鄉」的悲情中,青年學運的「台派」已經以「小確幸」的文化無意識為節點團結起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中頗具文化資本但又憂慮日趨邊緣化的文化界、出版界,與中小企業主,並對廣大青年學生發出危機召喚,訴諸青年的樸素社會意識,進行動員。
走出暗喻:對太陽花精英之外的青年學生的一個知識呼籲
因此,「小確幸」遠遠不只是一個軟綿綿的生活態度,而是一個強悍的政治建構。反服貿/反核四是「小確幸」的大型群眾運動,「小確幸」是反服貿/反核四的文化無意識。從表面上看,這兩者之間有一明顯斷裂或矛盾,「小確幸」具有濃厚的「私人」的大眾追求,為什麼會與以「公民」為名的大型群眾運動有關呢?但深入一層看,斷裂或矛盾其實並不存在,因為「公民」其實是一個隱喻。在我之前的另一篇分析太陽花的文章中,我就曾指出:「在太陽花運動所揭示的現實中,『公民』,既非傳統自由主義下的程序性概念,也非市民社會論或公共領域論下的規範性概念,而是一個動員與排除的隱喻。『公民』因此是反中運動的動員與排斥話語的核心構造,具有文明主義、族類主義以及二元對立的階序觀」(見拙著《風雨台灣:反思太陽花運動》)。於是「公民」隱喻和「小確幸」隱喻,在太陽花運動精英的無(半)意識操作下,有了完美的結合。如前所論,「小確幸」預設了一個高度問題化的社會情境,而太陽花運動精英則恰恰是越過了對那個「情境」進行理論與經驗的分析,反而用非分析、非概念、非理論的方式,直接訴諸恐懼與嫌惡的暗喻,把海峽對岸的「中國」(以及島內的「中國代理者」,即「馬政權」)直接定位為那個「情況」的唯一罪源,從而,能接受這個解釋(或口令)的才是「公民」。這是「太陽花」與「小確幸」能夠連接的這一端,而另一端則是在「小確幸」這個暗喻本身。如前所論,「小確幸」敘事之所以是一個「政治學概念」,首先就在於它是架構在西方的「扁平現代性」(或「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社會觀、歷史觀之上,在無意識層次上已經高度「西方化」,從而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內建於這個世界觀的某種「文明衝突論」的對立性。其次,它和一種妒恨的認同政治深刻地結合起來,把「小確幸」的擁有者視為弱小的善良者,時時刻刻面對著邪惡大野狼的威脅。
因此「小確幸」最反動的地方,是它的「隱喻性」的知識後果。「小確幸」借由「小小的確定的幸福感」這樣的無害的乃至外型甜美的外殼,防止社會苦難向經驗、理論,與社會探索開放。拒絕經驗、歷史與理論介入的後果,就是只有大量依賴隱喻與情緒,這於是形成了台灣當代主流社運與知識界的基本狀況。這個狀況何以致之?如何破解?也許是今日台灣最重要的一個知識政治問題。
受到台灣主流社會科學訓練的「台派」太陽花精英,真地超越了他們的「獨派」前輩嗎?老獨派的台灣人主體想像所賴以成立的那種「亞細亞的孤兒」、「在帝國夾縫中」的悲情形象,固然遭遇到主體空洞的問題──除了悲情之外幾乎一無所有。但相較於老獨派,「台派」的台灣人主體形象可能更有問題,而且一點也不曾超越老獨派的限制。他們面對的包括發展遲滯、低度就業、低度就業滿意度、貧富差距拉大、自我實現的困難,以及理想性的蒸發……這些重要問題的方式,並非試圖對這些問題進行超越的思想工作,而是正手將這些問題全部歸罪於「賣台集團」,反手卻將這些問題美學化甚至自戀化。就此而言,「小確幸」展現了「台派」與台灣現階段資本主義既得利益的共謀,透過想像中的「小而美」遮掩問題的實質。但是,再明顯不過的是,如果台灣不面對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不面對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只求「超前地」、「後現代地」、「願望地」、「美學化地」解決台灣的「發展問題」,那麼其實就也只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而已,而之所以仍是「政治」,則是因為任何牽涉到青年就業、貧富差距、合理房價、自我實現的「合理髮展戰略機遇」,都將因「小確幸」的無意識而被強迫放棄;對中國大陸的敵對,會因傲慢的「小確幸」而重新武裝;對美日的地緣政治依賴,也會因自卑的「小確幸」而持續。在一個根本意義上,正因為「小確幸」從來不是問題的提出,所以從來也談不上問題的解決,而只是問題傷疤的濃妝豔抹,是一種典型意義下的「意識形態操作」。
由「小確幸」作為無意識所推導出來的政治路線的高峰,就是今年三四月份的太陽花運動及其反核四接力。但是,物極必反,5月21日發生在台北捷運的不幸的隨機連環殺人事件,以及7月31日發生在高雄的不幸的氣爆事件,以及更近期的不幸的餿水油事件,都以暴力、災難或是惡臭,直接刺向或噴向這個「小確幸」自我感覺;用俚俗的網絡語言說:「小確幸」被打臉了!在某個意義上,這是暴力對「小確幸」隱喻的揭穿。但從台北捷運、高雄到餿水油的一連串災難事件,雖然造成了對「小確幸」客觀意義上的打臉,但是否會引領出主觀意義上的反省呢?我頗悲觀,不無可能的是,這些災難或許反而讓我們更加珍惜我們的「小確幸」呢!而就算有所「反省」,其實也不過只是「歸罪」而已。餿水油事件爆發迄今,台灣知識界的主流「反省」聲音也似乎只有:「這個政府到底怎麼了!」,而這似乎只能說明思想與知識的缺席。
坦白說,資本主義很麻煩,民族國家及其意識形態也很麻煩,兩岸關係更是一點也不簡單。而我們要有真正積極面對這些「麻煩」的態度,這些麻煩才會變成改變的契機,而這一切都需要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把問題情緒化、美學化、隱喻化,反而是偽裝成革命的反動,是一種「前政治」。這個反動的「小確幸」政治與文化無意識,如果不被確實地對象化、知識化,則可能會是那大千世界無處不在的而不一定需要被定名的小確幸(即,小小的確定的幸福感)的真正絕境的到來。真正的幸福或許應該是生活在幸福之中,而非碧落黃泉地窮於指認幸福吧。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善之為善,斯不善矣!」。而我們或許可以改寫為:「台灣皆知幸之為幸,斯不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