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閱讀內容:Discipline & Punish 「Torture」
上星期我們說明瞭Foucault對「論述」的看法,接下來這學期我們將處理他對「身體」和「性」的看法。到底他對論述有何種創見?──論述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會有不同的操作方式,傅柯以18、19世紀論述領域中的變化為例說明「作者」作為一個現代的社會位置有了很不一樣的功能,而且在科學和人文論述中扮演不同的角色,19世紀後更(因為學術專業化而)產生論述大師,不斷再生產新的論述;社會結構則同時建立起更多的外在內在限制,以侷限論述的影響力。換句話說,作者功能一方面限制論述,同時也產生論述,是個動態的位置。正因為這些權力結構的變遷,傅柯才建議以event的角度來看待論述,以捕捉論述的現代操作狀態,研究文學時應該把它當成論述來研究,以顯示其形成力場。【他和別的左派不同的是,左翼會強調社會有哪些因素造成這些轉變,或者說這些轉變如何反映了社會結構;而F則不假設這種反映,而只指出這些操作】
<規訓與懲罰>和上次的讀物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它運用在「身體」上,顯示身體如何銘刻了知識/權力,公權力的調查監控以及罪犯的認罪都在此刻透過刑求而銘刻在身體上。在歷史時刻中,公眾的殘暴刑罰消失眼前,這並不是司法的人道主義進展,而是新的知識權力技術的浮現,而這些知識權力技術則生產出現代人的「靈魂」來。在新的脈絡中,判刑(要啟動所有的知識權力結構)比刑罰(只是不可見的監禁或處死)來的重要。sentence(prescription for a possible normalization)包含了對正常的假設、因果的分析、評估可能的轉變、預期offender』s未來。現在,權力可及於人生,並且因為其抽像性,還可延伸擴展到別人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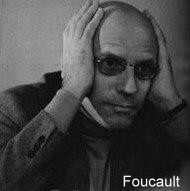 身體的權力技術──
身體的權力技術──
權力原本體現在刑罰上,但是在18、19世紀之交有了轉變:權力與刑罰開始保持距離,權力脫離這種明顯的、物質的暴力以及它可能引發的情緒,而有了另外一個抽像的、free-floating的存在:「its effectiveness is seen as resulting from its inevitability, not from its visible intensity; it is the certainty of being punished and not the horrifying spectacle of public punishment that must discourage crime」(9)──公開的行刑示眾,倚賴的是恐怖的感受,充其量只能觸及身體的表面,留下標記,但是權力的操作同時卻也把行刑者放到了和罪犯相同的位置上,分享了其不義和殘忍,也可能使得罪犯成為英雄或引發憐憫。同時,這樣的行刑折磨的是肉體,是感同身受的經驗,這樣的效應比較難以掌握。反倒是新的、不牽涉身體和痛苦、但是必然會降臨的權力刑罰過程有著更寬廣更深入的掌控力。
法的抽像化、知識的權力化──(13)「It is intended to apply the law not so much to a real body capable of feeling pain as to a juridical subject, the possessor, among other rights, of the right to exist. It had to have the abstraction of the law itself.」──法不再是身體上的標記,而是施展在主體之上的抽像權力,可以籠罩生命的全部,而不只是肉體。Penalty的目標不再是身體(生物個體)而是主體(鑲嵌建體系中,為體系之產品和承擔者)。參考16-18頁有關法所針對的對象的改變:法針對的不單是那個違法的行為,同時還包含了對這個主體的認知和掌握,因而創造出一系列的知識對象和抽取知識的專家,創造出新的知識權力網絡,衍生許多掌握司法決定權的小權威,形成一個龐大的體系。法和刑罰針對的不再是身體,而是「現代靈魂」(包括心靈、思想、意志、傾向,16),因而發展出一系列的評估、診斷、正常化的判斷,形成新的科學司法連結scientifico-juridical complex;現代靈魂是物質的存在,是對應於某種權力技術的,誕生自刑罰、管理、限制中。」The soul is the prison of the body」(30)指的是那些被教育家、精神學家、心理學家挖掘創造的知識是在刑罰、監控、限制的技術中誕生的(29)。現代靈魂因此是監禁身體的監獄。【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時代流行的courtroom drama並不是在顯示justice shall be done,而是顯示/証成知識是正義的基礎,知識的抽取因而得到justification】
傅柯的歷史社會觀點:看來是趨向leniency的法律改革事實上是配合不同的經濟現實所需而改變了對身體的掌握(25)。奴隸經濟的刑罰制度會創造國家奴隸以提供免費勞動力,封建經濟制度之下,身體是唯一財產因此體罰很多,商品經濟則需要自由的勞動力,刑罰因而降低了強迫勞動。
傅柯用了一連串的名詞來捕捉那個在歷史節點上浮現的新東西(25-27):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dy:身體糾葛於政治經濟的現實中,它如何被建構來服務政治目的,如何配搭當下的經濟氛圍對身體的觀點,這些都構成了身體的政治經濟學。身體的來去使用都有一定的規律,not only a productive body, but also a subjected body。
Political technology of the body:身體就是政治的力場,權力可以投注在身體上、標記它、訓練它、組織它、折磨它、強迫它行使某些功能。對身體的知識和操控形成了身體政治技術學。
Micro-physics of power:這些技術往往是diffused,分散的、片段的、使用著不同的工具、多種形式、並不集中於國家或機構。因此只能用微觀物理學才能捕捉其運作。
接下來傅柯就再進一步說,power不是property而是strategy,它的影響所及是氣質、操作、戰略、技術、功能。Power is situated in a network of relations, constantly in tension, in activity, rather than a privilege that one might possess; a perpetual battle; power is exercised rather than possessed.(26)從這個角度來理解論述權力就容易了,關注的是動態、張力、特殊歷史樣態。權力關係有著許多衝突的風險、不穩的焦點、有時還會顛倒,不能靠著抓住建制或體制就能擁有,而必須在本地化的結構中持續操作。權力和知識共生:權力使得主體得以成為知識研究的對象,知識則創造權力可以施展於其上的主體。傅柯認為我們應拋棄「暴力-意識形態」的模式來理解權力,轉而用body politic來看知識權力如何用各種物質成份和技術來攻擊、串連、溝通、投注身體,宰制它們,把它們弄成知識的對象,權力的效應(28)。
但是in case大家太過簡化torture的含意,太單向理解其中的權力佈局,傅柯在第二章中把torture放在整個司法體系中來顯示那個時代的司法體系的權力技術是如何操作的,而torture又如何配合了整體的需要。Investigation, confession, sovereign power都有其細緻的、或矛盾或匯集的關連。
Torture:當下的肉體殘害將身體當成物體,權力只及於身體表面,但是這也不是非理性的無法無天,而是個technique,是善用physical-penal knowledge,精細掌控身體的痛苦,看來過分,卻是必需的ceremonial of justice,有其特殊的economy of power(35)。在這個時代,所有的證據判決證詞都在掌權者手中,the truth of the crime由他生產,投注在被告身上,secret, written的調查結果真理是掌權者獨有的權力。然而相應而言,這些程式也使得公開宣告的confession成為一個被高舉的證據,因為它超越其他證據的真實性,而且因為主體自己接受了責任願意認罪,也就是接受了調查的真實性,這個負責的說話主體因此加入了生產真理的角色,有其影響力。這麼一來,torture就不再是單方面的權力施展,而是權力的抗衡,magistrate固然掌握了大部分的牌,但是也必須小心的使用行刑,以免犯人的意志透過其認罪宣告真理的時刻奪去這張王牌(40)。另外,公開的酷刑本意是要顯示犯罪行為的真理,要在罪犯身上展現權力的無限高超地位,要對比王權和罪犯之間的天壤之別,要罪犯在此時刻承認罪過,self-incriminating。但是諷刺的是,公開行刑也把人民放在目擊者的位置上,讓他們有權參與這個過程。原本是要人民的報復心理來實現統治者的報復,但是常常也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應,人民反而在這個時刻拒斥刑罰的權力,特別當受刑人是暴動領袖時。受刑人既然已經一無所失,反而可以肆無忌憚的咒罵,說出現實。行刑時刻也是狂歡時刻,是人民得以貼近罪犯、王權的時刻;18世紀末,下層人民愈來愈不接受刑罰,常常在行刑時發動solidarity,反叛而救走罪犯。
Tortured body:punishment by power(權力)以及extortion of truth(知識)的匯集點。
傅柯在這一章裡描述的是一個歷史的轉變,也就是體現君王統治權力的明顯殘暴公開行刑方式在歷史中的消失。對於不服的人民,君王通常以殘暴行刑來對待,殺雞儆猴,彰顯王權至高無上,可是Last words of the condemned man以及disturbances around the scaffold卻也都是當時的亂源,因為它們都被民眾視為人之將死,其言必真,而王權的殘暴反而在行刑中被這些悲壯表信凸顯出來,也因此被其徹底挑戰。行刑時的Confession是統治者需要的,因為罪犯一定要臣服於權力,但是它卻可能被膨脹成為亂世英雄的史詩,特別是當時流行的broadsheet正以小報的方式不斷重述、擴大罪犯對抗王權的英雄事蹟。行刑,其實上演了權力看似龐大卻很不可預期的脆弱。
後來公開行刑逐漸消失,傅柯認為這並不是說人們比較開明瞭,人道了,相反的,其實是權力的一種轉化。公開行刑無法適當的紓解它原本想要儀式化的權力關係,反而相應出現了無數罪犯奇情故事來探究權力與反抗之間的衝突,人們對非法行為有了無法抑制的興趣,想要看這樣的微妙對峙到底怎樣。有趣的是,當broadsheet被消滅的同時,卻也出現了另外一種罪犯文學,其中的罪犯在故事中被尊崇,他們似乎都有智慧巧思來和權力對抗,這種新的文類主角既然被塑造成heroic proportion,這種罪犯文學也就越來越創造了適合另一(中產)階級讀者的罪犯,那些微小的、不值得、非英雄的罪犯故事則被留給了報紙。這裡的split便是階級的分野,原來屬於所有普通民眾的罪犯故事、行刑時的悲壯英雄都被剝奪了呈現(broadsheet),高級的罪犯文學成了那些中規中矩的中產階級所壟斷的靜態閱讀。只有偉大的罪犯才值得書寫,小民原本對犯罪所感到的驕傲以及可能的反骨正逐漸隨著行刑的消失、罪犯小說的興起而被排擠到只能在通俗的報紙版面上以最渺小卑賤的方式存在。
公開行刑的消失,統治的溫和轉變,和罪犯文學的中產化(罪犯的知識智慧化),都是同一個過程,也都標記了權力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