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週:Beck的Normal Chaos of Love (I)
何春蕤教學筆記
 本週閱讀內容:Beck and Beck-Gernsheim, Normal Chaos 11-44; 140-167 本週閱讀內容:Beck and Beck-Gernsheim, Normal Chaos 11-44; 140-167
<風險社會>136頁談到現代化社會要求vigorous model of action in everyday life,要學會self-management,要會承擔責任和後果,要會算計得失。這個發展對個人的最大衝擊:人被要求更加為自己的人生負責,在心態上不再倚賴舊的價值和組織,不得不為自己負責。【這個觀念也是很現代的,很存在主義的,但是沙特會著重其中的孤獨和悲壯情懷,Beck等則比較著重這整情境所形塑的人格和前景。】風險也使得個人不得不學會評估、盤算,因而影響到過去親密關係中的混沌模糊。而這個趨勢被Beck運用到對婚姻愛情的分析上,寫成了這本書。【對風險社會的分析當然並不一定要這樣運用,換了一個人,推出來的結論就會不一樣。例如,所提出的建議不一定要像Beck以福利國家為基礎,也不一定要以保護婚姻家庭為主,而可以更進一步談原子化主體所可能結合成的關係形式,不過,好在Beck還是很常提到多元家庭。】
Beck談愛情的時候為什麼總是和婚姻放在一起來談?──我覺得他並不是像保守派那樣說愛情必定要在婚姻的框架內,或者愛情一定導致婚姻;相反的,另一個可能的讀法是:他是在說,在這個年頭,愛情所座落的脈絡,和婚姻一樣,都在薄冰之上,都只是人際親密關係而已,都一樣受到類似的社會力的衝擊,因此在它們之間再去做什麼區分也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課前作業討論
- 請閱讀http://www.ettoday.com.tw/article/350-390565.htm。中國大陸婚姻的變遷趨勢就Beck之理論來說可做何種comment?──相同處:都市、現代化造成婚姻變遷。相異處:並不是由勞動市場作為衝擊力量的來源,而還可能牽涉到政策、改變了的社會情境等等。
- Normal Chaos第13頁說love and inequality are after all as mutually exclusive as fire and water。請historicize──騎士時代的courtly love基礎就是在階層差距上,domination本身也可能形成愛情的某種基礎,父母對子女的愛更常常就是建立在不平等上。Beck此處對愛情的預設因此似乎是指某一個歷史時段對愛情的理想。
- 為什麼第五章題為」Eve』s Late Apple」?──男人的解放是意外,是隨著女人的解放運動而來的。但是女人的認知和獨立當然比起男人是遲來的blessing,不過apple是智慧的開端,也是誘惑,是痛苦:因為認識到自身存在的侷限。女人獨立自主當然也必然是個mixed blessing,因為不能再靠男人經濟支援;而女人性解放也沒有了家庭婚姻的壟斷/保護,因為,外面的女人多得很,家庭婚姻都不再鐵定了。
- 請詮釋161頁那一節起始的語氣以comment on Beck』s立場──152-154談男人解放時也有同樣的outburst of emotion。顯示他實在是個蠻浪漫的人,重幻想和理想,對生活中細瑣的變動有很敏感的感受。
- 44頁結尾的問題在163頁似乎有了某種解答,請comment on這個解答──什麼樣的社會能容許我們邁向自由?Beck的答案是改良的福利國家,並透過國家的力量來沖淡市場對個人的要求,以便我們的social needs得以被認識和滿足,因而在動盪中仍能維繫家庭。這個答案是statist的,而且假設了家庭成員願意在一起,願意同進同出,當然這也就假設了愛情中人一定是黏在一起的。【沒有有距離的感情嗎?人們分開就不可能愛了嗎?】
完整徹底的commmercialization of labor必定使家庭解體成為個人。但是這樣的自由也是mixed blessings,一方面有自由有空間,但是另方面卻也失去支援系統,進入另一種標準化。核心家庭作為基礎,建立了工業化社會,但是現代工業化的趨勢解放了所有的勞動力,也因此已經愈來愈衝擊自身的基礎(即家庭及其內部的權力和關係結構),讓女人及青少年都進入勞動市場。福利國家的措施更穿透了性別藩籬,及於所有的人,使得家庭成員因著工作而發展出不一樣的生活形態和期望,因而鬆動原來緊密統一的家庭。──另外,國家政策的不當也使得個別家庭必須負擔更大壓力(例如教育環境不理想,父母得自己教,環境污染使主婦的清潔、烹飪、防病工作增加等等)。
個人之死?
(38-44)在這一章中,Beck大致上重複了在《風險社會》中的說法,但是在最後一節加了一些新的東西,是有關個人之死與主體性的。批判學派如Adorno等人認為這個大眾社會中的「個人」已死(不但是因為個人在經濟上的依賴性,更因為標準化和組織化的趨勢)。Beck則認為這個說法錯誤,個人在福利社會中其實已經獲得了新的經濟地位,可以自立,做自身傳記的書寫者,把社會的決定性因素當作可以透過創意的方法來操作的環境變數,但是同時也自願的選擇適應社會的標準,以便達成例行化(routinization)以及隨之而來的更高效率──畢竟,我們面對了高度風險、隨時危機、無從預估的困難情境。個人生活和整體環境的密切糾葛、消費者意識的強化、自信的增高,都使得新的主體性高漲,人不得不面對未知、承認懷疑、接受變化,而且要以愉快的世故來面對。這些當然導致self-reflexivity的形成。Beck稱這為「新的啟蒙」,不是菁英的,而是普遍的、日常的自我意識,容或有點膚淺和不定,採用的或許還是過時的舊語言,然而這個自戀的世紀卻也使得人們自我檢視,尋求探索新的可能,慢慢培養出對自由的感覺。「為自己負責」的新倫理出現,不是簡單的自我中心,而是將個人和社會做一個新的融合,對劇變、成長都有新的期待。
面對資本主義商品及勞動社會,有些人的分析會強調這個結構是多麼的強大,個人的位置和力量因此都受到她已經被決定的社會位置侷限,抗爭也因此必定要在既有的社會參數基礎(如階級、性別等)上,以單一同質的腳步來進行。Beck對「個人之死」這個說法的分析卻顯示,資本主義商品及勞動社會的發展固然有其重大衝擊力,然而其影響卻(1)在主體身上形成反思的能力和動力;(2)促使主體為自身的人生做決定,構築故事;(3)因人生的選擇和變動,而凸顯主體之間過去隱而未現的差異及其後果。這些衝動或許是粗糙的,或許有時糾葛在最傳統的語言和形體中,但是無論如何,這些都有助於積極形成主體agency的能量。
除了勞動工作之外,個人生命中愈來愈多的抉擇機會也提升了個人意識。選擇多,就鼓勵個體進行評估,鼓勵個體多知道其中差別,多練習weigh其中的利弊優劣,以做出明智選擇。──Beck在資本主義商品市場邏輯中看到的,不是人們多麼的被矇蔽雙眼,沖昏了頭,而是進步的可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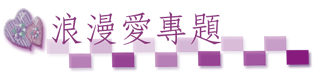
 本週閱讀內容:Beck and Beck-Gernsheim, Normal Chaos 11-44; 140-167
本週閱讀內容:Beck and Beck-Gernsheim, Normal Chaos 11-44; 14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