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阅读内容:Discipline & Punish “Torture”
上星期我们说明了Foucault对“论述”的看法,接下来这学期我们将处理他对“身体”和“性”的看法。到底他对论述有何种创见?──论述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会有不同的操作方式,傅柯以18、19世纪论述领域中的变化为例说明“作者”作为一个现代的社会位置有了很不一样的功能,而且在科学和人文论述中扮演不同的角色,19世纪后更(因为学术专业化而)产生论述大师,不断再生产新的论述;社会结构则同时建立起更多的外在内在限制,以局限论述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作者功能一方面限制论述,同时也产生论述,是个动态的位置。正因为这些权力结构的变迁,傅柯才建议以event的角度来看待论述,以捕捉论述的现代操作状态,研究文学时应该把它当成论述来研究,以显示其形成力场。【他和别的左派不同的是,左翼会强调社会有哪些因素造成这些转变,或者说这些转变如何反映了社会结构;而F则不假设这种反映,而只指出这些操作】
<规训与惩罚>和上次的读物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它运用在“身体”上,显示身体如何铭刻了知识/权力,公权力的调查监控以及罪犯的认罪都在此刻透过刑求而铭刻在身体上。在历史时刻中,公众的残暴刑罚消失眼前,这并不是司法的人道主义进展,而是新的知识权力技术的浮现,而这些知识权力技术则生产出现代人的“灵魂”来。在新的脉络中,判刑(要启动所有的知识权力结构)比刑罚(只是不可见的监禁或处死)来的重要。sentence(prescription for a possible normalization)包含了对正常的假设、因果的分析、评估可能的转变、预期offender’s未来。现在,权力可及于人生,并且因为其抽象性,还可延伸扩展到别人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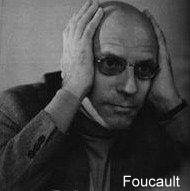 身体的权力技术──
身体的权力技术──
权力原本体现在刑罚上,但是在18、19世纪之交有了转变:权力与刑罚开始保持距离,权力脱离这种明显的、物质的暴力以及它可能引发的情绪,而有了另外一个抽象的、free-floating的存在:“its effectiveness is seen as resulting from its inevitability, not from its visible intensity; it is the certainty of being punished and not the horrifying spectacle of public punishment that must discourage crime”(9)──公开的行刑示众,倚赖的是恐怖的感受,充其量只能触及身体的表面,留下标记,但是权力的操作同时却也把行刑者放到了和罪犯相同的位置上,分享了其不义和残忍,也可能使得罪犯成为英雄或引发怜悯。同时,这样的行刑折磨的是肉体,是感同身受的经验,这样的效应比较难以掌握。反倒是新的、不牵涉身体和痛苦、但是必然会降临的权力刑罚过程有着更宽广更深入的掌控力。
法的抽象化、知识的权力化──(13)“It is intended to apply the law not so much to a real body capable of feeling pain as to a juridical subject, the possessor, among other rights, of the right to exist. It had to have the abstraction of the law itself.”──法不再是身体上的标记,而是施展在主体之上的抽象权力,可以笼罩生命的全部,而不只是肉体。Penalty的目标不再是身体(生物个体)而是主体(镶嵌建体系中,为体系之产品和承担者)。参考16-18页有关法所针对的对象的改变:法针对的不单是那个违法的行为,同时还包含了对这个主体的认知和掌握,因而创造出一系列的知识对象和抽取知识的专家,创造出新的知识权力网络,衍生许多掌握司法决定权的小权威,形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法和刑罚针对的不再是身体,而是“现代灵魂”(包括心灵、思想、意志、倾向,16),因而发展出一系列的评估、诊断、正常化的判断,形成新的科学司法连结scientifico-juridical complex;现代灵魂是物质的存在,是对应于某种权力技术的,诞生自刑罚、管理、限制中。”The soul is the prison of the body”(30)指的是那些被教育家、精神学家、心理学家挖掘创造的知识是在刑罚、监控、限制的技术中诞生的(29)。现代灵魂因此是监禁身体的监狱。【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时代流行的courtroom drama并不是在显示justice shall be done,而是显示/证成知识是正义的基础,知识的抽取因而得到justification】
傅柯的历史社会观点:看来是趋向leniency的法律改革事实上是配合不同的经济现实所需而改变了对身体的掌握(25)。奴隶经济的刑罚制度会创造国家奴隶以提供免费劳动力,封建经济制度之下,身体是唯一财产因此体罚很多,商品经济则需要自由的劳动力,刑罚因而降低了强迫劳动。
傅柯用了一连串的名词来捕捉那个在历史节点上浮现的新东西(25-27):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dy:身体纠葛于政治经济的现实中,它如何被建构来服务政治目的,如何配搭当下的经济氛围对身体的观点,这些都构成了身体的政治经济学。身体的来去使用都有一定的规律,not only a productive body, but also a subjected body。
Political technology of the body:身体就是政治的力场,权力可以投注在身体上、标记它、训练它、组织它、折磨它、强迫它行使某些功能。对身体的知识和操控形成了身体政治技术学。
Micro-physics of power:这些技术往往是diffused,分散的、片段的、使用着不同的工具、多种形式、并不集中于国家或机构。因此只能用微观物理学才能捕捉其运作。
接下来傅柯就再进一步说,power不是property而是strategy,它的影响所及是气质、操作、战略、技术、功能。Power is situated in a network of relations, constantly in tension, in activity, rather than a privilege that one might possess; a perpetual battle; power is exercised rather than possessed.(26)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论述权力就容易了,关注的是动态、张力、特殊历史样态。权力关系有着许多冲突的风险、不稳的焦点、有时还会颠倒,不能靠着抓住建制或体制就能拥有,而必须在本地化的结构中持续操作。权力和知识共生:权力使得主体得以成为知识研究的对象,知识则创造权力可以施展于其上的主体。傅柯认为我们应抛弃“暴力-意识形态”的模式来理解权力,转而用body politic来看知识权力如何用各种物质成份和技术来攻击、串连、沟通、投注身体,宰制它们,把它们弄成知识的对象,权力的效应(28)。
但是in case大家太过简化torture的含意,太单向理解其中的权力布局,傅柯在第二章中把torture放在整个司法体系中来显示那个时代的司法体系的权力技术是如何操作的,而torture又如何配合了整体的需要。Investigation, confession, sovereign power都有其细致的、或矛盾或汇集的关连。
Torture:当下的肉体残害将身体当成物体,权力只及于身体表面,但是这也不是非理性的无法无天,而是个technique,是善用physical-penal knowledge,精细掌控身体的痛苦,看来过分,却是必需的ceremonial of justice,有其特殊的economy of power(35)。在这个时代,所有的证据判决证词都在掌权者手中,the truth of the crime由他生产,投注在被告身上,secret, written的调查结果真理是掌权者独有的权力。然而相应而言,这些程序也使得公开宣告的confession成为一个被高举的证据,因为它超越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而且因为主体自己接受了责任愿意认罪,也就是接受了调查的真实性,这个负责的说话主体因此加入了生产真理的角色,有其影响力。这么一来,torture就不再是单方面的权力施展,而是权力的抗衡,magistrate固然掌握了大部分的牌,但是也必须小心的使用行刑,以免犯人的意志透过其认罪宣告真理的时刻夺去这张王牌(40)。另外,公开的酷刑本意是要显示犯罪行为的真理,要在罪犯身上展现权力的无限高超地位,要对比王权和罪犯之间的天壤之别,要罪犯在此时刻承认罪过,self-incriminating。但是讽刺的是,公开行刑也把人民放在目击者的位置上,让他们有权参与这个过程。原本是要人民的报复心理来实现统治者的报复,但是常常也可能产生相反的效应,人民反而在这个时刻拒斥刑罚的权力,特别当受刑人是暴动领袖时。受刑人既然已经一无所失,反而可以肆无忌惮的咒骂,说出现实。行刑时刻也是狂欢时刻,是人民得以贴近罪犯、王权的时刻;18世纪末,下层人民愈来愈不接受刑罚,常常在行刑时发动solidarity,反叛而救走罪犯。
Tortured body:punishment by power(权力)以及extortion of truth(知识)的汇集点。
傅柯在这一章里描述的是一个历史的转变,也就是体现君王统治权力的明显残暴公开行刑方式在历史中的消失。对于不服的人民,君王通常以残暴行刑来对待,杀鸡儆猴,彰显王权至高无上,可是Last words of the condemned man以及disturbances around the scaffold却也都是当时的乱源,因为它们都被民众视为人之将死,其言必真,而王权的残暴反而在行刑中被这些悲壮表信凸显出来,也因此被其彻底挑战。行刑时的Confession是统治者需要的,因为罪犯一定要臣服于权力,但是它却可能被膨胀成为乱世英雄的史诗,特别是当时流行的broadsheet正以小报的方式不断重述、扩大罪犯对抗王权的英雄事迹。行刑,其实上演了权力看似庞大却很不可预期的脆弱。
后来公开行刑逐渐消失,傅柯认为这并不是说人们比较开明了,人道了,相反的,其实是权力的一种转化。公开行刑无法适当的纾解它原本想要仪式化的权力关系,反而相应出现了无数罪犯奇情故事来探究权力与反抗之间的冲突,人们对非法行为有了无法抑制的兴趣,想要看这样的微妙对峙到底怎样。有趣的是,当broadsheet被消灭的同时,却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罪犯文学,其中的罪犯在故事中被尊崇,他们似乎都有智慧巧思来和权力对抗,这种新的文类主角既然被塑造成heroic proportion,这种罪犯文学也就越来越创造了适合另一(中产)阶级读者的罪犯,那些微小的、不值得、非英雄的罪犯故事则被留给了报纸。这里的split便是阶级的分野,原来属于所有普通民众的罪犯故事、行刑时的悲壮英雄都被剥夺了呈现(broadsheet),高级的罪犯文学成了那些中规中矩的中产阶级所垄断的静态阅读。只有伟大的罪犯才值得书写,小民原本对犯罪所感到的骄傲以及可能的反骨正逐渐随着行刑的消失、罪犯小说的兴起而被排挤到只能在通俗的报纸版面上以最渺小卑贱的方式存在。
公开行刑的消失,统治的温和转变,和罪犯文学的中产化(罪犯的知识智慧化),都是同一个过程,也都标记了权力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