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周:Beck的Normal Chaos of Love (I)
何春蕤教学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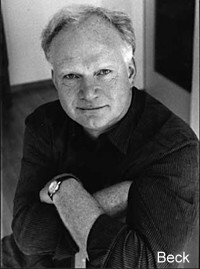 本周阅读内容:Beck and Beck-Gernsheim, Normal Chaos 11-44; 140-167 本周阅读内容:Beck and Beck-Gernsheim, Normal Chaos 11-44; 140-167
<风险社会>136页谈到现代化社会要求vigorous model of action in everyday life,要学会self-management,要会承担责任和后果,要会算计得失。这个发展对个人的最大冲击:人被要求更加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心态上不再倚赖旧的价值和组织,不得不为自己负责。【这个观念也是很现代的,很存在主义的,但是沙特会着重其中的孤独和悲壮情怀,Beck等则比较着重这整情境所形塑的人格和前景。】风险也使得个人不得不学会评估、盘算,因而影响到过去亲密关系中的混沌模糊。而这个趋势被Beck运用到对婚姻爱情的分析上,写成了这本书。【对风险社会的分析当然并不一定要这样运用,换了一个人,推出来的结论就会不一样。例如,所提出的建议不一定要像Beck以福利国家为基础,也不一定要以保护婚姻家庭为主,而可以更进一步谈原子化主体所可能结合成的关系形式,不过,好在Beck还是很常提到多元家庭。】
Beck谈爱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和婚姻放在一起来谈?──我觉得他并不是像保守派那样说爱情必定要在婚姻的框架内,或者爱情一定导致婚姻;相反的,另一个可能的读法是:他是在说,在这个年头,爱情所座落的脉络,和婚姻一样,都在薄冰之上,都只是人际亲密关系而已,都一样受到类似的社会力的冲击,因此在它们之间再去做什么区分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课前作业讨论
- 请阅读http://www.ettoday.com.tw/article/350-390565.htm。中国大陆婚姻的变迁趋势就Beck之理论来说可做何种comment?──相同处:都市、现代化造成婚姻变迁。相异处:并不是由劳动市场作为冲击力量的来源,而还可能牵涉到政策、改变了的社会情境等等。
- Normal Chaos第13页说love and inequality are after all as mutually exclusive as fire and water。请historicize──骑士时代的courtly love基础就是在阶层差距上,domination本身也可能形成爱情的某种基础,父母对子女的爱更常常就是建立在不平等上。Beck此处对爱情的预设因此似乎是指某一个历史时段对爱情的理想。
- 为什么第五章题为”Eve’s Late Apple”?──男人的解放是意外,是随着女人的解放运动而来的。但是女人的认知和独立当然比起男人是迟来的blessing,不过apple是智慧的开端,也是诱惑,是痛苦:因为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局限。女人独立自主当然也必然是个mixed blessing,因为不能再靠男人经济支援;而女人性解放也没有了家庭婚姻的垄断/保护,因为,外面的女人多得很,家庭婚姻都不再铁定了。
- 请诠释161页那一节起始的语气以comment on Beck’s立场──152-154谈男人解放时也有同样的outburst of emotion。显示他实在是个蛮浪漫的人,重幻想和理想,对生活中细琐的变动有很敏感的感受。
- 44页结尾的问题在163页似乎有了某种解答,请comment on这个解答──什么样的社会能容许我们迈向自由?Beck的答案是改良的福利国家,并透过国家的力量来冲淡市场对个人的要求,以便我们的social needs得以被认识和满足,因而在动荡中仍能维系家庭。这个答案是statist的,而且假设了家庭成员愿意在一起,愿意同进同出,当然这也就假设了爱情中人一定是黏在一起的。【没有有距离的感情吗?人们分开就不可能爱了吗?】
完整彻底的commmercialization of labor必定使家庭解体成为个人。但是这样的自由也是mixed blessings,一方面有自由有空间,但是另方面却也失去支援系统,进入另一种标准化。核心家庭作为基础,建立了工业化社会,但是现代工业化的趋势解放了所有的劳动力,也因此已经愈来愈冲击自身的基础(即家庭及其内部的权力和关系结构),让女人及青少年都进入劳动市场。福利国家的措施更穿透了性别藩篱,及于所有的人,使得家庭成员因着工作而发展出不一样的生活形态和期望,因而松动原来紧密统一的家庭。──另外,国家政策的不当也使得个别家庭必须负担更大压力(例如教育环境不理想,父母得自己教,环境污染使主妇的清洁、烹饪、防病工作增加等等)。
个人之死?
(38-44)在这一章中,Beck大致上重复了在《风险社会》中的说法,但是在最后一节加了一些新的东西,是有关个人之死与主体性的。批判学派如Adorno等人认为这个大众社会中的“个人”已死(不但是因为个人在经济上的依赖性,更因为标准化和组织化的趋势)。Beck则认为这个说法错误,个人在福利社会中其实已经获得了新的经济地位,可以自立,做自身传记的书写者,把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当作可以透过创意的方法来操作的环境变数,但是同时也自愿的选择适应社会的标准,以便达成例行化(routinization)以及随之而来的更高效率──毕竟,我们面对了高度风险、随时危机、无从预估的困难情境。个人生活和整体环境的密切纠葛、消费者意识的强化、自信的增高,都使得新的主体性高涨,人不得不面对未知、承认怀疑、接受变化,而且要以愉快的世故来面对。这些当然导致self-reflexivity的形成。Beck称这为“新的启蒙”,不是菁英的,而是普遍的、日常的自我意识,容或有点肤浅和不定,采用的或许还是过时的旧语言,然而这个自恋的世纪却也使得人们自我检视,寻求探索新的可能,慢慢培养出对自由的感觉。“为自己负责”的新伦理出现,不是简单的自我中心,而是将个人和社会做一个新的融合,对剧变、成长都有新的期待。
面对资本主义商品及劳动社会,有些人的分析会强调这个结构是多么的强大,个人的位置和力量因此都受到她已经被决定的社会位置局限,抗争也因此必定要在既有的社会参数基础(如阶级、性别等)上,以单一同质的脚步来进行。Beck对“个人之死”这个说法的分析却显示,资本主义商品及劳动社会的发展固然有其重大冲击力,然而其影响却(1)在主体身上形成反思的能力和动力;(2)促使主体为自身的人生做决定,构筑故事;(3)因人生的选择和变动,而凸显主体之间过去隐而未现的差异及其后果。这些冲动或许是粗糙的,或许有时纠葛在最传统的语言和形体中,但是无论如何,这些都有助于积极形成主体agency的能量。
除了劳动工作之外,个人生命中愈来愈多的抉择机会也提升了个人意识。选择多,就鼓励个体进行评估,鼓励个体多知道其中差别,多练习weigh其中的利弊优劣,以做出明智选择。──Beck在资本主义商品市场逻辑中看到的,不是人们多么的被蒙蔽双眼,冲昏了头,而是进步的可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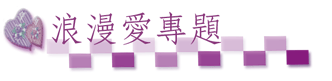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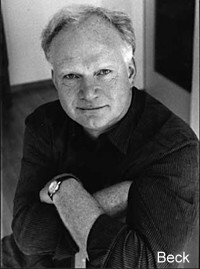 本周阅读内容:Beck and Beck-Gernsheim, Normal Chaos 11-44; 140-167
本周阅读内容:Beck and Beck-Gernsheim, Normal Chaos 11-44; 14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