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前言
 婚纱照,或用更广义的说法是结婚典礼上所捕捉的镜头,在西方的摄影理论架构下,通常被放置在家庭摄影的脉络下来理解。以家庭摄影簿(Family Photography Album)的型式呈现家庭集体生活的历史,纪录家族成员一生中的大事,例如:结婚、家庭聚会、或是家庭中有了新成员、新生儿的诞生等等。这一些被选入家庭摄影簿的照片无庸置疑是整个家族兴衰的纪实。而这样的影像经验在台湾,尤其是近十年的台湾所发展出来的婚纱摄影工业,可以说是独步全球的。台湾的婚纱市场以及相关产业,从上游的成衣业(礼服的制作)、教育界(专业美容造型师,摄影从业人员的养成),到中游的拍照、冲洗、电脑美工处理,乃至到下游的印刷(喜帖、贺卡、谢卡)、餐饮业(餐厅、喜饼)、旅游业(蜜月旅行、礼车租赁)、和一般服务业(花环花束、美发造型),其牵连程度之广,涵盖经济层面之深,可谓另一种全民运动。每家婚纱厂商提出的整套服务包办,从婚礼繁复的仪式到所需耗费的物质,每一步都是以专业的角度来包装一场浪漫的婚礼。每位即将步入教堂的准新人,无不以拍摄婚纱照来突显其幸福浪漫如王子公主般的美丽神话。当众亲友参加婚礼时,观赏新人婚纱照所呈现出来的幸福讯息,仿佛就是见证此情不渝的誓约。其中的影像呈现,其实已经迥异于一般,或说是台湾早期的结婚照,因为在技术上,当代的婚纱照结合了新的摄影科技,甚至以数位化的方式,化腐朽为神奇的将许多原本其貌不扬的新人们,化身为一对对如萤光幕前的旷世巨星。这其中已经暗示了许多现代人对身体的认知及觉醒,而在文化层面上,整体的婚纱工业所生产出来的影像讯息,早已隐含许多的文化意涵,更直接透露出现代人对婚姻、家庭乃至性别扮演,已经有了全新的诠释。
婚纱照,或用更广义的说法是结婚典礼上所捕捉的镜头,在西方的摄影理论架构下,通常被放置在家庭摄影的脉络下来理解。以家庭摄影簿(Family Photography Album)的型式呈现家庭集体生活的历史,纪录家族成员一生中的大事,例如:结婚、家庭聚会、或是家庭中有了新成员、新生儿的诞生等等。这一些被选入家庭摄影簿的照片无庸置疑是整个家族兴衰的纪实。而这样的影像经验在台湾,尤其是近十年的台湾所发展出来的婚纱摄影工业,可以说是独步全球的。台湾的婚纱市场以及相关产业,从上游的成衣业(礼服的制作)、教育界(专业美容造型师,摄影从业人员的养成),到中游的拍照、冲洗、电脑美工处理,乃至到下游的印刷(喜帖、贺卡、谢卡)、餐饮业(餐厅、喜饼)、旅游业(蜜月旅行、礼车租赁)、和一般服务业(花环花束、美发造型),其牵连程度之广,涵盖经济层面之深,可谓另一种全民运动。每家婚纱厂商提出的整套服务包办,从婚礼繁复的仪式到所需耗费的物质,每一步都是以专业的角度来包装一场浪漫的婚礼。每位即将步入教堂的准新人,无不以拍摄婚纱照来突显其幸福浪漫如王子公主般的美丽神话。当众亲友参加婚礼时,观赏新人婚纱照所呈现出来的幸福讯息,仿佛就是见证此情不渝的誓约。其中的影像呈现,其实已经迥异于一般,或说是台湾早期的结婚照,因为在技术上,当代的婚纱照结合了新的摄影科技,甚至以数位化的方式,化腐朽为神奇的将许多原本其貌不扬的新人们,化身为一对对如萤光幕前的旷世巨星。这其中已经暗示了许多现代人对身体的认知及觉醒,而在文化层面上,整体的婚纱工业所生产出来的影像讯息,早已隐含许多的文化意涵,更直接透露出现代人对婚姻、家庭乃至性别扮演,已经有了全新的诠释。
前言
随着婚纱这样一个深具俗民文化色彩的摄影工业的发展,台湾近年来不断的有学者用各种不同的面向来理解分析婚纱摄影,其观点多半以社会学、文化研究、消费行为研究以及市场分析的角度出发。然而,在众多对婚纱摄影所进行的分析中,以摄影的技术或是美学形式来分析婚纱摄影的文章,竟然是九牛一毛。众多焦点所关注的对象多是摄影这个事件本身,也就是拍摄婚纱的这项行为;而摄影的产品,也就是照片本身及其影像意义,却鲜少有人愿意关注。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婚纱摄影这项摄影范畴有太深的庶民文化色彩,乃至学者们对其不愿以美学的形式来看待并讨论,最后终至将其屏除在美学的领域之外。抑或是台湾至1990年代尚无任何一所大学成立摄影系,婚纱摄影的专业人才多半是师徒相授,或是由职业学校商业设计相关科系的毕业生担任,所以在学院中缺乏发声,以致毫无立场。本文即将以镜头下的技术,或是美学的形式出发,以摄影本身的影像呈现为文本,来讨论婚纱摄影,进而推演这样的影像呈现所意指的文化意涵。
你要结婚吗?你要拍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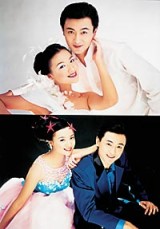 这样一句强而有力的广告台词,不知招唤了多少对佳偶,不惜重资拍摄婚纱,见证幸福的允诺。每对新婚佳偶似乎不能免俗的一定要拍上几组照片,见证属于这一生最美丽的时光,在台湾,几乎很难找到哪一对结婚新人结婚时不拍婚纱照,而婚纱业者也在积极促销的情况下,不断开拓市场,把拍婚纱照的对象来源的年龄层往下拉,锁定豆蔻年花的花样少男少女拍起写真。这种属于婚纱的副业,成本多半仰赖婚纱工业多年来累积下的成本,一本万利地用起135相机拍出一般的负片照片,减低成本,更迎合了年轻族群所能负担的经济能力。
这样一句强而有力的广告台词,不知招唤了多少对佳偶,不惜重资拍摄婚纱,见证幸福的允诺。每对新婚佳偶似乎不能免俗的一定要拍上几组照片,见证属于这一生最美丽的时光,在台湾,几乎很难找到哪一对结婚新人结婚时不拍婚纱照,而婚纱业者也在积极促销的情况下,不断开拓市场,把拍婚纱照的对象来源的年龄层往下拉,锁定豆蔻年花的花样少男少女拍起写真。这种属于婚纱的副业,成本多半仰赖婚纱工业多年来累积下的成本,一本万利地用起135相机拍出一般的负片照片,减低成本,更迎合了年轻族群所能负担的经济能力。
从拍写真到婚纱,反映出来的正是这整个市场庞大的消费能力,而在吞噬这个市场的竞争中,业者除了加强整体的服务,从拍照到结婚的各各面向一应俱全的包办之外,如何在拍出来的照片本身的品质与特色上作宣传,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当然,每对新人在挑选婚纱摄影公司的时候,也会希望摄影师们能为他们拍出与众不同、既出色又物廉价美的婚纱照。为了同时兼顾消费者期望与市场成本,婚纱业者早在多年的经营经验中创造出一套适应这样的市场法则的生存之道:每位执镜的摄影师,除了必须兼备专业的摄影技术之外,还必须懂得消费者心态,懂得为自己的照片宣传。在半哄半骗的情况下,新人们不断的追加原先的预算,一组组的婚纱照就这样被催生了出来。但是,真的有这么多的镜头值得加洗吗?摄影师如何绞尽脑汁地为每对新人们构思出专属于他们的镜头呢?
婚纱摄影的主题不外乎就是要新婚的主角及其背后的背景;在这两大主题的交相搭配之下,婚纱照也能用一套公式来理解:人物的变换多以礼服的搭配变换。新娘除了有一般标准的白纱之外,还有和服、晚礼服、凤冠霞披作选择,而背景的变化则就更多元,有室内景(壁纸)、室内人工布景(纱窗、家具、书房)、室外实景(公园、古厝、人行道),甚至还有电脑合成的背景提供e世代新人的选择。在这样的交叉搭配之下,也常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效(笑)果,例如;穿戴唐装及凤冠霞披的新人们,诗情画意地出现在欧式庭园造景的公园里,或是身着法式晚礼服的新娘唯美地(事实上是冒着生命危险地)站在铁道旁边。
姑且不论这样的影像呈现是否意味着某种荒诞不经──或是更积极的说法是某种另类美学风格的具体呈现──我们不禁要问:一般的市井小民有何种办法可以在短时间内转换在不同空间场景,身着数十套不同礼服,满足时下一般芸芸众生过着有如明星般、备受尊宠的享受呢?如今,婚纱摄影公司所拍摄成的影像以及所提供的服务,正好满足这样的心理需求。试想除了结婚,还有哪一种场合能让新娘在一天之内连换三四套正式礼服,无人投以异样表情,却能轻而易举的博得满堂喝采的时机呢?(郑维玮,1995)
再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也可以从中观察出在我们的文化中,显然对于公然地展示我们自身的身体会有多少的唐突跟不自然。只有在镜头前,只有在结婚时,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多方展示自己的身体,穿梭游走在不同的时空背景里头,才会被认可。自认双腿美肩过人者,可以恣意地在镜头前留下倩影,自认自己有无限的明星潜力者,也可大方的在镜头前搔首弄姿。即使只能在镜头前留下迥异于自己的镜头,即使只能在镜头下才能挑战自己天生的限制,这样一场如嘉年华般的摄影戏剧,正巧妙地在不同背景、在多变的礼服装扮中上演。
值得注意的是,卫道人士面对此种现象,惯用所谓的 “女性主义”批评口吻(也不知是哪个门派的女性主义),谴责婚纱摄影不外乎是现代人的虚荣心引起的浪费及对身体的过度迷恋及物化:
一场物欲横流的婚礼在婚纱摄影的演出下表露无疑,并不是说包装或雕塑有何不好,而是幻化起婚姻彩衣的手法,常常拒绝去承揽在婚后远离“王子与公主” 神话的家常事实…一名仍在传统包袱下,扮演婚后正常角色的女性,他可能开始了与婚礼中大异其趣的装扮;也就是说,她逐渐体现了老公所害怕,倦怠的黄脸婆模样…在婚纱摄影中将主角“高高的捧起” 后,随之而起的是新娘子的窘境将在传统的束缚中若隐若现,我们假使召见美丽的婚纱让一个女人昏炫不已时,唯一的期盼就是希望她们不要再被 “重重的摔下”!(自立晚报,1996,6月4日)
这样挟持客观包容的批评口吻,首先强调包装和雕塑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样的批评攻势还是开门见山的提出这一场物欲横流的败金糜烂;接着攻击这是虚浮的刻划王子和公主的神话,说这样的神话是不足以支持现代人在现代高度竞争的社会里,还能在传统家庭婚姻中立足,并同时可以幻想着王子公主的神话生活。这样的批评,假设了穿上婚纱的女性必然将自己投射成一位将过着幸福快乐日子的公主这个角色里,也预设这个角色会毫无抵抗力的自溺在这样的美丽神话中。这样的谬论其实是简化了认同与扮演的过程,如果我们将拍摄婚纱摄影的过程视为是一种表演,新娘并不会单纯的将自己扮演成公主,也不会在拍完婚纱,脱去礼服之后,还一昧地认为自己是那位“幸福的公主”。
在西方的表演理论中,以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的谢喜纳(1985)在观察过亚利桑那的传统鹿舞,提出他的见解,他认为带上鹿的面具的演员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正意识到他已经不会是“人类”,当然他也不会是那头“鹿”;相反的,演员现在正置身在介于人与鹿之间的模糊地带(somewhere in between)。这是一种复制行为(restored behavior),也就是说,演员在这样的表演行为中,并不会单纯的将自己二元化的投射为单纯的自己或是角色里。相反的,是有更多可能性正在其中展演。因为王子和公主的原型并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原版的再现,新郎新娘也就当然不会将自己完全投身到那样的假想当中,所以在表演中的新郎新娘其实将会把自身及其未来所要扮演的夫妻更紧密的结合,透过类似拍照、换装的过程,如仪式般地,当作进入家庭的准备。
无可否认的,这样的仪式是建立在浪漫爱的基础上。在分析浪漫爱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原有的性别分野依旧会被婚纱照的影像所呈现出来。例如,新郎必定是雄壮,英俊的表现;而新娘一定会娇羞,温柔的被呈现。为了用影像呈现出或更加强这样的假想认知,摄影师会用一些摄影技巧来处理这样的题材。以打光作例子,如果有一对新人,新郎的脸型较消瘦,而新娘的脸型则较丰腴,摄影师通常会在新郎的脸上打上侧光,如此一来,在视觉上新郎的脸颊会相较于没有受光的新娘的脸来得大,也才能平衡新郎新娘在性别上的差别。其他还有许多方法,例如在构图上,新郎通常会站在新娘的前方,用视觉上的透视法,突显出新郎的优越感,或是请新郎用站姿,新娘为坐姿来表现。在婚纱摄影的市场里,异性恋婚姻是其市场来源,所以在这样的市场里能衍生的影像并不难想像会用何种角度来诠释。
影像上除了彰显性别这个难以越界的藩篱之外,随着时代的改变,影像也越形丰富的表现现代的特色。传统的婚纱照通常都加柔胶或加丝网来表现浪漫的影像,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人喜爱挑选像黑白照,或是逆光的照片来彰显其冷峻的性格。高反差、背光、滤镜或是选择都会场所如捷运站、城市夜景为背景的照片都大受欢迎。尤其是电脑数位化处理的照片,更是可以将画面上的瑕疵,修理的整整齐齐,无怪乎越来越多的婚纱照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新人,越来越有明星般的架势,这样的情节其实影像化了“丑小鸭变天鹅”的经验,也凸显了婚纱摄影这样的庶民文化潜越天生美丑的可能性。
今生最美丽的新娘
婚纱业者在市场宣传上,通常打着将“新娘最美地一面拍出来”为口号,为了捕捉今生最年轻、最美丽的影像,自然有不少的消费者会利用拍婚纱的机会,好好的将自己的青春留下见证。这种------“一生只有一次”,“不趁青春时拍就错过了”的焦虑,在婚纱业者在不断的怂恿之下,一组一组的照片就会不断地被拍摄出来。这样捕捉青春的影像意义、凸显了影像在时间轴上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意义。而且透过大量的复制,广送诸亲友,婚纱影像显然在此有不同于一般照片的社会实践。这样大量复制的影像,另人不禁想和在30年代,班雅明(1935)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提出的批评及讨论一同作比较。在他的讨论中,摄影、电影之类新兴科技的艺术领域中,不少新的媒材改变了传统对艺术品的看法,对于用机械来大量复制的作品,班雅明提出他的看法:
即使是最完美的复制也总是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艺术作品的“此时此地”,—独一无二地现身于它所在之地,—就是这独一的存在,且为有这独一的存在,决定了它的整个历史。谈到历史,我们会想到艺术作品必须承受物质方面的衰退变化,也会想到其世世代代拥有者的传承经过。物质性的双退痕迹只有仰赖物理化学的分析才能显露出来,这种方式是不可能施用于复制品的; 要确知作品转手艺主的过程,则需要从作品创作完成之地为起点,追溯整个的传统。(Benjamin W. 1935; 许绮玲译1998)
近年来时兴以婚纱照作为结婚典礼上的谢卡,婚纱照透过大量的复制,在婚礼上与亲友分享结婚的喜悦。这样的复制如果在班雅明的眼中,作品的灵光早已消失,其独一无二的“此时此地”也势必荡然无存,甚至作品的“传统”也深受打击。但是相当有趣的,婚纱照在此却是悖其道而行。
婚纱照在大量复制的过程中,其实突显的是新郎新娘年轻时独一无二“此时此地”,这种“此生最美丽”的捕捉,趁着青春正好让即将进入婚姻的新人们,留下一生最美丽的注解。试想当新娘人老珠黄的变成黄脸婆的时候,谁还会有心情为自己拍下数量如此之多,价值不斐的照片?而婚纱摄影业者就是凭着消费者的这个需求与心态大发利市。在业者的广告文宣上,我们不难找出诸如“将你拍成最美丽的新娘”,“一生一次的美丽”之类的宣传手法,其所召唤出来的消费族群自然会是想利用结婚时,趁着年轻美丽时留下镜头的人们。而拍摄婚婚纱的新人们其实也心知肚明,拍摄婚婚纱彰显的是年轻时的美丽,并不会直指一生一世永恒的誓约,因为在现今高离婚率的社会中,永恒的婚姻誓约已经不可守,唯有年轻时的美丽值得捕捉与纪录。
约翰、达在分析19世纪的人像摄影时发现,当时的中产阶级在拥有属于自己的照片时,其影像意涵象征着自己个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地位。相同的,现代人用婚纱摄影不仅将自己的青春留下纪录,更彰显新人们以小家庭为单位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很少看到婚纱照是以家族为主题的),个人化地将婚姻关系用影像来表达。至此,婚纱照片已经从传统的家庭照相簿中独立出来,象征新一代的人们从传统的家庭结构中出走。
结语
婚纱照,一种影像消费(image-consumption)的庶民文化。与其用法兰克福学派如清教徒般道德观点来批判它,倒不如将它放在社会脉络中,用一种社会实践来理解它。因为这样的影像消费其实已经不是一种需求而已,而是一种欲求,一种展现庶民的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摄影型式。藉由拍摄转移在不同空间背景,不同服装造型中,游移于不同主体中,超越现有的社会身份,展现另一种行动主体,为台湾社会文化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参考书目
<女性主义焦点下的台湾:高高的捧起,重重的摔下!>,《自立晚报》,民国85年6月4日,11版。
李玉锳,民国88年,<实现你的明星梦—台湾婚纱照的消费文化分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6期,页174-186。
许绮玲,民国90年,<摄影创作、家庭、女性—角色的寻思>,《形象的建立,女性心灵之旅》──文学、艺术、影像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许绮玲译,Benjamin, Walter箸,民国87年,《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台湾摄影工作室。
郭力析,民国86年,《书写摄影—相片的文本与文化》,台北:远流出版事业。
郑正清,民国87年,<婚纱摄影背景情境之消费者喜好度调查>,《台中商专学报》第30期,页249-275。
---,民国88年,<台湾婚纱摄影之消费者生活型态集群研究>,《商业设计学报》第三期,页77-110。
Schechner, Richard, 1985. Between Theater And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Tagg, John, 1988.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Pres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