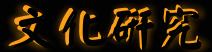|
1939年出生於英格蘭的傳播學界的大師級學者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遠道從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來到霪雨霏霏的6月臺北。在下榻的飯店一側,一盞柔和的夜燈,灑落在費斯克光潔的額頭上。
留著灰白的長須、目光深邃的費斯克,有著老祖父般沈穩持重的嗓音,有時甚至有點混濁。這位素有「庶民文化的樂觀者」稱號的費斯克,即便是說到會心處,也不過是淺淺地露齒微笑。在一個多小時的訪談中,費斯克仍不改其對庶民文化的關注,同時也點出橫梗在臺灣面前的一些問題。
60多歲的費斯克,數度在回答問題前先發出深長的歎息,令人不禁想到,是否他對庶民文化的樂觀堅持,部分是建立在對現實悲觀面的體認之上。以下是訪談紀要。
傳播理論的建立和批判
記者(以下簡稱「記」):就我所知,你原來唸的是文學,爲何後來會轉到文化研究?你爲何想要將文化研究的思考,引入傳播領域當中,你是否感到傳統的傳播理論有所不足?
費斯克(以下簡稱「費」):其實我沒有轉行,當我還在念大學時,並沒有任何媒體或文化研究的課程,以致於我希望能發展這些學門,所以我在英國建立了第一個大學部的傳播及文化研究課程。
的確,我認爲文化理論在很多方面都挑戰到了傳統的傳播理論。特別是,過去「線性傳播」(Lineal
Communication)或過程傳播所著重的「發送(sender)-訊息(message)-接受者(receiver)」的理論模型,被文化研究者完全摧毀。許多傳播理論的核心理想是讓傳播盡其可能地更好、更有效率,而更有效率正意味著更具宰製性格,這就是文化研究質疑的地方。文化研究可以觸動不同的社會、文化條件,而傳統的傳播理論則想要忽略社會、歷史的偶然性(contingency),以建立均一的模型,而文化研究卻非常強調在地的偶然性,這是他們之間衝突的原因。
記:你將傅柯、葛蘭西、羅蘭巴特等理論大量注入傳播理論當中,傳統理論者如何看待你這種「革命」?
費:事實上,我覺得這種融入(fit
in)的工作仍未盡完美。我認爲葛蘭西(Gramsci)的理論是大部分文化研究的真正核心,我不認爲我們可以跳過葛蘭西,而能夠瞭解文化研究所開展出來的道路。傅柯
(Michel Foucualt)的爭議性較大,但是我個人認爲傅柯對文化研究將會有很多啓發,我不認爲文化研究可以忽略如此極端重要的思想家,特別是關於監控自我的議題上。
庶民的自主性
記:在你的《瞭解庶民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一書中,你對「庶民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大衆文化」(mass culture)做了嚴格的區分,舉出「庶民」具有戰爭的場域(site)對抗宰製的能動側面,這和完全受到媒體霸權操弄的「大衆」的臣服性格,形成強烈的對比。是什麽理由,讓你能如此樂觀看待「庶民文化」?
費:細膩考察,很多例子都顯示所謂「庶民」有很強烈的抗鬥性格。當各種領域的權力都物換星移或遭到阻礙,庶民即便遭到壓迫,卻從未被真正的打倒與趕盡殺絕。我的樂觀性是建立在庶民的耐受力(endurance)上。事實上,許多從屬的(subordinate)群體能夠利用各種方式強化自己的認同及和他人差異感,建立自己的獨特性。
例如,年輕的世代非常主動地消費「大衆文化」(mass
culture),從中搞出反權威、反傳統等不同的東西。很多證據顯示,庶民依照自己的旨趣(interests)大量利用大衆傳播媒體,用一句傳播學名言來說就是:「重要的是不要看媒體對庶民做了什麽,而是要看庶民對媒體做了什麽!」(Not
what media do to the people,what people do to the media)
當然,許多傳播理論喜歡將媒體做爲「媒體本身」(media
itself)來研究,因爲這樣比較容易,而要耙梳「庶民對媒體做了什麽」則要困難得多了,所以這個面向常受到忽略及刻意漠視,但我覺得這卻極其危險。我的工作就是嘗試用庶民的眼睛來看媒體。
「大衆文化」讓「高級文化」更加鞏固
記:在這個E世代,許多人擔心過度強調媒體視聽(audio-video)等感官性質,會磨鈍、減損庶民欣賞所謂文字文化(literate
culture)的心智慧力,你認爲「大衆文化」是否會吞噬諸如文學等「高級文化」(high
brow culture)?
費:我不認爲新的大衆媒體足以摧毀古老文字所建立的文化,反而文化型式是不斷累積的,我不認爲大衆文化嚴重地挑戰這些高檔文化,在許多方面,高級文化的地位甚至更加「鞏固」(secure)。當我們的社會漸漸不再以外顯的階級來區分群我時,某些人--特別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爲了顯示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於是就運用不同的「文化品味」(culture
taste)來表徵其社會差異性。現在我們看到西洋古典音樂CD、歌劇、交響樂團等比以前更加興盛,這就表示:只要高等文化製造更強大的社會差異的功能不變,就有自視爲高人一等的人士,繼續趨之若鶩。
記:兩者之間難道沒有對話、互動影響的空間嗎?
費:當然有。許多自視文化品味甚高的人士會輕視大衆文化或庶民文化,但是私底下,他們似乎又很縱情於享受、消費大衆文化;同時,浸淫于大衆文化的人,也可能受現代藝術吸引,就像我的小孩著迷於那種「塗鴉」一樣,當然也有沈迷於「噪音」般的熱門音樂的人,可能會認爲古典音樂「愚蠢」、「沒有重點」。有人投入了很大的能耐去維持兩者的不同,也有人將他們「混」(mixed)得很完美,這也是庶民文化有趣的地方。
Hello Kitty的文化爭論
記:去年我們這裏曾興起一場針對凱蒂貓玩偶引發的爭議,當時不少父母和祖父母漏夜守在麥當勞門口,只是爲小朋友或自己買到心愛的Hello
Kitty布偶....
費:對不起,那是什麽……?(摸摸鬍子,費斯克露出十分困惑的表情)
記:一種由日本風行來臺的只有眼睛沒有嘴巴的小貓布偶,在美國相同的例子應該算是「口袋怪獸」(pocket
monster),它不也是吸幹美國許多父母口袋的怪獸嗎?(費斯克終於豁然開朗,點頭表示理解)當時,凱蒂貓橫掃都會的排隊購買儀式,讓部分人士聲稱這是一種文化多元之下,個人自由的表現;而另外卻有聲音嚴厲地批判了這種天真樂觀的看法,指陳其忽略背後資本主義的精細操作面,最後不少專家學者也加入這場討論,引發不小的文化論戰。你對資本主義當令下的庶民文化,仍毫無保留的給予好評嗎?
費:你能告訴我這個例子真是太好了。這種文化事件基本上是一種社會論戰(social
debate),表示社會某些成員關心:「我們要讓我們的文化往哪個方向發展?」如果只有一種聲音、只有單方面佔優勢,那就成了一種集體洗腦(brain
washing)的社會過程。
如果你嘗試去理解一般人急於購買凱蒂貓或口袋怪獸的慾望,贊成者和反對聲浪都産生自同一種社會文化,這種差異衍生的爭論才是問題的核心。在爭論的發展下,想要買這些商品的消費者可能會逐漸地意識到另一方不買的人的想法,反之亦然。因此,只要我們持續爭論這個議題,情況將會有所不同。
我們應更樂於看到社會成員因不同的喜愛、慾望而爭論不休,這總要比不要麥當勞、不要凱蒂貓的一言堂式的(totalitarian)冷靜社會要好得多了。
記:然而你不認爲資本主義可以炒作人的慾望法則,製造開明的假像?
費:毫無疑問,我們生活在一個商品化全盤籠罩的時空中,但是爲了在其間生活,我們必須學會如何處理這種商品勢力。這就表示,一般人不會只是被動地(passive)接受市場。我認爲,所謂「市場」一直是人民和當權力量抗鬥、協商(negotiate)的場域。如果過於簡化複雜的市場,忽略人民選擇(select)的過程中,大量地利用市場玩弄市場的看家本領,這是一種過於化約主義的觀點。
快VS.慢
問:你在「全球化經濟下文化的角色」的演講中提到網際網路所帶來的變化,部分讀者對你的樂觀看法,頗爲反感,你對網路加大差距難道不表憂慮嗎?
費:對於這項爭議,其實也是我想在演講當中闡述清楚的。我想我們應該停止使用所謂的「第一」、「第三世界」或「已開發」、「未開發」這種「冷戰語詞」(cool
war terms),這些辭彙都應該留給歷史。我覺得用「傳輸快」與「傳輸慢」倒是比較接近當前實情的描述。特別是,這種描述並沒有地理分佈意涵的指涉,反而「快」與「慢」兩種世界可以同時存在,並且兩方互相毗鄰而居。就好比我所謂的權貴式在地(privileged
local)與勞動型在地,就分屬「快」與「慢」兩種世界,而不論他們是在美國或臺灣,倫敦或東京。
所謂傳輸「快」的世界指的是資訊與資金的即時流通及獲得,然而我所擔心的就是在這場戲局中,「快」與「慢」的差距愈來愈大、愈深,截至目前,我們還未看到許多縮減這項差異的嚴肅嘗試。
從樂觀到比較不樂觀
記:對於這個景況,你還抱持樂觀的態度嗎?
費:我感到非常地「掙紮」(conflicted)。我的確認爲「慢」的世界是真的處在危機當中,我並不樂觀。過去在福特主義之下,勞動力量集中管理,那種剝削是容易覺察出來,而今在後福特時代,在地的勞動單位分散而流動,反而不易讓人意識到,可是種種迹象卻顯示這種「慢」的世界,正面臨強大的被剝削壓力。另一方面,全球資本主義總是不斷地尋求擴張市場,不幸的是,「慢」的世界又是目前唯一留存、而全球資本積極想要進佔的領域。
記:對於隔絕於全球化的優勢之外的血汗在地者,例如那些幫耐吉生産棉衫的工人(記者註:棉衫工作廠是耐吉在全世界各地的超小型工作廠,通常以極低薪資僱用女人和小孩從事生産,一旦當地工資開始提高或法規開始保障工人,耐吉可以很迅速關閉這種超小型工作廠,立刻轉移至其他容許剝削的國家繼續生産。)難道他們就註定被這樣的跨國企業當作工具利用,而絲毫沒有對策嗎?
費:(停頓許久)當然是有的,這涉及跨國公司和工人對耐吉這個「品牌」的意義詮釋的抗鬥戰。如果這些工人正對著後福特主義時代的品牌邏輯,努力將喬丹所塑造的「品牌」形象,塗抹上一層醜陋的剝削色彩,讓人意識到這個品牌正面形象背後,所包藏的負面特質,才可以鬆動資方的高姿態,同時喚起國際性的注意,藉此由根部施壓,如此運動才可能成功。當然,這是最理想狀態,大部分的情況,血汗在地者(labor
local)並沒有條件挑戰品牌的力量,這才是令人憂心之處。
認同與全球化
記:我發現你已看出臺灣的兩種現狀,一種是極力搭上全球化列車的願景,一種是仍舊迂迴曲折在國家認同之上。這兩種力量似乎是當前兩種主要平行發展的趨勢,對於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民族建構,你似乎另有詮解?
費:安德森發展他的理論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可以說是福特主義式的品牌型式。然而當前是後福特主義或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的時期,安德森也許也不會樂見他的精細推考的「想像的共同體」論證,被抽離脈絡簡化地使用。然而,往往也事與願違。即使不願意,但我覺得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暗示了民族是由所有不同社會成員的共識(consensus)所構成,然而建構民族認同的過程中,往往會要求民族內的附屬部族,放棄自己的認同。與此相較,擁有權力的權貴,往往具有認同上的領導地位,因此,共識的達成比較切合他們本身的既定狀況,所要求他們犧牲的部分較少。所以,這種認同的形構歷程,往往蘊藏著很大的階層性格,也壓制了其中零星的阻抗火花。
我的一些學生告訴我,臺灣的民族主義包含了原住民、先後來臺的華人等,爲了達成想像共同體的共識國度,不少群體被迫整合進一種認同的框架中。因此,我十分懷疑臺灣的民族認同只能是「一種」(single),而更應該屬於多重連結式(hyphenated)、混雜的認同模式,當然,我知道這其中有很大的壓力。
記:可是很諷刺的是,在全球與在地兩極化的驅力之下,國家認同開始變得更加地多重連結、多重定義的同時,也有另外一些人感到一種認同的焦慮,對於全球化似乎敵意頗深?
費:國家在未來將仍不會消失,只是不斷地縮減她的影響力。這種矛盾,不止發生在臺灣,全世界很多人都在這全球化和民族間做協商,在這個場域,人民又再度顯出一種抗鬥的活力,從這一點來看,我還是樂觀的。
我就不認爲臺灣在全球化之下,將失去自己的文化認同。全球化不會將地方差異及文化掃除,只會改變它。我們對地方文化所持的那種傳統、保守的概念,將變得更爲流動、能動及開放,且絕不會變成完全同質的(homogeneous)全球化産物。在這個意義之下,我還是樂觀的。
全球/在地新關係
記:當前全球化和在地化兩種勢力的角逐過程中,地方(local)真的能夠和全球抗衡,創造不同於過去的在地意義?
費:我認爲全球化必須包含而且需要在地化。在我的區分裏,我認爲能夠掌握全球化資源的權貴式在地,能夠將在地歷史、文化帶入全球化的領域當中,利用這股力量創造出一種雜交型的(hybridized)文化。如果以封閉的、防衛的心態,試著去保守一種在地文化,認爲只有將全球化趕盡除滅才能保有純粹的地方性,我認爲這樣做剛好會「殺死」(kill)原先所要保護的在地。我認爲健康、騰動的文化活力,肇生於多重資源的滋養,以不斷地重新、重製她自己,所謂「全球」正是資源之一,因此,我不認爲一味否定全球以儲存在地的策略,最後可以奏效。
記:在這次來臺的演講中,你特別選了有關全球化及監控(Surveillance)的問題,你期待這兩個主題可以帶給臺灣一地的文化工作者,怎樣的刺激或衝擊?
費:當然,自然是這兩個議題最引起我的關注。我最大的希望是藉由和臺灣本地的學者會面的這段時間,試著去刺激(provoke)他們思考,如何將這些議題放入臺灣社會中討論。我只有一個帶有距離的視野,在對臺灣的片段瞭解中,我知道臺灣現在正掙紮於國家身份(nationalhood)及全球化的問題,但我覺得臺灣人民將更細膩而睿智地處理全球化和在地化的關係,這個複雜的脈絡不是我這個局外人可以窺其全豹,因此我只能說提供一個參考架構而己。
來源:清華大學人文日新網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上網日期 2001年07月02日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