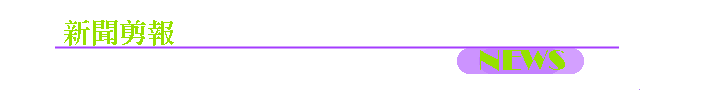|
|
||
|
跨性別的啟示與省思 【2000/07/10/聯合報 】 主題品書 朱偉誠 新聞來源:聯合新聞網 |
||
|
先是《男孩別哭》獲得多項奧斯卡大獎,把美國中西部鄉下青年布蘭登‧蒂娜(Brandon Teena)易服扮裝的悲慘遭遇推到了主流無法忽略的視界當中;然後是屏東葉姓少年在校內廁所離奇死亡,經過同志紀錄片導演陳俊志的熱心查訪,發現竟然與葉姓少年明顯的女性化傾向受到同儕排擠有關。這兩個事件中令人驚痛的冷血暴力,竟都指向跨越(被認為是逾越)社會一般男女分野的「跨性別」(transgender)行為,逼使大家不得不去正視所謂「跨性別者」所受到的歧視與迫害。 適逢此時,臺灣書市不約而同推出兩本女同志文化重要的譯作:一是一九二0年代末轟動一時的現代女同志開山之作,瑞克里芙‧霍爾的自傳體小說《寂寞之井》;一是九0年代初開始為跨性別運動發聲的費雷思(全名為雷思里‧芬柏格Leslie
Feinberg)自己的故事《藍調石牆T》,為我們比較深入地思索這些相關的議題提供了難得的契機。 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 其實同志運動在最初的時候,也就是跨性別運動,不惟因為當時在主流眼中,同性戀者無非就是一堆娘娘腔與男人婆,也因為在運動肇始的石牆事件中,正如《藍調石牆T》裡所記述的,帶頭反抗警察暴力的主要就是扮裝的女男同志。只是一方面在同志運動正式起跑之後,主流這種單一的認定與化約的等同被視為一種壓迫扭曲,因而為男同志所極力抗拒,並且有些矯枉過正地只強調自己也能十分陽剛的表現;在另一方面,由於女性主義對於男人之所以為男人的所謂男性構成(masculinity)的強烈批判,也使得具有男人樣的那些女同志(即所謂butch或本土的T),遭到複製男性沙文主義的批判。所以兩者終至分道揚鑣,跨性別者反而成為弱勢中的弱勢。 然而同志運動這樣的劃清界限,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毋寧是選擇了一條比較容易的抗爭道路,因為性愛取向上的異乎尋常,終究並不如性別行止上的違逆常規來得明顯,而且具有公開挑釁的意味。這也就是為什麼同志會有「出櫃與否」的難題,而跨性別者則多少一直背負著自己的汙名。畢竟那個決定於我們生理性徵的男女性別分野,是既有秩序所仰賴的種種區分中最根深柢固的一個。正如《藍調石牆T》中的主角潔斯所不斷遇到的質問:「你到底是男的還是女的?」可以見出這種不定所造成周遭的不安與焦慮。 生理上的女人與性別上的男人 尤其是當一個生理上的女性,在行為舉止上太過逼近地以慣常屬於男人的面貌出現時,似乎更容易激起(主要是男人)暴力的反應,因為男女之間權力不平等的現實,使得這種做法被視為一種「不當的僭越」。這種主流價值觀不斷內化的結果,則是跨性別的女同志自己,如潔斯與《寂寞之井》中的史提芬,都時常強烈地感受到自身的「不足」。而這種感受的極致表現,就是如潔斯一般想要藉著變性手術,來「回到」生理性徵與性別行止間相互吻合的伊甸狀態(雖然他/她後來中途放棄)。 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九0年代以來漸次興起的跨性別運動展露了它的顛覆想法,因為它所挑戰的正是這種「性徵(女性)→性別(女人)」的超穩定連結狀態,而主張大家皆有拆散此種連結,並且將其種種蘊含隨意組合的自由權利。所以不但一個生理上的女人不妨是性別上的男人,而且一個人也不妨同時擁有,譬如,乳房與陰莖。 這樣的想法或許聽來太過科幻駭人,但事實上這類型的人(如扮裝、變性慾者與生理上的陰陽人)早就自然存在我們週遭,只是一直受制於僵化的男女二分,不是被壓迫犧牲,就是被強行歸類,直到今天才有那麼一點機會來突破人類自己所創造的意識牢籠。而在世紀末與千禧年的科技創新,已經賦予人越來越多改造自己的可能之時,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去杯葛限制人們自我形塑的權利(變性豈不也是一種整形手術)? 逆向思考「非此即彼」的身份框架 不過,問題也確乎並非這麼單純地只是個人自由權利的伸張而已。因為對於「跨性別」作為一個極富啟示的進步運動而言,仍然必須要考慮的是:並不是一切跨性別的行為,都是符合它進步的概念的。有好些變性慾者其實並不想要停留在所謂的「跨性別」狀態,而只一心一意想要變成「真正的男人」或「完全的女人」;再不然就是有些在個性或裝扮上被認為是跨性別的人,卻極有可能因為種種理由,而根本完全拒斥這樣的思考範疇與認同標籤(「我並不認為我這樣算什麼跨性別啊」)。則跨性別運動勢將面臨所欲動員群眾自身「政治不正確」的反彈。 至於此次藉著《寂寞之井》與《藍調石牆T》所捲土重來的女同志「T婆關係」,固然是成功矯正了近來臺灣女同志圈主張角色「不分」所可能形成的批判霸權,卻也不宜忘卻當初之所以會有這種批判的緣由之一,毋寧是因為「T婆關係」在部分的女同志次文化中,已然僵化為一種非此即彼的身份框架與角色要求,以至於對無法或不願進入這種固定身份角色的人,造成一種排擠效應。則攻擊「T婆關係」是「複製異性戀關係模式」的批判,或許失之過激,卻也仍反映了部分真實存在的問題,是跨性別運動本身也不會贊同的。顯然跨性別不僅是一種他人無權干涉的個人自由,也是一個必須徹底自我「改造」的啟蒙過程。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