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我在一些運動現場的言論點燃了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為了負責任的說清楚「情慾解放」的含意,我在那年底出版了《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一書,全書現已上網,歡迎閱讀。當年在新書發表會上,一位女性主義同行提出質疑:性解放是西方說法,早已經被證明失敗,你憑什麼認為,我們拿來用會有不同的結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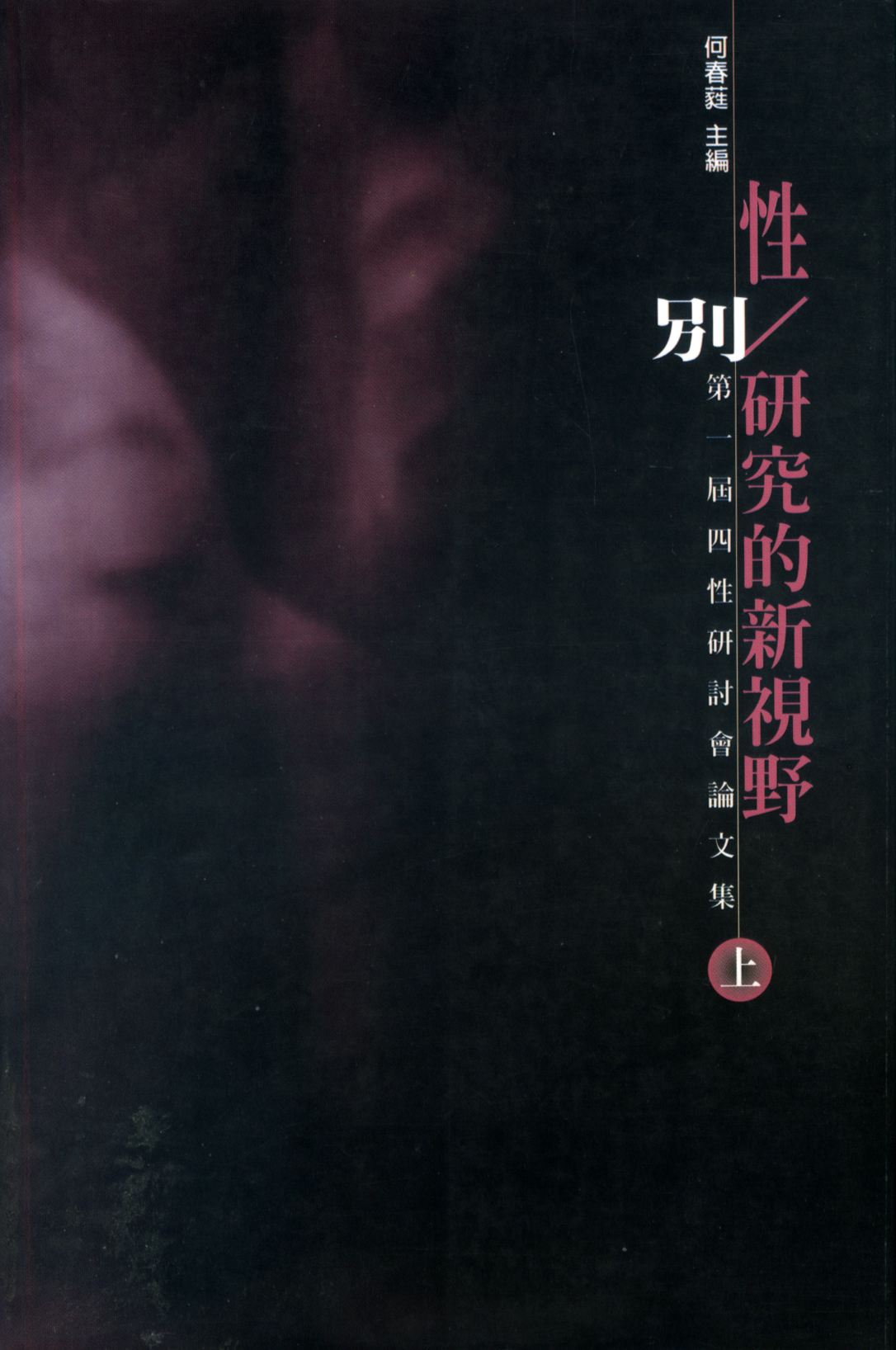 老實說,在那一刻之前,我根本沒讀過西方性解放相關的文獻,對我而言,女性情慾解放論述是我在本地社會文化脈絡裡意外生產出來的一些說法。但是為了回應這個質疑,我就努力做了一些歷史研究,並且用我所擁抱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分析方法,對被說成已經「失敗」的性革命歷史提出分析。論文首度在1996年6月29-30日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舉辦的第一屆性學、性教育、性別研究、同性戀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宣讀,然後出版於《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何春蕤編。台北:元尊文化,1997年。頁33-99。本文後來構成我「情慾政治導論三部曲」的第一篇。
老實說,在那一刻之前,我根本沒讀過西方性解放相關的文獻,對我而言,女性情慾解放論述是我在本地社會文化脈絡裡意外生產出來的一些說法。但是為了回應這個質疑,我就努力做了一些歷史研究,並且用我所擁抱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分析方法,對被說成已經「失敗」的性革命歷史提出分析。論文首度在1996年6月29-30日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舉辦的第一屆性學、性教育、性別研究、同性戀研究學術研討會中宣讀,然後出版於《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何春蕤編。台北:元尊文化,1997年。頁33-99。本文後來構成我「情慾政治導論三部曲」的第一篇。
第二篇 〈色情與 女/性能動主體 〉在 1996 年 5月 3日第 20 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中宣讀,定稿則發表於《中外文學》第 25 卷第 4期, 1996 年 9月,6-37 頁。第三篇則是 〈從左翼到酷異:美國同性戀運動的「酷兒化」〉,《性/別研究》第 3-4期合刊, 1998: 260 -299 頁。】
摘要
當主流女性主義者將簡化的階級理論接合到二元的性別分析架構上時,性別權力的社會佈局也被定型化,一切新興現象與改變都被放到這樣的定型內來理解。結果,面對現代情慾領域中的急速變遷躍動(亦即所謂的「性革命」),許多研究者都傾向於將其理解為只不過是順應資本主義的商品化趨勢而將身體進一步性化,或者只不過更加強化現有的階級、性別差距,讓男性的性掠奪方便化、正當化,或者只不過是情慾優勢女性模仿或複製男性慾望以擴張自己的情慾版圖而已。
這些夾帶著價值判斷與各種化約論假設的問題,需要歷史的、社會的具體複雜分析來加以回應。本文藉助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架構,整理釐清各家豐富錯綜的歷史敘述,描繪出美國近代百年的情慾革命史,最終顯示,所謂「性革命」的意義在於「情慾生產力」與「情慾生產關係」之間的張力如何被社會運動凝聚轉化,被情慾邊緣人口用來改變抗爭的基點、累積新的主體養成資源,漸次的質變情慾文化的承擔者。在這個意義之內,有關性革命已經成功或失敗的簡單判語不但是一種化約,更標記了新的「性部署」正在嘗試以這種判斷論述來消解已經存在而且繼續滋生的情慾脈動質變。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這段話帶著一股極強的必然性,指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激化矛盾就是社會革命發生的契機。這個分析方式固然提供了理論架構來思考社會革命的發生條件,可是它似乎也暗示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彼此獨立的整體,各自有其頗為統一的性質和內容,因而在兩者之間形成矛盾也是頗為容易理解和觀察的事情。
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阿爾圖塞(Louis Althusser)在寫《捍衛馬克思》(For Marx, 1969)的時候為這個架構做了一些補充。他引入了一個借用自佛洛依德的概念,也就是「多重決定」(overdetermination),細緻的說明社會革命的發生是因為許多「來自不同源頭、不同意義、不同層次和施力點的矛盾」──其中有一些甚至是極端異質的──在歷史際會的時刻同時積累於同一場域,融會成為一個爆發的整體,因而形成社會革命(100)。阿爾圖塞對多重決定的說法顯示,是諸多異質矛盾的社會力在某個社會場域的際會,互相影響,互相運作,形成革命;這個說法在上層/下層單向決定論(determinism)的二分模式中開闢了更多的複雜空間。然而,多重矛盾的聚積和匯集雖然聽起來是偶然的、自然的發展,但是其中仍有其必然性:「它們在『融匯』成革命式爆發時所構成的整體(unity)是被它們的本質和效應構成的,也就是被它們各自運作的特殊模態所構成的」(Althusser 100)。換句話說,阿爾圖塞認為即使是多重異質的矛盾,也會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中必然匯集成「整體」,形成革命。以1990年代此刻的眼界而言,這個具有某種統一性質的整體已不必然具有什麼實證意義,諸多異質矛盾的社會力也不再輕易的享有不言而自明的融匯傾向,但是作為一個充滿啟發性(heuristic)的思考架構,阿爾圖塞的分析模式在捕捉歷史的某些際會時刻上還是個可用的工具。
比較不為人討論的是,早在阿爾圖塞之前,奧地利的佛洛依德-馬克思主義者賴希(Wilhelm Reich)就已在其名著《性革命:邁向一個自律的人格結構》(The Sexual Revolution: Toward a Self-Regulating Character Structure)中[1],嘗試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另一種寬廣的理解,也就是把有關社會革命的結構分析運用到性的領域內。賴希和所有的社會建構論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一樣,認為個人的性慾強度及需求性質總是在「性」的社會發展中逐步形成的(Reich, The Sexual 17),婚姻則是最主要規範情慾的制度。他也觀察到,在他所處的歷史階段中,性──不管作為觀念或實踐──雖然已經發展到無法在既有婚姻道德所允許的關係中得到滿足,但是婚姻關係中(許多)妻子和孩子在經濟上的依賴位置卻仍然要求婚姻道德繼續鞏固,以維持婚姻制度的存在及其所提供的保障。而另一方面,(某些)婦女和青少年因為勞動民主化而得到機會參與生產工作,在經濟上逐漸向獨立自主邁進,在生活方式和情感心理上也傾向更多樣的需求,婚姻家庭制度之內強制要求的、一向極為有限的情慾運作管路在面對這些需求時更加凸顯出其威權的本相[2]。這兩股由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形成的根本變遷一旦匯集,就使得情慾的需求和婚姻家庭的道德要求之間產生了基本的矛盾──賴希認為這就是性革命的時機和條件了(Reich, The Sexual 152)[3]。
賴希的歷史眼界當然沒有給他機會能夠像1990年代情慾政治(erotic politics)研究者那樣細緻的認識「性慾強度及其需求性質」中包含了何種複雜多樣、與主流道德對立的內涵,他所說的「性革命源自婚姻制度的緊張矛盾狀態」似乎也太簡化了社會變遷過程。不過,以下本文將透過對19世紀末以來美國兩次重要的性革命的歷史分析,初步顯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特別是透過我對賴希和阿爾圖塞的運用和補充──在情慾領域中的可能操作[4]。我想要說明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在解放勞動力的同時,因著一些歷史際會的原因,而在商品化的過程中創造了愈來愈明顯的情慾發展與多樣化,這也就是我所說的「情慾生產力」(forces of erotic production)的大幅提升,以致於和原本規範情慾運作的「情慾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erotic production)──現階段最主要的體現就是一夫一妻父權婚姻家庭和異性戀體制──形成了強大的緊張狀態[5]。這種緊張狀態不但表現為情慾活動日漸升高的可見度,更帶動各種情慾論述展開意識形態爭霸戰,為各種運動主體創造介入施力的可能──這些激盪的匯集就是我所謂的「性革命」。
在理論的層次上我也想指出,情慾生產力的發展當然和資本主義生產及其所帶動的人口流動和慾望創造密不可分,而且情慾生產力的發展方向和形式也極可能糾葛了既存的其他權力網絡(如性別、階級、族群、年齡、性口味等)。但是這並不表示這個情慾生產力的躍進就全然只是為資本主義生產服務,或者必然只會加劇其他不平等權力的運作而已──提出這類結論的人不但低估了社會力的矛盾複雜(也就是高估了宰制權力的彼此配搭合作無間),同時也蔑視了權力弱勢的主體和她們的運動實踐在此過程中的各種可能壯大施力。
事實上,在本文的動態結構觀點中,「情慾生產力」和「情慾生產關係」並不是什麼固定明確的兩塊鐵板,而是情慾的不同呈現與沈澱在特定歷史時段中展現出來的緊張及對立。因此,某些在此刻被視為體現情慾生產力開拓躍進的實踐和論述,固然可能和那些體現當下情慾生產關係的實踐和論述形成意識形態領域的爭戰,但是這種緊張關係或者敵我的部署並非絕對或固定,它們都可能在進一步的挪用串連中,形成新的位置和關係,而且新生的情慾生產力若能在某些有利的條件(如基進社會運動的介入)之下擴散沈澱,建立自我再生產的機會,就有可能重織情慾生產關係的經緯,甚至介入資本主義主體再生產的途徑和性質。畢竟,傅柯所謂的「性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從不是固定不變的,它總是在各種社會力的激盪抗爭中流動變換的[6]。另外,性革命對於更廣泛的、根本的社會革命也有其深刻蘊含,我將在結語中提出賴希在這方面的重要貢獻,以破除此刻反挫氛圍中一般人對美國1960年代性革命過分簡單輕蔑的評價。
在本文的理論架構之內,性革命並不是情慾實踐被整體的、單一的、徹底的翻轉或全面取代;相反的,它是情慾模式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段中──被觀察到、被大量關注討論到──的多樣化發展,這個多樣化的增長速度和幅度使得性的運作方式、具體實踐、論述說法、甚至相關情緒反應,都一再突破原有情慾體制的決定或侷限,這就是性革命的徵兆。同時,本文對性革命的歷史分析也將指出,性革命的方向、幅度、以及它對不同社會群體的衝擊,都深刻受到基進社會運動的介入影響。因此,我在論述性革命這個問題的時候,將一方面關注多重異質的、在性領域中各有其特殊運作動力學的權力關係如何相互競爭、操作、衝突,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仍然保留像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樣的分析工具,以作為介入論述的切入點,希望能串連不同的抗爭,拉出一條鬆散但確定的反對戰線,在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s)的前提中不喪失對立政治(oppositional politics)的眼界。
I
研究性與社會之間互動關係的學者們多半同意[7],美國近代史上有兩個時期呈顯出極大的情慾模式變遷,也就是我所說的「情慾生產力」和「情慾生產關係」極為緊張的時期,一個是1880到1920年之間有關性道德和婚姻的重大轉變,另一個則是1960年至今瀰漫西方的性革命[8]。這兩次性革命在各自的歷史條件之內都已形成重大的影響,深刻的改變了家庭、婚姻、愛情、性、墮胎、求偶、同性戀等等的文化面貌及實踐,而這些具體的衝擊和改變並不是「成功」或「失敗」等等簡單評估可以捕捉的[9]。或許運動者更需要做的,是深入研究這兩段歷史,以便尋找可以在現有脈絡中使用的思想及運動資源。
雖然史料極為有限,常常要依賴口述流傳的個人經驗和觀察,或者只能從一些政治決策者對社會現象的憂心記述中側面推敲,但是研究者幾乎都同意,最明確標記出19、20世紀之交的性革命的,就是過去在情慾雙重標準之下飽受限制和監控的女性。19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持續轉變以及伴隨而來的家庭功能變遷,很明顯使得女人的社會定位有了極大的變化,女人有了更多的人生選擇,逐漸有機會和能力脫離以婚姻家庭為主的依賴關係和生活空間[10]。引人注意的是,當時(未婚的)女人開始有經濟能力和機會發展新的屬於她們的生活文化時,由於一些很重要的歷史因素的際會(詳見下文),使得「性」成為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面向,並在開發情慾的過程中形成了鬆動原有情慾關係侷限的趨勢。這也就是說,「某些女人【在當時】之所以選擇進行比較隨便的情慾模式,這必需要透過那個更廣大的塑造其性文化的階級關係和性別關係來理解」(Peiss 132),而不能簡單的歸納為「女人的經濟獨立」而已。
促成世紀之交美國情慾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顯是當時資本主義大幅擴張時所帶來對家庭結構的衝擊。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和勞動力的需求,年輕勞動人口開始流出原有家鄉的人際脈絡,進入新的都會空間,單身的勞動者大量集中到工商業都市的周邊,在逐漸增多的臨時居住空間(如YMCA)或者供膳宿、混合性別的寄宿型住家中找到居所,以便在當時新興的工廠、店鋪、和百貨公司就業(Seidman, Romantic 67-68)。在這些外在於家庭或社區人際網路的流動生活空間裡,年輕的勞動者開始建立新的人際網路,原本被父母、教會、鄰居、學校主導的求偶模式,漸次被自主性愈來愈高的交友方式取代,年輕男女在嘗試和摸索中社會化,逐步發展出在她們父母和社群控制之外的情慾關係和模式,而且由於多多少少擺脫了原生家庭和社區的持續規訓,她們對於不合道德常規的性活動也有較高的容忍度(D’Emilio & Freedman 228),這種自在和自由於是形成了情慾生產力蓬勃發展的有利環境。
在另一方面,年輕勞動人口的流動和集中居住,以及新的年輕生活形態和經濟實力的形成,很快的回頭為當時正在擴張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提供了開發新型消費的誘因,以便吸收工資回籠,創造新的利潤。這些新興的消費事業則重新定義原本在家庭脈絡中進行的閒暇活動,把工餘的「休息」轉化為在商業領域進行的「休閒」(Freedman 38-39),而為了呼召年輕的消費主體,這些休閒事業多以一向最被成年人壟斷的「性」為最主要的賣點,戲劇性的促成了情慾生產力的大躍進以及情慾生產關係的多元化。
眾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當時在都會區出現大量像舞場和俱樂部之類的新物質空間,首度標誌了陌生男女當時已經可以藉此聚集並互動調情,這些新空間則把工作之餘的休閒呈現為勾動情慾的特別節目與活動形式,以便吸引下班以後無「家」可回但是又無事可做的年輕單身消費者(D’Emilio & Freedman 195-196)。在這種充分激動而鼓勵的空間中,年輕的消費者相應的自發創造並擴散新的身體經驗,刺激新奇、兩人配對、擺動身軀、密切接觸、充滿情慾暗示的動感舞步,取代了19世紀那種老少皆宜的排序制式集體舞步而成為新的流行;同時,從擺動臀部到身體接觸到擁抱等等充滿性暗示的動作,也直接雕塑出新消費主體充滿情慾活力和誘惑的身體(Seidman, Romantic 71)。此時各種新興的「釣人」據點出現,更凸顯情慾的波動已經在這個階段成為休閒活動的主要觸媒(Peiss 128-129);交遊的需求甚至帶動其他新型娛樂場所的興建,世紀之交開始出現的大型遊樂場(最出名的例子就是紐約附近的Coney Island)就以各種刺激驚險的遊樂設施來直接提升感官的刺激,並以各種聳動情慾的廣告來間接鼓勵陌生男女在搭乘遊樂設施的緊張過程中順勢進行身體的接觸[11]。同一時期開始出現的電影院則提供了黑暗的自在空間和銀幕上具體的情慾形象,供情侶們邊看邊學,在後段號稱「情人道」的座位中探索情慾接觸的極限(D’Emilio & Freedman 196-197)。
以上這些以情慾為主要焦點的空間硬體及活動形式,同時在世紀之交出現、普及、和擴張,不但標記了情慾的可見度和強度大幅提升,凸顯了情慾生產力的迅速擴張,同時也顯示身體情慾協商模式的重大轉變,逐步超越原本由父母和宗教道德主導的交往範疇,代之以隨著資本擴張而大幅提升的情慾強度與多樣性。人口的流動聚集、因就業而延後的婚齡、情慾的擴張和平常化──這些變遷都在情慾生產關係中引進更多變數,創造了更多空間和資源,邊緣情慾形式因而得到發展和成熟的的機會,使得不婚和同性戀在這個階段首度成為個別女性在婚姻之外的人生選擇(D’Emilio & Freedman 190-193),並且在紐約哈林區和格林威治村等少數特殊地點成功的形成明顯可見的同性戀文化及社群,藉著周遭情慾生產力創造的開放空氣而自在發展(Faderman 67-92)。
當然,即使在這些邊緣的情慾社群中,情慾生產力的躍升就個別主體而言也有不同的意義和實踐空間。具體來說,未婚的年輕就業人口雖然在經濟上證明了自己有生產力,但是在操作這種經濟能力以滿足自我的物質需求上仍然受到既存的性別、代間權力、階級等因素限制[12]。例如,女性勞動者的個別階級位置往往影響到她們情慾實踐的能力,有些中產女性因為受過大學教育,就業機會比較好,經濟能力比較獨立,因此比較有本錢選擇終身不婚或採取被稱為「波士頓婚姻」(Boston Marriages)的公開同性同居;無產階級女性的同性情誼則多半以一人扮裝為男人來製造異性同居關係的形象,以避免人言(D’Emilio and Freedman 188-194)。另外,代間與階級位置也在女性情慾空間上形成複雜的影響。勞動階層女性的工資有限,而且仍被視為家庭整體收支的一部分,除了日常生活的必需之外,絕大部分工資要交給父母以貼補家用。這麼一來,她們面對各種流行的消費形態時所能使用的資源就很有限,在這種慾望與實力的大幅差距狀態之下,以性作為某種交換蔚為風氣[13]。勞動階級的女性可以主動以當時流行的、但是與妓女大為不同的「甜頭女郎」(charity girls)的方式,用不同程度(除性交之外)的身體開放來換取男人招待她們享受新興的休閒娛樂,但是也因此在其中開闢出比中產女人更大的情慾探索機會(D’Emilio & Freedman 198-200; Peiss 134)。
II
情慾生產力的大幅擴張一旦形成以上所顯示的可見度,並向情慾生產關係的疆界和底線挺進,就難免引起另一些社會力的騷動。1860、1870年代已經開始對情慾生產力逐步增長的強烈關切,首要表現為由一些性主流婦女主導的社會改革運動。例如,「社會衛生運動」(social hygiene movement)與「淨化運動」(purity crusades)就在此動盪的時刻合流,希冀透過宣揚文明的道德觀來教導維多利亞式的自制,並消除性病及其傳染媒介──妓女(Seidman, Romantic 72),以維繫既有情慾生產關係的穩定;她們也呼籲政府消滅紅燈區,並且透過婚前驗血、性病病例強制報告等等措施來加強對性的管理(D’Emilio & Freedman 205)。這些有組織的社會運動成功的把紅燈區趕到性主流婦女視野之外,進入勞動階級、移民、和黑人的居住區域,反而大量增加了勞動婦女(即使短暫)賣淫的機會,然而也為後來進一步擴大強制掃黃提供了正當理由(Peiss 132-134)。
值得注意的是,當階級意識在這種張力中凸顯時,「性」也開始逐漸成為身分認同的一部分[14]。換句話說,不但階級可以透過性來反映其在社會資源和權力上的差異(某個階層的人才可以得到或享受某種性),同時,性本身也漸次成為構築階級的文化範疇(表達或擁有某種性才算是某階級的成員)(Haag 165)。因此研究者注意到,20世紀初新興中產階級女性定義自我的方式之一,就是透過各種行動和論述來顯示自己的情慾是道德而自制的,與當時普遍可見的妓女、甜頭女郎、或淘金女郎那種商業化了的情慾截然有別。即使在進行與傳統有別的情慾探險時,中產階級女性也強調自己是有意識的「自主情慾」,而不是像基層年輕女性那樣心智不成熟,暈頭轉向,無法掌控自己的性,更不像基層年輕女性那樣物質能力太弱,以致於拜金虛榮,只能盲目順從情慾市場的邏輯(Haag 165)。中產階級對自我情慾的這種定位與期許,一方面推動了各種健康衛生或淨化的改革運動成功的操控社會輿論,另一方面,也常常表達為對基層女性施恩式的保護心態,反而形成對基層女性主體的另一種管制與階級壓力。
在這裡我們看見情慾生產力和情慾生產關係在世紀之交形成的拉鋸戰,而正是這種拉鋸戰在性文化中形成了意義和實踐的移位及轉化,才使得我們注意到性革命的徵兆。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固然推動了休閒與情慾的結合,提升了情慾的生產力,而隨著消費生活形態的擴散,新興的消費道德也繼續鼓勵充分享受愉悅,追求自我滿足──包括在情慾方面的享受和滿足(D’Emilio & Freedman 234);但是,同時在這種突破各種原有權力和慾望疆界的氛圍中,情慾生產關係也因為它與其他權力關係以及整體文化生產關係的共生而必須採取一些維繫本身穩定的努力,也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中產淨化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這種穩定局勢的努力,世紀之交的進步社會運動也發動了新的性政治,不但為(已婚)女人爭取節育的權利,也在無意之中間接的為未來發展並推廣更普及、更方便的避孕措施準備比較有利的環境。隨著都會的形成以及其所帶來的人際關係複雜流動,美國政府原本在1873年設立「Comstock反色情法」,嚴厲禁止避孕資訊和工具的公開販售或宣傳,拒絕讓女人的身體和人生脫離生養重擔的陰影,世紀之交的社會運動因此把這方面的解放視為重要目標。1910年代前後的基進運動份子(特別是艾瑪.勾嫚Emma Goldman與維多利亞.伍得爾Victoria Woodhull)、勞工運動領袖(如尤金.戴普斯Eugene Debbs)、進步記者(如約翰.瑞德John Reed)等,都相信社會解放必然包含身體情慾的解放,因此大力鼓吹「自由戀愛」(free love)的說法(這裡的戀愛事實上指的就是性),積極反對制度性傳統婚姻的相互責任制及生殖目標,並主張建立以熱烈戀情為基礎的新關係模式,企圖在被視為個人實驗的情慾活動中創造社會運動集體努力的目標(Bullough 101)。勾嫚並且首度為當時還被視為非法的各種節育避孕措施提供「女權」的理論解釋,認為節育是女性身體自主的具體運動路線之一,女人(特別是勞動階級的女人)應透過節育來拒絕強制式的母性母職,這不但可以為女人創造自我生命的實現空間[15],更可以因女人集體的抗拒而形成對資本家的壓力[16](Grant 40; D’Emilio & Freedman 232; Segal 82)。
就個別的女人而言,這個非常基進的左派運動路線為女人的情慾處境提供了一個新的複雜力場。因為,在節育不普及的年代,懷孕的高機率可以被女人用來擋掉不想進行的性事,但是它同時也為想要開展人生的女人創造無比的焦慮和可能不想要的後果。而左派運動在此時把節育重新定義為女性自主的正面措施,一方面奪走了女人推阻性事的方便理由,迫使女人不再繼續強化性和懷孕之間看似自然必然的連結,轉而在女性主義抗爭的基礎上擁抱情慾,甚至在抗爭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積極尋求新的抗拒論述。另方面,節育也很明顯的降低了女人參與情慾活動的代價,享受情慾再也不用像過去一樣必然帶來生養的重擔,相反的,女人從此可以全心投身創造其他的人生出路,迎接新的挑戰。
以世紀之交的歷史眼界,這個抗拒母職、身體自主的說法是非常進步的。然而後來最積極推動節育運動的人,像瑪格麗特.桑兒(Margaret Sanger)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瑪俐.史透普斯(Marie Stopes),卻都在各自的交遊圈中受到了當時中產階級背景的優生運動(eugenics)所影響;她們冒著牢獄之災,熱誠的推動節育的理念和實踐,基本信念則在於減少下層貧窮或「低等種族」的人口,以便讓社會更進步(Asbell 9; Grant 43; D‘Emilio & Freedman 245),同時為了避免背負鼓吹性開放的惡名,她們也堅決反對教導未婚女性避孕 (Grant 41)。結果,在不動搖種族、階級、婚姻地位的立場上,優生的信念逐步贏得了醫學人士的支持,並進一步透過醫學論述建立的正當性,節育運動得以在大西洋兩岸開展,其主要的對象則是下層階級的已婚女性。從這個發展來看,這些努力雖然促使節育得到正當化的地位,間接緩和了一般民眾對性的顧慮與負面印象,但是節育的基進解放內涵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出自優勢階級立場的優生考量所取代[17]。
當劇烈的社會變遷引發輿論強烈關切社會秩序的變動時,有關「性」的論述往往成為道德及社會變遷的一個象徵指標,也因而成為各方爭戰的場域,更成為階級張力充分展現其操作的替代場域(Weeks 74)。畢竟,情慾上的越軌行為並不只是女人們各自生活上的祕密而已,情慾論述也不只是另類的意見而已;事實上,世紀之交的情慾消費空間、活動以及論述一旦形成高度的可見度,很快就引發社會關切,並因而激化各種道德的和意識形態的辯論,更加提高性革命的分貝。
世紀之交,除了前面提過的社會淨化運動和進步社會運動之外,來自美國第一波本土性學先驅者的專業論述也在此刻浮現[18],其動力和正當性則來自社會淨化運動對性病、青少年、及女性情慾的憂心(Bullough 304-308; Weeks 75)。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時的性學研究基本上也是一個新的身體政治學:它以專家的、學術的、醫學的論述,來重新定義並經營身體的規範、道德的重整、甚至優生的考量。
即便如此,性學研究從歐洲發源開始就帶著另一些相對於當時主流文化脈絡而言頗有進步意味的內涵,因而也有助於推動性論述與性意識的革命。性學研究者對科學抱持的無上信念不但表達為他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更呈現為他們對性的自然法則的追尋(Bullough 3-6; Hekma 187; Weeks 62-72),而這種把性當成自然天性的研究態度和語言,有效的挑戰了原本由道德譴責來主導的傳統性論述,也首度提供機會讓諸多性模式浮現。歐洲的性學研究前驅們(如Richard von Krafft-Ebing, Havelock Ellis, Magnus Hirschfeld等人)都竭力以客觀的語言來描述性的各種面貌及形態(由性變態到同性戀到童年性慾到女性情慾等等),他們鉅細靡遺的記載個案、分析特色、列舉性質,終究則是希望在這些看似差異多樣的性現象及性表現之下,發現其共有的性慾源頭及自然法則,並追溯此源頭在發展的過程中因著哪些個人的、意外的、環境的因素而形成此刻眾多差異的面貌。性學研究者於是以性百科全書的模式來記載描述並進行他們對性的分析;取樣的完備多樣及描述的準確詳盡是他們的目標,理性的了解和冷靜的研判是他們希望投射的形象。在這兩方面,性學研究都展現了典型的現代化趨勢及色彩,研究者自我期許客觀中立,以科學為指標來理解並掌握性的各種面貌和表現,在知識的領域中努力發現有關性的「真理」以奠定性學發展的基礎。在那個還頗為宗教禁慾、道德保守的社會環境中,性學自詡的理性研究態度可以說是非常前衛的。
性學論述對性實踐和性主體的列舉描述固然將各種性主體類型化、定型化,促成了後者被抹黑醜化,但是學者們指出,性學論述同時也生產出可以被轉化挪用的語言和思考(Bullough 318; Faderman 91-92; Weeks 76-79)。至少,性學研究的科學語言在某一程度上正當化了性的社會呈現以及一般人(特別是女人和青少年)對性的高度興趣,因此間接支撐了情慾生產力的發展,甚至從性學研究的角度顯示了當時情慾生產關係規範之不當[19]。這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舶來的性論述,例如,英國的哈夫洛克.艾利斯(Havelock Ellis)的著作在英國被禁,因此轉而在1897到1910年間連續在美國出版了六冊《性心理學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雖然他的理論仍然假設了男女在情慾表現上的本質差異、性愛靈肉之不可分、以及一夫一妻制度的優越性(但除去了排他的貞操觀),可是艾利斯同時也對19世紀以來的保守情慾傳統大加批判,平反了手淫、女性情慾、同性戀等等積極表現情慾的方式,把非婚姻生殖導向的性,從過去那種病態罪惡的說法,轉化為無法自抑、「不可避免的發展」(Robinson 13),具體的試圖在以婚姻和生殖角度來思考情慾的傳統中投下變數。另一個對美國情慾生產力有重大影響的性學研究者就是1909年首度訪美的佛洛依德,他有關幼兒性慾、家庭羅曼史,以及性壓抑會導致精神官能症、性本能強大而時時流動等等說法,透過諸多知識份子的普及引介而深入人心,促使性逐漸被視為一個不能不面對、不能太壓抑的能量,把性更加自然化、正當化,也把人類的文明(以婚姻、異性戀、保守性道德等為代表)顯為外加之惡(D’Emilio & Freedman 223)。世紀之交的這些性學研究論述都對情慾生產力和情慾生產關係之間的互動關係有著複雜但是深刻的影響。
年輕勞動人口的流動生活方式、資本主義慾望生產的擴張運作、情慾空間和活動的多樣化、激進社會運動的眼界異象、中產階級的認同及其性操作、性學研究的啟蒙理想──這些因素各有其運作的方式和領域,各有其推動的方向和速率,彼此之間甚至有著重重因果滲透關係,但是它們的歷史際會,在快速增長的情慾生產力和搖搖欲墜的情慾生產關係之間形成複雜的張力。
這個張力在世紀之交性革命末期的歷史沈澱,可以在1920年代風行美國的各種婚姻手冊中找到跡象。在這些婚姻手冊中,雖然貞潔仍然是個不言而喻的鎮山石,而性基本上還是被要求在婚姻之內進行,但是從《婚姻之愛》到《理想婚姻》[20],當時走紅的婚姻手冊的書名就描繪出婚姻性質的轉變:情感和性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性愛的滿足被視為是夫妻二人都需要努力的目標(D’Emilio & Freedman 265; Seidman, Romantic 77-81)。而當婚姻的品質(特別是性愛的品質)被凸顯,被視為夫妻雙方的責任時,這也暗示婚姻的問題是可以由個人的努力來解決的──只要有「專家的指導,如:正確的性知識,適當的技巧,和正確的態度」(Seidman, Romantic 76)。
這種對婚姻和性愛關係的改良式看法,顯示情慾生產關係已經發生了深刻變遷,因此一夫一妻婚姻體制也必須為此前澎湃的性革命提出了一個折衷的調和,把性更深刻的崁入婚姻關係,以間接對蓬勃的情慾生產力加以包裹控制[21]。同時,這個關注也種下後來美國社會對「正確性知識」的渴求,強化了性學論述和專家在情慾領域中的知識權力運作。
III
經歷世紀之交的性革命之後,1930、40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或許帶來了生活的困苦和不安,挑戰了情慾活動的動力和物質基礎[22],因而挫折了情慾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但是這個物質缺乏、生存不易的時刻卻也使得切斷性與生育之間的連結成為愈來愈迫切的需求,加速了各種節育措施由中產階級向下層擴張(D‘Emilio & Freedman 247),反而漸次鬆動了既存的情慾關係體制。相較於情慾文化其他方面在這段期間的緊縮,避孕研究以及原來已卓有成果的性學論述這兩方面的耕耘反而在此需求中有長足的進展,也為60年代蓬勃上路的性革命準備了具有正當性的論述和實踐,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避孕研究方面,醫學發展史上一向充斥著因為懼怕「不道德」的標籤而放棄或避免的性研究(Bullough 135)。1930年代內分泌醫學首度成功的分離出男性和女性荷爾蒙之時,原本也只是想對(男性的)生殖功能和循環有更深入的認識[23],希翼透過操作荷爾蒙的分泌來創造或終止衰老的過程(Bullough 125-126),至於要進一步獲得正當性來進行所謂「干預自然」的節育研究,這還需要另外一些強大的理由。好在,1920年代性革命之後,新婚姻手冊的風行不但反映了性愛在婚姻中的意義和地位已有了重大的轉變,同時也具體呈現了許多人不便明說的擔憂──那就是,傳統的婚姻日漸衰頹,而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夫妻因擔憂懷孕而在性愛生活上躊躇(Bullough 137)。這樣一來,一旦大家相信性愛成為婚姻關係中須要不帶後顧之憂進行的熱情活動,那麼和性愛相關的資訊及商品就成為迫切需要普及的基本裝備了。這個和改善婚姻關係相連的考量使得從1930年代開始,不但許多藥廠對相關避孕的研究大有興趣,連醫學界也因為避孕和婚姻幸福的連結已經得到了正當性,因而投入研究。在這種社會氛圍中,從19世紀起就以淫穢為理由阻礙節育研究討論及資訊流通的Comstock法案終於在1936年取消,積極推廣節育避孕的「計畫生育」組織(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於1942年成立,正式標記了節育從進步運動的女性身體自主理念,轉為鞏固家庭結構、提升家庭品質的政策性措施(D’Emilio & Freedman 248),然而也在此中留下了改變性意識的種子和建制,為70年代墮胎合法化提供一個現成的發展據點(D’Emilio & Freedman 335),這是後話。
值得在此提醒的是,1930、1940年代不管是婚姻性愛或避孕節育,甚至婚外婚前的各種性實踐,都已經是在世紀之交性革命所沈澱的性意識中被理解、被認知、被慾望。換句話說,前一段時期情慾生產力在性活動、性論述、性道德方面的熱烈發展或許在此刻速度減緩沈潛,但是它們已經留下了新的情慾地平線,新的思考和經驗起點,甚至構築了新的情慾運作基礎。畢竟,艾利斯和佛洛依德性理論的通俗化引介,透過對婚姻性質的新要求,已經深深的種下了性的正面意義與必要性,求偶消費文化的積極變遷則逐步正當化了許多新的性活動,這些都重新刻劃了性的文化想像與呈現,將在下個階段重大的人口遷徙集結中帶動新的情慾生產力。
以1940年代一個重要的發展為例。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涉入,深刻的影響了原本以異性戀婚姻為主的情慾發展,大批年輕美國男人離開原有的異性戀人生軌道,進入男性集結的軍中,後方的女人則首度有機會穿上傳統認為非女性的服裝──長褲(Faderman 125),離開她們受限於異性戀婚姻家庭的小世界,大量進入幾乎全女性的國防工廠和軍事單位工作。同性情誼於是在這兩個純粹性別的有利場域中甦醒茁壯,並在戰後解散軍隊時繼續在諸大城市集結發展成為同性戀的新社群(Faderman 120-130)。但是,這一波的同性集結和世紀之交的同性情誼發展有一個根本的差異:世紀初性學論述對性的凸顯以及對同性戀的友善描繪,加上1920、1930年代圍繞著像《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之類通俗同性戀小說的猥褻官司和知名度,使得1940甚至1950年代對同性情誼的期望、想像和實踐都帶著身體和性的全部慾望和動力,前一個世代逐步發展的性意識、性實踐和性態度也在此時達到了新的成熟高度和多樣性,這些歷史條件的匯集遂促使二次大戰後的情慾生產力開出燦爛的同性戀花朵來。
另一方面,如果說世紀之交的性學研究使得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正當性,被視為人生重要的動力,那麼1940、1950年代的性學研究在戰後的新性別氛圍中就更進一步展現了性慾的多樣呈現,自然化了性的諸多表現及滿足形式。特別是印地安那大學的金賽(Alfred Kinsey)接連出版有關男性(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1948)和女性(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1953)性行為的研究報告,將性充分帶進大眾的眼簾。這些研究的龐大數據、廣泛取樣、及綿密的訪談,有力的聚焦於美國人的性習慣和性價值觀,具體的顯示有一個極其廣大多樣而隱密的情慾世界存在於普通人的生活中,和一般道德規範所教導的單一貧瘠模式截然不同,而所有的性實踐和性口味,不管多麼邊緣,在金賽的分類系統中都不過是性光譜上具有些許程度差異的表現方式而已(Bullough 172-177; D’Emilio & Freedman 268-270; Robinson 66-81)。金賽的性研究所投射的科學形象和數據的說服力,成功的扣緊了當時實證科學在通俗媒體中日漸升高的可信度,不但吸引一般媒體廣泛刊載引用,也提供了大量範例素材給尋求聳動題目的通俗作家及專欄作家自行轉化運用,因而更加普及了金賽研究的結論,形成主導美國性討論的權威論述。
金賽性學報告對美國情慾生產力的發展顯然有深刻的影響。畢竟,當性理想與性現實之間的差距和差異鋪陳眼前時,群眾過去對自己獨特性事上的焦慮終於得到了紓解;當眾人各自的性差異觀點和性實踐以具體數據和細緻描繪方式呈現時,原本單薄的情慾資源世界突然有了豐盛的想像和學習空間;而當性學研究成功的結合了實證研究努力建立的強大說服力時,性的公共討論和呈現也同時贏得了正當性。更可貴的是,金賽的性多元理念正是在冷戰的1950年代麥卡錫白色恐怖對性異議份子的沈重打壓之下浮現[24]。儘管帶著有限的歷史眼界,金賽對性差異的包容尊重態度在當時保守的政治氣氛中卻仍然奮力創造了新的友善環境。例如,當性習慣和性價值觀被性學研究顯為多樣而差異時,當性被認為不再僅僅是異性戀插入式性交時,一向控制性的文化呈現的司法官就再也不能以單一的尺度來衡量性的公開消費。因此,由1957到1967年間,以華倫大法官為首的美國司法系統對色情表達出極大的寬容態度(D’Emilio & Freedman 287),使得情慾言論自由得到司法制度的包容,性的商品迅速嗅出開發市場寬廣需求的機會(Ehrenreich et. al. 105),一向被打壓在地下流傳的色情書籍、雜誌、圖片及其他商品終於得以搬上抬面,為情慾生產力的多樣發展提供最具象的呈現。
畢竟,性學論述或許在學術和理性的層次上提供了思考框架,但是對於普通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實踐而言,還是要靠通俗出版品以持續的、多采多姿的方式把性自然化於日常生活的消費和活動中。在這方面,美國出版業在1939年推動的「平裝書革命」首度使書籍得以廉價方便的在處處皆有的雜貨店、報攤、及其他零售據點販售,1940年代的出版商於是順勢推出各種聳動的小本情慾小說、撲克牌、照片、甚至色情內容的唱片(D’Emilio & Freedman 280),這些小本經營的性文化事業為當時不太豐富的情慾資源提供了最平民化的消費,也大量普及了情慾的圖像和感官呈現。隨著美國經濟的快速蓬勃發展,1953年海夫納(Hugh Hefner)創立中產品味的《花花公子》月刊(Playboy),接著推動各種和情慾相關的休閒企業,不但以最絢爛的方式展示女體,更同時推動男性觀點的性自由哲學,鼓吹自我沈醉和奢華的生活方式,帶動了整個一代男性的自我幻想形象(D’Emilio & Freedman 302-303)。
有些教條女性主義者或許認為《花花公子》的出現僅僅是父權恣意展露其自身的醜陋面目,但是也有許多其他的女性主義學者指出,這種文化產品的出現其實主要是因為當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逐漸進入消費導向的經濟,需要把佔一半人口的男性也營造成為新的消費主體而非汲汲工作的生產主體而已,因此鼓勵男性背叛傳統中以養家為人生成就的男性形象,多在消費活動中實現自我。在這個理解框架內,女性身體的暴露呈現,與其說是僅僅提供給男性發洩享用,倒不如說具有另一種進步意義,可以用來鬆動拆解「男人打拼養家」的傳統性別分工模式,更重要的則是保障男性認同與異性戀的不可分 [25](Ehrenreich 51)。這個解讀在性別的軸線之上又加了經濟模式和異性戀兩條軸線的考量,對情慾現象提出了較為豐富的理解。不管如何,《花花公子》深刻的改變了女體的呈現,改變了情慾的形象,它以最有中產品味的口味形式來包裝呈現過去在道德規範下被當成最低俗的情慾和身體活動,具體呈現了──也因此正當化了──新的、性的市場品味。
也正是因為像《花花公子》之類的男性色情產品以明顯的男性本位觀點自然化了性的開放,因此許多女性主義者在評估這段歷史時,常常認為性革命其實只是屬於男性的「性市場革命」而已(如Jeffreys 91-94)。不過,這個簡單的評估有點問題,另外一些女性主義者就指出,性自由並不是什麼出現在男性生活裡的嶄新東西,一般而言,男性一向就享受比較大的情慾空間:「事實上,如果有哪個性別曾經經歷性態度和性行為的大轉變,值得被稱為革命的,那應該是女性,根本不是男性」(Ehrenreich et. al. 2)。
IV
世紀之交的性革命已經為女性情慾主體創造了個別實踐和探索的具體空間,1930到1950年代一連串論述、研究、以及通俗文化在性領域之內的累積則為性的享受創造了正當性;時至1960年代,風起雲湧的社會解放運動將被壓抑的、禁忌的話題更廣泛的帶入文化領域,年輕一代藉著不受羈束的身體性愛做為抗拒成人建制的政治表態方式(Grant 13),資本主義的情慾生產則在文化論述方面達到另一個高度,這股強大挑戰既有性道德的動力使得新的情慾主體的生產進入了集體的、全面的發展,形成第二波的性革命──帶頭衝刺的仍然是女性。
首先,景氣的1960年代資本主義在文化消費層面上的積極生產,使得躍躍欲試的女性得以在商品和新的生活方式中具體塑造女性情慾主體的身分與實踐。最明確的徵兆就是,1950年代的女性雜誌主要還是一般的家庭主婦雜誌,充滿日常生活中的家事心得和經驗,但是短短十年後,性變成了女性雜誌的主要賣點。例如,原本是家庭雜誌的《柯夢波丹》(Cosmopolitan)於1963年由以暢銷書《性與單身女郎》(Sex and the Single Girl, 1962)著稱的作者Helen Gurley Brown接手編輯[26],初期以職業婦女的生涯指南為主,但是很快就認識到讀者群的性質已經在歷史的過程中轉變,新一代的年輕婦女經濟上比較獨立,自主的動機強,教育水準也已提高[27],《柯夢波丹》於是聞風轉向,順勢把當時英國已經很發達的「浪蕩單身女人」(the swinging London dolly-bird)概念,建構為新的美國版「柯夢女郎」(the Cosmo Girl)。在雜誌內容方面則主要是為單身女郎提供情慾和身體消費上的指南,並且明確的以圖像和文字來表達女人擁有新的性自由。雜誌推出之後大受歡迎,有些歷史家甚至認為,《柯夢波丹》最大的貢獻就是使得女人的性顯為自然而可敬(Grant 98-123),這在普遍相信「性屬於男人」的美國文化中是很重要的一個發展,也帶動了後來其他如Ladies’ Home Journal以及Redbook等傳統女性雜誌在競爭的壓力下進行對性話題的開墾。
除了通俗雜誌的女「性」化之外,充分反映1960年代女性觀點的性學論述也在此時深刻的影響了一整代女人對身體、對性的觀點與實踐。其中最有名的研究論述要算是馬斯特與瓊生(William Masters & Virginia Johnson)的Human Sexual Response(1966)以及Human Sexual Inadequacy(1970)。這些研究雖如其批評者所言,受限於中產智識階級受訪者的性經驗和偏好口味,只反映了那個階層的成年受訪者在性事上的特有表現,把高潮當成性愉悅的唯一尺度,甚至在統計時還刻意排除了所謂偏差的情慾模式(Robinson 134-140),但是馬斯特與瓊生的研究首度正面肯定了人類可以主動透過自慰來達成情慾上的自給自足,他們對性高潮模式的分析還顯示,女性在性上面的能力與需求和男性無分軒輊,甚至遠超男性。更令人驚訝的是,女人甚至不需要男人,因為她們透過陰核可以自行達到的性歡愉比異性戀插刺性交更為強烈。甚至,性不再僅僅是主動男性宰制被動女性的場域,而有可能是「對女人的力量和獨立的肯定」(Ehrenreich et. al. 69)。
身體是力量和愉悅的來源,這是一個嶄新的概念,也是全新的女性情慾實踐。馬斯特與瓊生具有實證基礎的研究結論幫助女人肯定她們的性慾需求和探索,也使得女人對性採取比較正面的態度,這對情慾生產力的闊步前進有極為重要的貢獻。不過,當馬斯特與瓊生在肯定女人的性的同時,他們不但熱情的把婚姻視為性的主要場域,也強調女人在性上面的「困擾」應該尋求「專業」的幫助(如性治療門診)而不要在彼此的傾訴敘述中「加重病情」;這麼一來,性的理解和詮釋最終還是被保留在醫學專業權威的手中(Irvine 142)。好在1960年代各種社會運動的集體自我成長風氣使得女人有機會在「意識覺醒」(consciousness-raising)的小組活動中操練自我描述的論述生產,更在交心的敘述中沈澱捕捉自身的經驗感受[28],故而到1976年海蒂(Shere Hite)開始出版她的性學報告時,女人已經累積了足夠的語言和觀察,可以用最肯定的語調和最具體的說明,來對既有的情慾生產關係在她們生活中所造成的嚴重枯竭提出最沈重的抗議。
另一個對新的女性情慾主體有利的發展是,在1960年代性革命之前所有的性論述幾乎都掌握在醫學專家手中,即使是多所鼓勵開放的婚姻手冊也是由醫學專家撰寫;然而從這個歷史時刻開始,有愈來愈多的通俗論述出現,突破性醫學的論述壟斷,而且多半是以教戰手冊的方式教導女性讀者如何主動進行性事以達到最滿意的性生活(Ehrenreich et. al. 81)。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Terry Garrity(筆名是J)1969年出版的《性感的女人》(The Sensuous Woman)。作者以自助手冊的方式實際教導女人如何做充滿情慾、不畏身體享受的女人、如何做好性伴侶、如何展現性魅力、甚至如何口交等等。另外,1971年波士頓女性主義成長團體集體撰寫的醫藥保健及性手冊Our Bodies, Our Selves首度開創由女人經驗出發的身體論述,極力推廣女人的自主選擇和性愛自由,甚至遠超異性戀和婚姻的規範(Seidman, Embattled 46; Snitow et. al. 27)。這些自發的論述都以開朗肯定的語言來談女人和性之間的正面關係,並明確的、按步就班的教導女人如何發現身體,如何自我營造快感,如何累積女性情慾的文化經驗,因而大大的提升了女人涉足情慾的正當性。同時,這類建基於主體經驗的性論述也將性呈現為無數可供個人選擇挪用的具體活動形式,其中包括像從1970年代開始流行的口交(Ehrenreich et. al. 82-87; Grant 120-123),因而使得各種過去並不普及的性活動在交流學習中逐步擴散[29]。更重要的是,當性不再是什麼神奇神祕的身心交融,而被視為是需要經驗和練習的「協商」過程時,女人被賦予了更大的空間來掌控這個活動(Ehrenreich et. al. 90),也因而有機會積極介入情慾生產力的發展。
在這個節骨眼上繼續創造女性讀者以支撐這些情慾讀物的當然是美國的生產體制。由於經濟形態變遷,此刻的女性人力需求已由藍領勞工轉向粉領的秘書文員(Ehrenreich et. al. 54),因就業機會增加而出現的單身粉領階級擁有更獨立的經濟力量和消費形態,因而回過頭來也為資本主義文化生產提供了發展創意以爭取市場利潤的動力。於是1960年代大量出現的單身酒吧、休閒設施、電腦交友中心、各種消費閱讀雜誌等等商業發展,不但為新的單身生活方式提供休閒和社交的硬體軟體,也在這些消費活動中逐步塑造新的單身身分認同,為女人開闢在婚姻之外另一可敬而且可行的人生選擇(Ehrenreich et. al. 60)。建築業也在此時為滿足年輕單身人口的需要而設計出專屬的公寓社區,好讓她們能夠獨立生活甚至開派對而無虞影響父母、鄰居或其他老一倍的人口,這些物質基礎更加鞏固了單身的生活方式(D’Emilio & Freedman 304)。獨立於父母的居住環境當然有利於自主性比較高的親密關係,根據統計,單單在1960到1970年之間,不婚同居的人口就增加了十倍(Seidman, Embattled 39)。這種性生活的安排方式並不是此時才有,但是它們過去在通俗論述中往往被呈現為少數的、可恥的、會有不好下場的,可是此刻在大眾媒體中卻被呈現為新潮的、灑脫的、令人欣羨的;就連硬體空間的安排設計也更方便並肯定這種身體關係的運作。也因為如此,新的、與情慾相關的、以消費為主的單身文化很快就擴散到廣大的中產階級,成為1960年代以後流行的生活方式,其中快速躍進的情慾生產力當然更是遠遠超越婚姻所認可的情慾關係。
在這裡需要一提的是,活躍自在的性生活當然需要可靠方便的避孕措施,1960年開始量產販賣的口服避孕藥早已帶著應許降臨[30];不過,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都很謹慎的強調,口服避孕藥並不像它的批評者所憂心的那樣有力量「創造」性革命;事實上,它只不過合理化(或者說「方便化」)了已經在蓬勃進行中的性革命而已(Ehrenreich et. al. 41)。況且,即使醞釀於優生運動者的理念,成形於充滿種族及階級考量的人體實驗,並且還帶著各種當時尚未發現的副作用,口服避孕藥卻具體標誌了女性對自我身體情慾和人生選擇的輕鬆掌握,徹底的重繪了性別、經濟上的角色分野。當然,身體情慾上的自主自由並不表示女人就萬事如意,但是,就像後來1993年「家庭計畫組織」的執行長談到口服避孕藥時所言:「擁有選擇的權力不等於快樂幸福,但是它至少逼迫女人成長;擁有選擇的權力也不表示人生就一帆風順了,但是它至少使得女人有力量去計畫她的人生。」(Grant 56)。
事實上,性革命昂揚的氣勢也並不依賴口服避孕藥,因為,即使1960年代末期揭露了避孕藥丸可能的副作用之後,女性也並未因此挫折而放棄性革命。相反的,在法國女性主義者西蒙波娃的情慾自主論引導之下,婦女運動轉而以墮胎合法化為主要運動目標,更積極的進一步突破情慾生產關係對婦女身體情慾的束縛(Ehrenreich et. al. 62; Snitow et. al. 18),迫使美國最高法院在1973年作成歷史性的判決,使墮胎合法化,為女人提供另一個自由操控身體的機會。
1960年代情慾生產力最爆炸性的開發,顯然並不僅僅在於開拓各種性觀念與性實踐,也不止於開發新的女性情慾主體。事實上,性革命最令父母師長衛道人士憂心的,是它也把情慾動力賦予了另一個從未在公共論述中與情慾沾上邊的人口群──也就是戰後富裕年代中首度有經濟能力享受休閒的青少年(D’Emilio & Freedman 353)。
各種情慾消費與休閒設施原本就不排斥青少年新近獲得的的經濟消費能力,當時女性主義在思考身體情慾自主權時也非常遠見的把青少女的墮胎權包含在內(Thompson 296),這些歷史條件的際會都或多或少自然化了青少年的情慾發展。另外,在這個年齡層中還有一個最主要的情慾中介,那就是此時開始熱烈普及的搖滾樂,它提供了情慾流動的具體節奏和震耳欲聾的節奏音樂,徹底懸置了成人文化對身體的形塑,動搖了主體已經內化的清晰自我控制,使個體暫時放縱於充滿狂野含意的節奏中。此刻配搭的舞蹈也不再是中產白種成人圓滑優雅的擺動,而是從貧民區黑人舞蹈中學來的抽搐震盪式的抖動,不但抖腿、抖臀、連頭部都在激烈的甩動中帶來暈眩的感覺,快速的節奏和巨大的音響幫助青少年用純粹的身體來體驗並刻劃世界(Fiske 50-51)。這種擺脫文化對身體心靈之銘刻的嘗試,也在當時流行的迷幻藥或大麻吸食中得到具體的出路。搖滾樂、迷幻藥、和自在的性活動相連,形成年輕人口群全面拒斥既有社會文化的標誌,也和情慾生產力的解放互為助力。
同時,伴隨著搖滾樂誕生的巨星偶像也為新的性別形象和性對象開創範例。相對於二次大戰後美國男性的平頭短髮陽剛趨勢,搖滾樂的長髮和緊身褲傳達了中性(雙性)時代的來臨(Ehrenreich et. al. 32),也嚴重的挑戰了傳統的去性(de-sexed)青少年形象。另外,與經濟成長齊頭並進普及的電視媒體更將搖滾樂的具象(搖擺的身體、新潮的穿著、扭曲的身體、情慾的暗示等等)以最明確的方式普及呈現在新一代的青少年眼前,便於他們模仿學習並正當化自己的作為。更引人注目的是,一向被視為柔弱無慾的青少女們在此刻首度形成的偶像文化中成群的尖叫、昏倒、推擠、追跑,以最具體放縱失控的形式來表現她們的情慾感受,歷史學者認為這是女性性革命「最早而最戲劇性的起義」(the first and the most dramatic uprising of women’s sexual revolution)(Ehrenreich et. al. 11)。很明顯的,這種徹底的放棄自持,是對性壓抑的一種強烈抗拒,也使得新一代的女性主體及早開始探索寬廣的心理情緒幅度和自在情慾的表達。
新情慾主體的大量浮現,顯示性革命的能量生產到達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對(性別的、代間的、道德的、身體的、生活方式的)既有文化規範的激烈挑戰,創造了1960年代特有的動盪印象,也把當時情慾生產力和情慾生產關係之間緊張的關係,用最戲劇性的方式呈現在日漸普及具象的影視媒體中,更加強化了性革命的跡象。
V
1960年代情慾解放的傾向顯然是在大氛圍中得到商品文化的全力推波助瀾,然而它最主要的成就卻是在社會運動的反對文化中找到了突破情慾生產關係以及性別體制的力量,並在這個過程中凸顯並挑戰塑造情慾的其他社會軸線。或者,換一個角度來說,社會中各種衝突矛盾的力量和權力軸線總是積極的在情慾戰場上角力的。
事實上,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女性自主理念就是從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和左派社會運動中得到了它最深刻的體認和反省。那些激進社會運動中本來就有大批女性成員在運動過程中累積組織經驗,性革命的風潮鬆動了激進運動的情慾表達,但是也明確的凸顯了性愛關係在種族和性別軸線上的不平等(Echols 29-32)。1960年代中期以後,黑人民權運動的目標在改革牛步慢進和領袖人物(如Martin Luther King, Jr.及Malcolm X)連連遭到暗殺的陰影中,由起初的「族群同化」激化為「黑權」,擁有眾多白人成員的左派運動則相應的在這種種族關係激化的情況中把主要的注意力從民權移至反戰和反徵兵,以避免尷尬。在這樣以男性議題為主的運動趨勢之下,(白種)女性成員在運動中的位置進一步的邊緣化,但是男性成員對她們身體的要求則未嘗稍減(Echols 37-38)。1967年激進的女性成員在進步運動的年會中正式提出了性別不平等的控訴,凸顯了「婦女問題」(The Woman Question)的浮現,但是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1968年,婦女解放升高為女性成員的首要關懷,各個草根的婦解組織在各大城市成立,不但積極找尋自己的理論出路,也在實踐中發展出一系列特有的說法和理念[31]。
這個分裂的舉動顯示,除了在性別歧視方面的體認外,女性成員也在最素樸的身體經驗中意識到,蓬勃開展的情慾生產力極可能有其性別的內涵假設;而女性需要突破這種性別盲點,挑戰既有的性別定位和關係,開拓新的思考空間,才能將性革命改造成女「性」的革命。女人和性之間的關係也因此形成婦女解放運動下一階段的新爭議焦點。
除了情慾的性別軸線之外,激進社會運動在1960年代所創造出來的開放空間中也為性偏好這條軸線提供了浮出的機會,並為邊緣情慾人口的壯大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支撐。早期成立的同性戀聯誼組織逐漸發現自己的溫吞氣質愈來愈不能滿足時代的需求,新一代的年輕同性戀教育程度比較高,政治意識比較強(Faderman 197),她們在其他的激進運動團體中已經學會了活躍的主動出擊策略和經驗,更透過其他弱勢群體的抗爭語言來理解自己和少數民族一樣受到主流社會壓迫,因而發展出帶著強大正當性的強悍氣勢。她們追求的不再是僅僅被接受、被包容,而更是徹底的平權和完整的人權。事實上,著名的1969年石牆暴動事件之所以能快速凝聚同性戀群眾,形成1970年代同性戀解放運動全面出發的契機,正是因為它已經從那個時代各種進步運動所累積的動員策略和抗爭經驗中得到了不可或缺的滋養(Faderman 193-196)。在日常生活實踐方面,嬉皮運動中對於傳統性愛、衣著、道德、生活方式等的挑戰,則為同性戀的自我呈現提供了靈感和掩護,使得整個一代的同性戀得以在比較豐富自由的文化資源中開發自我的形象(Faderman 203)。這種揉合了強悍抗爭和自我壯大的運動經驗,深刻的塑造了後來像「酷兒國族」(Queer Nation)、「女同志國族」(Lesbian Nation)和「酷兒運動」(Queer Movement)之類的運動形式[32],也為開發新的情慾論述和思考打開了視野。1960、1970年代的這些解放運動,普遍提供了自主抗爭的氣勢以及人權至上的論述武器,滋養了被污名的性邊緣人口的解放運動:例如1970年代中期美國的性工作者便由原本積極參與的婦女運動中分出,開始推動伸張妓權的組織,以最肯定自我的強悍姿態挑戰性主流霸權(參看Jennes)。
情慾生產力在1960年代的長足進展隨著進步社會運動對整個社會結構的挑戰而不斷的衝撞既有的情慾生產關係,但是性別、種族、性偏好、階級等因素卻也在情慾生產力的發展中顯現為各種相關議題上的矛盾衝突立場,而當這些立場的對峙遭遇到比較緊縮的歷史條件時,就難免形成對情慾生產力的嚴厲質疑。畢竟,女性主義者宣告退出男性主導的進步運動自成組織時,並沒有就此解決了性別、性偏好、階級、生活經驗等軸線上的差異。
以性傾向為例,1960、1970年代婦女運動的組織和壯大主要是以意識覺醒活動作為互動的場域。在這種成長活動中,個別女性成員透過自身生活經驗的交流和敘述來認識父權的歧視和傷害,也藉此鼓舞反抗的氣勢,鞏固女性的主體性。雖然在傳統的情慾語言中並沒有提供女性主體的發言位置,但是此時的通俗文化中已經出現不少異性戀女性情慾解放的文本,有些女性主義者也在著作中對女性的「性自由」(sexual freedom)抱持高度的肯定(如1970年Germain Greer出版的The Female Eunuch),因此當時確實有機會可能讓情慾經驗透過女性主體的交流而形成智慧和力量的積累。然而與此同時成長的還有女同志運動的主體力量,1970年激進女同性戀團體Radicalesbians在女性主義的基礎上提出「女人認同女人」(woman-identified-woman)的理念,覺得女人應以女人的利益和連結為首要目標,在這種純粹的立場之下,與敵人(男人)共枕變成不可想像的實踐。而當這種強勢的要求持續擴散成為女性主義的新火車頭時(Faderman 212; Snitow et. al. 20),政治正確的光環很快就被原本對情慾開拓有所保留的中產女性主義者接受,將女同志的自我期許接合到異性戀女性的情慾敘述中。這麼一來,既然性愉悅極有可能是可疑的、政治不正確的感受,意識團體中的情慾經驗分享就只能以受害者的敘事情節和情緒出現,以便控訴父權並與(可能來自與男性互動的)愉悅劃清界線(Snitow et. al. 20),保守情慾文化中所提供的豐富受害意象和語言更在此時協助具象化了有關性侵害的一連串揭發和自覺(Grant 207-208; Tieffer 115-116)。[33]
女性成長團體中逐漸浮現的憤怒和無力感透過「奪回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之類的街頭抗爭運動而擴散,也部份的扣連了當時美國大環境中另一些際會的變化情勢[34]。經濟衰退的1970年代創造了美國人不安的心境:政治上,越南戰爭的失利和柬埔寨的失守動搖了美國一貫的世界強國地位;經濟上,石油危機則暴露了美國富裕生活下的薄弱基礎(Seidman, Embattled 62-72)。在這種焦慮的環境中,新右派(New Right)等保守團體於1974年浮上台面,成功的動員媒體,在論述中把這些不利的局勢歸罪於性解放以及其他進步運動帶來的家庭解體和相應的國力衰頹[35](Seidman, Embattled 82-89)。「擁護家庭連線組織」(Pro-Family Coalition)隨即在1970年代末期開始推動「家庭」的單一傳統定義(Trudell 17),各種在此刻應運而生的民意調查於是順著人心的躊躇和不安,重新刻劃單身女性的孤寂空虛和性的危險,把懷舊的家庭意識形態發揮到最高點 (Ehrenreich et. al. 171-179)。
逐步成形的自我懷疑、退縮心態表現為對一切異己和新興變化都深具戒心,在這種氛圍內,性革命所帶來的進步空間首當其衝。1973年才通過的墮胎合法化法案,在四年後就遭到國會通過進一步修法,裁撤醫療制度對墮胎的經費支援,也撤去了好不容易才奪來的女性身體自主權的經濟基礎,腐蝕了婦女運動奮鬥多年的成果(Snitow et. al. 28)。更沈重的打擊是1978年前後,原本已經通過的「性別平權憲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證實無法獲得38州的認定支持,因而無法成為正式的憲法修正案,更加深了婦女運動的挫折感[36]。這種挫折無助的感覺在媒體和保守團體強大的論述攻勢中很容易的就被徵召到「回歸傳統」的陣營中,於是女性成長團體中沈痛控訴父權的能量不但沒有被引導去批判連保守派都已經看到的問題焦點──家庭結構及其所養成的性別權力及性角色分工,反而被聚焦於情慾生產力中最令保守派非議的面向──色情。這個諷刺性的發展當然也有其歷史社會的脈絡。
1970年代初期色情電影工業在開明的社會風氣中蓬勃發展,逐漸脫離短片的形式而模仿主流電影的情節和製作,成為大量發行、普遍可見的成人級劇情長片(Williams 120)。電影科技在影像上的鉅細靡遺呈現,加上色情產品在文化中的高度普及,使得它們輕易的成為爭議的中心,不但引發保守份子的攻擊,其男性觀點也引發某些女性主義者的強烈關注。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認為,雖然經過了1960年代的努力,女人的地位和權力卻一點都沒有改善,仍然是全面遭受剝削壓迫的,在色情材料中就能清楚看到[37];因此,要改變女人的處境就要全面禁除色情。這種關切在這個歷史節點上與保守人士出於道德或宗教理由的批判形成諷刺的合流,反色情的運動因而在1980年代快速壯大,並提供保守份子機會,轉化使用女性主義色情批判的語言來對色情材料全面撻伐(Vance, “Negotiating” 37-38)。可是事實上,面對女性消費能力和情慾角色的變化,1970年代中葉已出現男性脫衣舞的場所,色情影片也已經開始調整腳步以訴求愈來愈活絡的女性情慾主體(Ehrenreich et. al. 111-117)﹔即使許多色情影片仍然纏繞在虐與受虐的主題上,有些成人色情長片卻已經很明確的開始描繪以女性性主體為中心的劇情發展,而不再把女人只當成被使用來滿足男性慾望的性客體(Williams 176)。然而,對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而言,這些都只不過是父權更進一步收編女人、控制女人情慾的作為。換句話說,情慾生產力的任何發展都只不過是男性霸權的進一步擴張而已──因為對她們而言,情慾本身就是「男性權力的社會建構」(a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le power)(MacKinnon 128)。
在此同時,婦女運動之內也因為複雜的歷史原因而出現反挫的現象[38]。1960年代以來性革命所帶來的重大轉變在短短一、二十年間還沒有機會沈澱吸收,就遭遇到美國經濟社會環境惡化以及新右派無情的抹黑打擊;性革命在個人生命以及理論及實踐方面也都還有許多問題,亟待細緻的處理和用心的開拓。比方說,大多數女人在長久調教的情緒和無意識中仍相信女人的力量有限而男人的暴力與權力無限,整個社會的資源分配和價值判斷也繼續認定家庭結構仍然是不可懷疑的社會關係。1981年通過的「家庭保護法」(Family Protection Act)更以控制政府經費補助,來壓制不同於傳統的學校性別教育或同性戀家庭組合(D’Emilio & Freedman 349),以致於在性別關係上越出常軌的個人(特別是女人)常常面對極大的困苦孤立,要不就只好選擇回歸家庭(Willis, No More125-127)。面對整體環境的緊縮和女性個人生活中的困難抉擇,從1980年代開始,在女性主義陣營中就有反挫的跡象,不少著名的女性主義者公開拋棄原來對一夫一妻家庭體制及其不平等權力結構的徹底批判,重新擁抱(此刻被媒體大量凸顯美化的)家庭和它一向所代表的溫暖[39],認為家庭的某種有機完整性是深植在個人心中而無法動搖的。她們也放棄早先自由開放的性主張,轉而認為女性主義不應該用太激進的理念得罪太多男人或女人,而應該拾回原來的傳統性別分野和母性角色,並且認為比較有效的社會變革方式是用女人的特有溫婉風格和氣質去改變公領域中的真實政治(Stacey 210-221)。
婦女運動之內對性的「政治正確」要求、甚或從改變「性部署」的努力中退卻,以及婦女運動對外的強烈反色情立場,都一再縮小婦女解放的運動和論述空間。在另一方面,另一些女性主義者和女同性戀則深深覺得進步運動不能放棄情慾生產力所可能帶來的自由和自主動力,也不能放棄對一夫一妻異性戀婚姻體制的持續批判──特別是在雷根政權上台後所代表的保守氛圍之內。於是1982年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Barnard College舉辦的”Toward a Politics of Sexuality”學術會議點燃了女性主義的性辯論,凝聚了女性主義性激進派(sex radicals)多樣多元的性觀點[40],繼續向女性所受到的的傳統情慾社會調教(erotic socialization)挑戰。從S/M的性角色扮演、到女同性戀色情材料、到性對象的多元發展、到禁忌的性愛活動,性激進派的現身及論述生產使得這些邊緣的情慾形式得以出線擴散,也為新的性主體創造集結和組織的動力(Seidman, Embattled 146),將繼續蓬勃發展的情慾生產力積極導向挑戰情慾生產關係的方向。
映著1980年代背景中逐漸加大的愛滋病陰影以及它對邊緣和多元性主體的抹黑恐嚇,性激進派在謹慎中繼續性革命已經開創的情慾空間和選擇,在愛滋的現實中重新思考性的實踐與意義,更在愛滋病所衍生的各種醫療和服務中強悍的對抗其中隱含的性歧視和性壓迫(參考Patton)。事實上,1980年代以來美國資本主義文化生產被迫愈來愈唱和保守的道德觀,除了媒體中繼續刻劃性的虛幻和危險之外,在面對青少年的性探索時,國家機器也得到成人的充分授權而將性教育課程廣泛的進駐校園,更加普及性的意識。可惜其中主要的語言仍是延遲加恐嚇加危險,性革命中逐漸浮出的女性情慾仍然被壓抑醜化(Fine 32-45);性雖然已經成為大眾常識中的基本思考面向,然而它也時刻遭受強大的監控。在這個時刻,也還只有那些邊緣的、另類的情慾運動主體(例如性激進派、同性戀、雙性戀、酷兒、跨性別等)在公共論述的場域中繼續轉化資本主義情慾生產力的衝撞力,繼續活絡使用性革命的豐富遺產,拒絕讓情慾生產關係緊縮空間,拒絕讓一夫一妻的異性戀婚姻壟斷情慾的合法園地。
1980年代以來,美國的經濟衰退和新右派所形成的社會緊縮心態互相搭配,或許不太有利於情慾生產力的大幅發展,但是新的邊緣情慾主體仍然不停的在抗爭中浮現,新的情慾爭議也使得性的疆界和部署時時流動擴張;更重要的是,此刻的情慾地平線已經大大不同於往日。回歸婚姻和家庭的保守呼聲雖然似乎仍然甚囂塵上,但是人們在進入婚姻之前絕大多數已經有了豐富的性經驗和性資訊,性變成了個人成長過程中必須而且不斷進行的活動,這些性經驗也使得女人有了更多能力來協商自己身體的主權,家庭的結構和組成實驗著各種新的面貌,性別的角色和功能都有了新的定義,婚外情慾活動更是頻繁而多樣,生殖科技的突飛猛進使得性和生殖功能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通訊科技則使得性的資訊和人際連結方式更廣泛的流傳。從青少年到老年,情慾再也不是什麼遙不可及的奢侈(D’Emilio & Freedman 333-338)。
換句話說,1960年代以來持續進行的性革命或許在某些人的論述中被劃歸為過時,被通俗的觀點視為錯誤,更被保守派宣告死亡;但是,性革命所創造的新世界卻是此刻任何情慾實踐和理念的新基點;情慾文化的任何進一步(或退一步)發展也都必須從這個基點和其所創造的權力佈局和人生可能上開始協商。「令人深思的是,至少西方世界已經對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性解放風氣重新進行了不少評估,但是這個重新評估也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儘管那個年代有其過度放縱以及不容置疑的性別歧視,但是它所達成的進展是值得保存的」(Altman 105)。
回顧1960年代開始的性革命,女性主義者有著矛盾複雜的情緒。不過,就像妙麗.戴門(Muriel Dimen)說的:
性當然不是革命的唯一之路,但是它是塑造慾望的主要力量,而我們對慾望的限制往往直接導致了自我否定和社會虛偽。說實在的,我們的問題不是慾望太多而是慾望太少;我們的無力反叛以及未完成的革命都根植於性壓抑對慾望的壓迫,而正是這種性壓迫截斷了一切希望。1960年代反對文化中那種呼求解放慾望的烏托邦狂想,現在在左派及女性主義者中間都不再流行了;我們好像已經應該長大了,不應該再眼睛大、肚皮小了。可是這種時髦的「成熟」恐怕根本沒認清楚慾望的本質,那就是:不管慾望多麼痛苦,不管慾望看起來多愚蠢,多貪心,我們都需要盡力的想望。我們或許得不到想要的一切,但是只有繼續想望我們所能想像的,我們才可能得到我們所需要的(Dimen 48-49)。
VI
以上的敘述為性革命──甚至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的理論補充了一些思考方向。我認為簡單的說勞動民主和經濟能力的發展促成了性的發展,因而造成對婚姻體制的衝擊,甚至形成性革命;或者太輕蔑的漠視性革命的重要性,或者太快的斷言性革命的必然方向或結果──都漠視了性領域中的複雜動力學。歷史顯示,資本主義本身的擴張已經具體的帶動了情慾作為商品生產和消費的一部份,勞動人口的流動、休閒文化、媒體及廣告、性別角色的變遷、消費道德所滲透的情慾享受心態、青少年次文化等等方面的快速發展,都已經大幅提升了情慾生產力[41],再加上進步社會運動和現代性學的某些論述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各種交戰施力,這些風雲際會都為情慾生產關係的動盪提供了更多的變數。
性行為、性論述、性認同、性商品、性模式的多樣化以及它們在再現和論述領域中的明顯可見度,這正是性革命昂首前進的徵兆,也是性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動盪變化的時刻。而什麼樣的介入能夠更進一步壯大情慾生產力,激化它與當下情慾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或者換個方式說,就是徹底改變情慾的生產關係,駕馭資本主義生產所帶來的情慾生產力擴張,使得情慾生產關係更加多元、開放、平等、流動──這恐怕是所有進步的運動者需要思考的問題。[42]
由歷史的先例來看,性革命帶來的當然並不見得一定是情慾生產力的全面解放,性革命也不一定保障情慾受壓迫者的全面翻身,情慾體制總是以各種方式繼續吸收改變的動力。但是,只要有進步運動的介入,有抗爭,就至少「改變了辯論的條件」(Willis, “Foreword” viii),也就是改變了壓迫和鬥爭的條件及局勢。美國百年來的兩次性革命都因著各種進步運動的積極挪用和轉化,為多元情慾主體創造了此刻以及下一階段抗爭的資源動力,這些介入和抗爭不但使得女人、青少年、同性戀及其他性多元人士等等情慾受到壓迫的主體,有機會在動盪的社會條件和結構中尋求抗爭的機會和可能,更重要的是,不管此刻的抗爭形成了多少進展,下一階段的女人、青少年、同性戀、性多元人士等等受到壓迫的主體至少不必從原點開始,而可以在新的思考和實踐的基礎上前進。可惜許多進步人士總是輕看情慾領域中的抗爭而看不見它對徹底的社會變革的重要性,在這一方面,佛洛伊德-馬克思主義者賴希倒有不少洞見可以供我們思考。
賴希對情慾革命的關切並不是對馬克思革命論的教條式套用,而是來自於他對蘇聯1920年代性革命的反省 [43]。當時許多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者總認為經濟領域有關「生產」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徹底的革命,而其他領域(如性別或情慾方面)的變革充其量也只是從屬的、片面的、奢侈的、不太重要的;因此這些人對經濟生產以外的社會脈動抱持著漫不經心的態度,或者用各種階級色彩的大帽子來扣它們(Reich, The Sexual 160)。但是賴希相信,革命不能忽略存在在群眾心理中的「歷史的主觀因素」(subjective factor of history)(Reich, The Sexual 174),因為這種心理狀態──也就是在一夫一妻父權情慾生產關係中養成的情慾匱乏狀態和威權人格──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革命的動力,而且這個心理情慾的結構並不完全隨同經濟力起舞,而是形成「一個影響經濟和社會的獨立力量」(Reich, The Sexual 188),甚至可以左右一個革命的走向。「父權家庭為所有建立在威權原則上的社會秩序提供了一個結構的和意識形態的繁殖地」(Reich, The Sexual 161),因此在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家庭情慾結構一定是一個重要的改造節點 [44]。
從理論的角度來說,賴希在社會革命的架構內首度認識到情慾(性)的物質性(the materiality of sexuality),以及物質的情慾基礎(the erotic/sexual basis of the material),複雜化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生產力(下層建築)和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的截然二元分野 [45]。賴希嚴正的指出,「一個社會的情慾過程(sexual process)一向就是其文化過程(cultural process)的核心」,也就是再生產(reproduction)的核心。換言之,情慾領域中的革命就是再生產的革命;「性革命就是社會文化重新結構(re-structuring)的客觀表現」(Reich, The Sexual 160),而父權家庭及其相關的人格心理情感情慾絕對是這個革命的主要場域。
換句話說,以蘇聯的性革命為例,賴希認為是強烈的家庭情感影響了革命的執行者,因而使得革命的果效無法全面展開;這個深刻的認識也為我們思考美國百年來的性革命提供寶貴的洞見。畢竟,新的社會連結方式總是新的、剛建立的、尚未生根的、有待體現落實的,可是原有的家庭情感及其構成的人格結構卻是根植於日常的每日生活活動儀式中,每一個習慣動作及情緒反應都可能促進並鞏固主體在原有社會結構中形成的自我定位。因此,一個革命的真正效應除了改變社會的經濟結構之外,一定要改變其人格結構的再生產方式,改變那些維繫現有人格心理運作的日常生活與慣常反應,也就是改變養成這些日常生活與慣常反應模式的一夫一妻異性戀婚姻家庭結構。賴希甚至明確的指出,革命的效應不是由它建立了多少新的立法而定,而是由人民是否經驗到嶄新的、革命的生活方式和內容而定(Reich, The Sexual 174)。因此,社會革命不能只是經濟與政治層面的重組,它必然要包含人格結構和和情慾心理的重組,才不至於一時進步,終究倒退。可惜蘇聯的革命政府並沒有意識到這個深刻的意義,反而用階級的帽子扣上推動性革命的努力,使得蘇聯的整個革命功敗垂成。因此賴希才會沈痛的說:「真正的悲劇就是當革命運動開始維護反動的、庸俗的觀點,並稱呼性革命者為『小資產階級』的時候」(Reich, The Sexual 160)。
賴希在1920年代蘇聯性革命反挫的例子中所學到的寶貴功課是:性革命決不只是相關現有既存的、已經帶著各種文化人格心理包袱的抗爭主體及其實踐,更重要的是如何切斷體制再生產自我的管道,也就是解放一夫一妻家庭的情慾壓抑,挑戰此刻的性部署及其中的權力關係,積極改造並生產未來將承擔體制的新生主體。在這個層次上,性革命構成了所有社會革命的情慾/物質基礎。
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全面擴展當然會包含了情慾生產力的拓展和性意識的擴散普及,這個新開發出來的動力和空間也當然有可能如傅柯所言使得性的權力部署更加細緻化;但是對抗這個趨勢的策略絕不是開歷史的倒車,努力回復情慾白色恐怖的禁絕狀態,而是要像傅柯一再強調的,去挖掘串連已經存在的零散的抗爭點,平反被壓抑的知識和論述(subjugated knowledges and discourses),暴露性部署的鬆散和矛盾。
這也就是說,情慾生產力能否為情慾上受到壓迫的主體形成抗爭式的支援?能否徹底的改造既有情慾生產關係的單一及權力不平等?能否被串連起來搖撼迂迴相連的其他壓迫關係?這些都還要看運動者如何像本文中所提到的進步運動一樣積極挪用並轉化資本主義的情慾生產力,如何呵護那些已經在此刻片面或局部突破情慾生產關係的畸零主體以擴散她們攪擾體制的效應和力量,如何積極介入通俗媒體中不斷複頌的情慾常識、家庭意識形態中的性養成、青少年次文化的情慾實踐、性與家庭的相關法律及制度常規、性領域中的性別歧視和階級歧視、性(醫)學及性(心理)研究等學術及論述生產、以及在現階段愈來愈強大的知識/權力場域中形成的性教育 [46]。
如果說台灣現階段澎湃進行的性革命有機會為情慾弱勢創造什麼發展的空間,開拓什麼情慾方面的資源,改變什麼現有的不平等分配,那麼,對性革命的歷史和理論進程的活絡認識和詮釋,實在是此刻迫不及待的工作。
註
[1] 研究者一向就注意到,賴希晚年大量修訂其早年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因此對於了解他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困難;但是基本上,賴希嘗試融合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倒是不爭的事實。賴希覺得個人心理問題有其社會源頭,同時,他也覺得精神分析理論只在個人範疇之內打轉,沒有看見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在個人的性生活和性態度甚至人格結構上具體的操作以便再生產適合本身需求的勞動力,故而需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來顯示社會組織方式對個人心理的細緻塑造。但是賴希又覺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只有宏觀的眼界,而沒有思考在社會條件中形成的個人心理和情慾結構如何阻礙、或延緩、或有助於社會生產的操作以及再生產體制的維繫,故而也需要精神分析的理論來實地檢視社會文化在個人心理中的沈澱如何反過來使得生產模式得以成為可能。由於這個關切,賴希才對1920年代歐洲及蘇聯的性文化變革充滿興趣,期望了解其中各種力量的運作。本文在此沿用的是1945年出版的英文版《性革命》。
[2] 賴希在這裡的分析當然不是說所有的家庭都經歷了這些衝擊(個別家庭和個人當然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變遷發展),而是說整體的社會結構中有這些新的趨勢和現象。
[3] 賴希認為美國的婚姻制度崩解速度最快,是因為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最高,因而在「情慾經濟」(sex-economy)上創造了最大的矛盾:一邊是高度嚴格要求禁慾的清教徒精神,另一邊卻是強制性道德(compulsory morality)在社會變遷中的逐步崩潰。事實上,賴希也暗示,清教徒式的情慾生產關係正是被強制道德所壓制不住的情慾生產力衝垮的(Reich, The Sexual 142)。
[4] 有些學者質疑「性革命」的說法,認為「革命」包含了一個前傅柯式的歷史發展觀念(Seidman, Embattled 22)。但是連質疑者也都承認,使用「革命」這樣的語言,並不一定要包含什麼實證式的全面翻轉現象,而可能只是代表了性的多樣化和多元化,而且在動員群眾、創造反叛的象徵上,有其重要的修辭策略的意義(Seidman, Embattled 21)。我個人的閱讀認為,傅柯雖然強調抗爭點的零散、流動和短暫,但是他也承認有巨大激進的翻轉可能:「毫無疑問的,是那些﹝散見於社會階層和個人生活中的﹞抗爭點被策略性的串連符碼化,使得革命成為可能」(Foucault 96)。而我認為所謂社會革命就正是要創造並實現那個可能,因此本文對美國百年來性革命的「重新描寫」(redescription)並不在於「發掘歷史的真相」──那些言之鑿鑿說性革命是不可能的空想、已經被女人視為錯誤而唾棄、美國人現在傾向回歸家庭之類的斷言,倒常常宣稱自己是知道「歷史真相」的。我的立場比較靠近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Richard Rorty:現實總是在論述中被經驗、被建構的,而任何描述都只是發言者所選擇的隱喻(chosen metaphoric)(Rorty 39),也因此只不過呈現了發言者引以理解和建構世界的角度而已。而我們之所以不斷重寫歷史、重述現實,正在於開拓另類描述的空間,也就是以「自我創造」(self-creation)的隱喻來取代「發現史實」(discovery)的隱喻(Rorty 40)。
[5] 在這裡,我的語言有可能使讀者誤以為這兩個概念也有某些單一本質(monolithic),不過我在下面的歷史分析中會具體顯示,美國歷史上兩次性革命是由愈來愈複雜的運作因素和力量促成的。在這篇論文中,情慾生產力和情慾生產關係將只是一組啟發性(heuristic)的工具,以幫助我們串連各種敵意以及各類與性體制矛盾的實踐,以形成對立或反對陣線,並且和馬克思主義論述串連。
[6] 關於「性部署」的觀念,參考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1980),特別是第四部份的後面兩章。我在這裡所提出的動態分析事實上正希望重新轉化庸俗馬克思主義者的物質基礎(所謂下層建築)/意識形態(所謂上層建築)二元分野。
[7] 如D’Emilio & Freedman, Epstein, Faderman, 和Seidman。
[8] 這兩次「性革命」所涵蓋的層面當然包含了「性」和「性別」方面的各種變遷,本文將比較聚焦於性領域內的變化,而以性別為背景。
[9] 事實上,也只有那些自我定位為場外裁判的人才會熱衷於用一竿子打翻船的方式來評斷一個運動或思想革命是「失敗」(或「成功」)的──彷彿一旦決定了功過,就可以把其中的一切抹上本質主義式的色彩,然後輕易的全面拒斥(或全心擁抱)個中的一切。可是,就社會運動、就改變世界的出發點而言,真正要關心的恐怕應該是如何去轉化使用串連那個運動或思想革命中的各種論述或歷史資源,以操作此刻的意識形態場域,擴大此刻的運動能量。
[10] 研究性與生產模式在西方社會中互動關係的許多學者都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大量擴散之前,家庭的結構和功能是經濟的;也就是說,每一個家庭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勞動的生產活動絕大部分在家庭之內進行,因此性別分工並不十分明顯,家庭成員合作生產每日所需,互相依賴存在。這種生產體制並沒有提供在家庭之外的其他謀生方式,因而使得個人的人生選擇十分有限,情慾活動的模式局限於維繫這樣的家庭和生產模式,也就是局限於服務婚姻,而由家長全權決定。性和婚內生殖密不可分,因為那是唯一可能大幅增加勞動力也就是增加家庭財富積累的方式。歷經17、18、19世紀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把許多勞動生產活動移至家庭之外,提供了雇傭勞動的機會,家庭成員因而被吸引離開了原本自給自足但此刻在生產力競爭中居於劣勢的家庭生產模式。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減弱,女人在家庭中的工作窄化至子女之照養,同時,幼年人口的經濟貢獻力因著勞動的職業化而延後或減弱,生育子女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這些發展都可以部分解釋19世紀末對節育的關注。事實上,學者認為到了20世紀初,家庭的經濟功能已被其情感功能取代,因此性也不再局限於生殖功能之內了(D’Emilio 6-7; Epstein 156-158; Reich, The Sexual 135)。
[11] 有些遊樂設施的廣告詞明白的宣告其情慾性質。例如,「愛之桶」的廣告詞說:「聽過小木屋賓館嗎?「愛之桶」比它浪漫十倍!」(意譯)。「炮彈飛車」的廣告詞說;「她會大聲尖叫,飛身躲入你懷中嗎?是的!一定會!」(D’Emilio & Freedman 196)。
[12] 值得注意的是,D’Emilio and Freedman在敘述主體在情慾實踐力上的差異時,並沒有以區分高下的方式來斷言階級因素全面決定了情慾滿足的程度,也沒有斷言當時的情慾生產力擴張對中產女人比較有利因此不值得推廣等等。階級(以及另外許多因素,如婚姻狀態、居住區域、家中排行、相貌身材、年齡輩分等)當然會影響到情慾資本的大小與運用﹔正如它在教育、就業、高普考等等方面也同樣會影響個別主體施力的機會與結果。但是我們需要反省的是:為什麼許多人面對主體的階級差異,仍然對各種方面的解放運動熱情支援,不遺餘力,卻唯獨對情慾領域的解放運動特別有保留,而且時刻祭出階級差異來勸說大家駐足不前?「忌性(sex-negative)文化」(Reich, The Sexual 25; Rubin 11)和「情慾沙文主義」(Rubin 32)在這一點上的同時運作,值得運動者進一步反省。
[13] 世紀之交的情慾革命可以從另一個跡象觀察到。金賽的性學研究顯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男人在婚姻體制之外的情慾出路多半只有找妓女,但是戰後的現象是,男人轉向非妓女的比例大幅擴張(Kinsey et. al. 300),不再嚴守情慾規範的20年代女人甚至贏得了「新女人」(New Woman)的封號(D’Emilio & Freedman 190)。
[14] 不少歷史觀察者都指出同性戀身分在此刻浮現(Bullough 177; Weeks 90),但是我在此處更關心的是階級、性別與認同身分在此時刻的匯集發展。
[15] 節育從19世紀起就一直是個引發焦慮的社會議題,因為各種節育的措施不但意味著人口的減少,更意味著女人首次有了機會決定自己的生命有多大一部分要投注到養兒育女的事業或者其他的人生目標上。這種蘊含自主能力的選擇權不論對男人或女人而言都是一大挑戰(Epstein 158-159)。
[16] 德國的著名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就曾在1913年呼籲工人進行「生育罷工」,以全面拒絕生產新的工人來抗拒資本家對工人的壓迫(Asbell 30)。
[17] 這種優生的考量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納粹對猶太人的滅種罪行被揭露,才逐漸在許多中產人士中減弱,繼之而起的節育說詞就變成了所謂的「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Grant 42)。
[18] 美國本土生產性學研究的男女醫學人士包括Katherine Bement Davis, Prince A. Morrow, Gilbert V. Hamilton, Latou Dickinson, Clielia Mosher, Max J. Exner等(參見Bullough)。另外,同一時間之內,透過中產婦女的支持,專業的婦產醫學也逐步取代傳統的產婆,把女人的生育過程醫療化,從家庭和社區移往專業空間中(如醫院)。這個醫療權的爭奪戰牽涉到複雜的階級和種族問題,也凸顯了性革命的複雜動力學(Riessman 126-130)。
[19] 這些性學家對於性的熱情正面描述使得評論者都稱呼他們為「性狂熱份子」(sexual enthusiasts)(Robinson 3),可見他們在性學領域中的突破性絕不亞於那些積極抗爭既有體制的社會運動者。
[20] 1918年Marie Stopes推出Married Love,1926年Theodoor Hendrik van de Velde在德國和荷蘭同時推出Ideal Marriage,兩本都在美國成為暢銷而且長銷的婚姻手冊。
[21] 1920年代歐洲各國進步人士也曾透過各種性改革的組織,如「性改革世界聯盟」及「德國保護母親暨性改革協會」,來推動性道德及文化革新,其中還包括蘇聯1917年革命之後,新社會對墮胎和同性戀的諸多開放、對婦女經濟地位的改善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的鬆弛、對青少年和兒童性教育的創新學程等等新措施及政策。1920年代歐洲的性革命承襲了當時左翼的進步思潮,把性視為社會文化的物質基礎之一,也因而把性改革當成社會改革的重要環節,宣稱追求更公義、更理性、更現代的性道德與性文化,以減輕強制式的禁慾為個人生活帶來的痛苦壓抑,並消除雙重標準的偽善式性道德在社會中造成的惡果(如嫖妓、性病等等)。對同時期的賴希而言,1920年代歐洲各國的性改革運動者雖然有其進步性,也具體的為消除非理性的性道德壓迫盡過心力,但是,賴希堅定的指出,這些性改革運動者注定走不了多遠,因為他們共同有一盲點:他們都還死守婚姻制度為最後底線:換句話說,性改革者只希望在不動搖婚姻制度的前提之下,對當時的性道德做局部的改革,以建立一個新的、比較理性的新道德秩序,她們所作的努力充其量只是調整了婚姻的內容和性質以保存婚姻體制而已(Reich, The Sexual 52-73; 亦可參考Seidman, Romantic 73-81)。
[22] 例如,就業機會的緊縮使得許多女同性戀在經濟上無法單身獨立生活而被迫進入異性戀婚姻,可是同時有些女同性戀也策略的調整情慾生活,以某種雙性戀式的妥協模式來維繫自己的同性戀身分(Faderman 95)。
[23] 內分泌方面的研究動力,很大一部分來自對繁衍生殖過程的關注,還有一部分則來自男性醫學人士對恢復自身男性雄風的個人興趣(Bullough 125-126)。
[24] 二次大戰後,國家安全成為首要考量,右派份子如參議員麥卡錫等人利用恐共心理,對許多政治異議份子大加迫害,例如1954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獲悉金賽的性研究中心遭受調查之後就立刻終止了對金賽的經費補助(Segal, Straight 88)。這種氛圍對同性戀等性異議份子亦不放鬆,1947到1950年間軍隊和政府單位中就開除了將近五千名同性戀身分的員工(Faderman 140),艾森豪總統並且在1953年下令,以後政府的雇傭程序中必須查明申請者的性偏好取向.冷戰階段中社會大眾的不安心理遂以排擠異己作為紓解,造成了對同性戀極為不利的社會氛圍(D’Emilio & Freedman 291)。不過,同性戀仍在如此的劣勢中推動自我意識和認同,左派同性戀就在此時成立The Mattachine Society,女同性戀則組成了Daughters of Bilitis的聯誼組織,作為下一階段運動組織的前身。
[25] 過去有許多女性主義者對這個趨勢的詮釋是:花花公子哲學為男人提供了逃避家庭責任的藉口,這對女人絕對是百害而無一利。然而這個詮釋沒有思考的是,如果女人要打破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和家庭體制,開拓新的人生道路,那麼她們對那些已經在拒絕支撐家庭體制的做法──包括女人逃家(不婚、出軌、第三者)或男人不養家(外遇、離婚)——也必須有更細緻複雜的分析,而不能一竿子打翻船的全面加以批判。
[26] 歷史學家認為1960年代性革命的號角是由兩本重要的女性著作吹響的。其中較為女性主義者樂道的是1963年Betty Friedan憤慨描繪中產家庭主婦生命荒原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另外一本就是這裡所說的、更早一年出版而且輕鬆決斷的一舉將婚姻及女性迷思徹底撇棄的《性與單身女郎》(Ehrenreich et. al. 56)。
[27] 1950年代初的冷戰高峰是美蘇之間在古巴的劍拔弩張,末期則轉為兩國的太空爭霸戰。1957年蘇聯成功的發射Sputnik太空船,美國驚覺落後遂投入大量經費和獎助學金來補助大學的擴張,希冀透過教育來提升競爭力。這個「教育的民主化」為原本與高等教育無緣的女性和少數民族成員開闢了自主自立的道路(Faderman 197)。
[28] 「意識覺醒」這個名詞是紐約市左翼女性主義者Kathie Sarachild所創,但是這種活動的靈感來源則是1950年代全球反帝、反殖運動中發展出來提升人民自覺的團體活動;Sarachild曾經參加過的民權運動在南方黑人群眾中就曾有「細訴真相」(tell it like it is)的做法,中共在農民中則推動過「憶苦思甜」,瓜地馬拉革命游擊隊也使用過類似策略來提升群眾意識(Echols 83-84)。
[29] 此刻另外兩本以通俗語言撰寫的經典著作則是Alex Comfort的The Joy of Sex(1972)以及Nancy Friday的My Secret Garden(1973),前者以豐富露骨的圖片和明確的文字描繪,具體教導讀者如何創意的享受性愛,後者則展現了女性性幻想的狂野和主動,直逼任何社會的道德禁忌。這類著作的風行都宣告了性醫學再也不能壟斷性的論述。
[30] 口服避孕藥的研究和實驗推廣過程充滿了歷史的偶然和意外發展,可參考Bernard Asbell, The Pill: A Biography of the Drug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以及Linda Grant, Sexing the Millennium: Women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1994),第3章。
[31] 例如前面提過的「意識覺醒」(consciousness-raising)活動,目的在透過個人的經驗敘述來發展階級意識和姊妹情誼。她們相信女人的覺醒不是用什麼理性或教條的教育來認識女人的處境,而是透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麼一來,「一般人民的智慧」既然高過別的運動(特別是美國當時由男性主導的進步運動)已經建立的理念,那麼就需要盡量鼓勵個人提供經驗,集結以作為知識的基礎。這個做法後來也被同性戀解放運動採用,作為壯大主體的活動形式(Echols 82-85)。
[32] 這方面的分析可參考Faderman (215-245)及Smyth。
[33] 可惜,後來主流女性主義運動的抗爭似乎只以父權的暴力侵害作為目標,而對女性情慾空間疏於耕耘,甚至對其他女性自發在此領域中的開拓都加以質疑或妖魔化。
[34] 1960年代逍遙探索的那一代年輕人在1970年代已成為必須面對現實生活的青、中年人,她們之中有許多人已經有了穩定的社會地位和成就,或者想要結婚但找不到可以共同建立平等關係的伴侶,想要生育後代而已經晃過了生育的年齡。不同的年齡及其相應的社會角色,使得許多人的心態起了轉變(Stacey 227)。而不巧的是,她們所面對的美國現實正好是1970年代後期的危機四伏和挫敗連連,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後來雷根保守政權對這些人產生了廣泛的吸引力。
[35] 1980年代前後出現了一大批擁護家庭、回歸家庭的作品,把女性主義者刻劃為肇始家庭解體的元兇,例如Berger & Berger及Kramer。言論風氣所及,甚至有些左派學者也有相同的論調,例如Illich及Lasch。
[36] 在這些發展過程中,基進的左派女性主義者已經意識到婦女解放運動的中產化。因為此時的「婦女解放運動」已成了「婦女運動」(Women’s Movement),「女性主義變成了一種改良主義的政治」(Willis, No More 118)﹔原本高舉女性情慾自由和女性自決的首要議題──墮胎權──也已經在運動的語言中變成了溫和的「人生選擇」之說(choice)(Willis, “Foreword” 7)﹔而要求女性得力壯大並且對體制進行全面集體的抗爭,變成了一系列自我救援式的療傷組織,例如強暴救援及輔導中心、家庭暴力受害女人的中途之家、女人的健康診所等等。雖然這些機構有其及時救助個人的重要性,但是它們需要長期的支援和經營,更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資源,而在這些方面都必須仰賴對女性議題不一定友善的國家機器。在這樣的低迷氣氛中,當性傷害層出不窮,社會環境的改造速度有如牛步時,各種來自父權社會的反挫和來自女人本身的喪志,都使得性革命的脈動受到極大的耗損。
[37] 有意思的是,領導反色情運動的主要是白種中產女性,而非那些在體制中受害最深的少數族裔女性(Segal, Straight 62)。
[38] Susan Faludi的《反挫:誰與女人為敵?》(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就記錄了許多這方面的跡象。
[39] 例如Betty Friedan, The Second Stage (New York: Summit, 1981)和Germain Greer, Sex and Destiny: The Politics of Human Ferti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4).
[40] 這個會議的相關論文可參看由Carole S. Vance編的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41]僅以台灣電視上以情慾為主題的論述節目而言,從90年代初中規中矩的的「女人女人」,到有線電視開發之後所帶來的情慾現象脫口秀「邊緣對話」、「情色邊緣」,中下階層情慾綜藝節目「性不性由你」,或者是醫學專家主持的「知性量販店」,到最近一波的中產主流情慾綜藝節目「紅色炸彈」以及「非常男女」(兩個節目後來都在輿論壓力下改為以相親為主的節目取向),再加上偶而引介邊緣情慾人口的「男女雙峰會」,以同志為訴求對象的「同志come out」等,甚至結合情慾、商品、異色對話的「花魁藝色館」,更不用說解碼台全天播放及其他頻道在午夜之後播放的情色影片,這些節目顯示台灣的情慾生產力已經在大眾媒體中打下可觀的園地,為情慾生產力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
[42] 頁: 24
反觀本土,二十世紀九零年代台灣社會的情慾面向是複雜矛盾的。原本最主要規範情慾的婚姻關係及貞操觀念已進入崩解的危機,婚前性行為、外遇、多重性伴侶、未婚懷孕、同性戀、色情等等「越軌」情慾,似乎已經普及到了一個臨界點,原本在個別生命中不能為人所知的祕密情慾,逐步以集中的方式具體呈現為處處可見的賓館,沈默但觸目驚心的宣告了情慾的狂潮。同時,原本在朋友之間的口耳相傳和閒言閒語,也開始在媒體和學術甚至常識領域中凝聚成相關的正式論述,透過這些現象的社會分析、統計數據、翻譯的自白等等形式,來理解譴責預防解決日漸凸顯的情慾出軌現象。
[43] 蘇聯在1917年革命之後,曾經嘗試推行一連串性革命的措施來改變有關婚姻、離婚、節育、同性戀、青少年生活、及兒童教養的社會實踐。以當時的歷史眼界而言是十分進步的做法,可惜沒有多久就在各方守成勢力之下倒退,賴希在《性革命》的後半段對這一段歷史有頗為沈痛的檢討和分析。他認為當時有很多人抱持著非常簡單的經濟觀點,「以為隨著資產階級的敗亡和蘇聯新頒佈的性立法,性革命就『已經完成大業』,或者只要無產階級一掌權,性的問題就自然的解決了」(Reich, The Sexual 187)。賴希認為這些人的大錯誤正在於他們只看重立法,而忽略了情慾領域的(半)自主性:「任何對歷史發展所作的研究,只要它以為群眾的心理狀態僅僅不過是經濟過程的產物(product),而沒有認識到這些心理狀態也同時是經濟過程的動力(motive force),那麼這種研究還算不上是有革命眼光的」(斜體字為本文作者所強調的;Reich, The Sexual 174)。
[44] 就1980年代以來性/別解放運動所遭遇的挫折來看,家庭顯然還是最重要的爭戰場域,情慾革命的果效似乎與家庭結構的革命息息相關。傅柯曾特別指出,從18世紀以來,家庭單元就是「性部署」的最主要場域,包括女性身體、兒童性、生育、及各種變態等等主要的性軸線部署策略,都在家庭中的「夫妻」和「親子」兩個面向上找到它們最堅實的支撐:「性的專屬發展場域就是家庭」(Foucault 108)。傅柯的興趣是在高度抽象的層次上指出「性部署」在家庭中運作所形成的各種矛盾張力,如亂倫禁忌與情慾灌注的共生;但是家庭「性化」的內容和結果在個人具體心理的層次上倒底是何面貌,這樣的主體形塑對社會運動又有什麼影響,傅柯並未處理。在這方面,我們倒可以由賴希的性革命論得到一些啟示。賴希並不是籠統抽象的宣告性慾的社會形成,而是更深一層由微觀的角度指出,一夫一妻父權婚姻家庭中的管教式情慾調教根本無助於主體快感能力(orgasmic potency)的養成,也因而無助於愉悅開放的人格養成。賴希在研究當時甚囂塵上的法西斯心態時,逐漸認識到一夫一妻婚姻家庭是促使個人快感能力薄弱、情慾經驗匱乏、以致於無力創造愉悅而只能養成權威人格的主要場域(Reich, The Sexual 95)。賴希指出,一個強烈(而且強迫)要求婚前貞潔和婚後忠貞的一夫一妻家庭,事實上正是威權體制的縮影,也是養成權威人格的溫床(Reich, The Sexual 75-82),在這種家庭中運作的最主要權力關係是伴隨資本主義而發展出來的「身體私有制」以及按著父權邏輯來執行的「父親權威制」。「身體私有制」使得夫妻之間強制排他的性交關係在實質上早已喪失自發的性和愉悅,而多半是維繫體制的例行活動而已;「父親權威制」則勾畫出父權的一夫一妻婚姻家庭中,父親與妻子兒女間的赤裸權力面貌以及父母對子女的性管制。賴希則認為,這兩種所謂的「強制道德」(compulsory morality)構成了家庭人際關係最主要的運作模式,而嘲諷的是,環繞著家庭的意識形態再現卻是最甜蜜溫馨的圖像和描繪,以至於不管婚姻關係和家庭生活如何苦悶無趣沈寂,不管孩子的人格發展如何被性焦慮和性壓抑所構成,人們還是不自主的合理化其中的痛苦,習慣性的覺得有義務鞏固這個制度。而在這種環境中所養成的自欺、偽善、敵意和怨憤也往往在無意識中啃噬家庭成員的心靈,使孩子不但無力創造自己的愉悅,連對別人的性愉悅也不是忌妒就是打壓,而且傾向唯唯諾諾、膽怯退縮、保守內歛,但卻同時迷信領袖、懼怕權威、甚至殘暴易怒。這些──正是權威人格的特質,也正是納粹之類的威權政治體制需要的臣民,其對情慾的矛盾畏懼但又自責壓抑,更形成資本主義生產制度需要的嚴謹勞動主體(Reich, The Sexual 82)。這種人格心理的固著一旦遭遇挫折的情勢就立刻退縮轉向,渴望回到某個安全的、不引發變動的位置上去。若不面對並改造這種人格心理的生成,性革命的效應往往只是一時的、有限的、個別的突破現象,而不能徹底切斷舊情緒、舊習慣、舊心理對舊制度的依戀和支撐。這個體認使得賴希視婚姻家庭為性革命的首要場域。賴希在這裡指出了體制內的性醫學和性教育專家們極力迴避的一個事實:一夫一妻婚姻家庭固然有可能是關愛和依賴的小屋,但是它也同時是壓迫與限制的牢籠。婚姻義務和家庭中的權威只會創造出一個個無力以自主的愛性來經驗人生、只想靠著婚姻的道德與法律制度來強取他們希望享有的安全感、歸屬感、佔有感的怯懦人格(Reich, The Sexual 29)。賴希本人則主張用自主自在,不建立在占有及監控上的自然結合(及分手)來取代強迫式的婚姻制度,徹底的改變人際結合的方式和形態,藉以改變在父權一夫一妻家庭中生成的情慾匱乏和權威人格心理結構。
[45] 不屑性革命的左派總是強調要先談情慾的「物質基礎」,好像情慾是什麼依賴著某種物質基礎而存在的次要東西,而那些「物質基礎」則有著自我獨立的優先地位。賴希所關心的則是那些使得物質基礎得以持續運作的「情慾基礎」──在這裡指的特別是婚姻家庭所養成的心理情慾結構。更有趣的是,賴希同時強調,這個情慾基礎從任何方面來說都是物質的,他在《性革命》的前半部指出,情慾的發展意味著物質世界的重組和資源的分配,因為性愉悅能力的培養需要文化物質基礎。換句話說,性當然不只是個人選擇什麼生活方式的問題,而是個牽涉到社會資源分配的問題。賴希很明確的指出,對一個經濟能力有限的青少女而言,她的情慾如果要能自在的得到滿足,這不只是她的性慾自由的問題,她同時需要隱私權、需要屬於自己的空間和經濟能力、需要避孕的知識與資源、需要肯定面對性事而且有能力愛她的性伴侶、需要開明支援的父母、而且絕對需要一個正面看待性的社會環境(Reich, The Sexual 15)。不過,由於在現有的婚姻家庭制度中,這些情慾資源的掌控主要是由父母來進行日復一日私密生活的監管和性道德觀的灌輸,因此賴希對父母以性控制來建立自身的權威並挫傷孩子的人格感到深惡痛絕。更值得台灣本地進步運動人士深思的是,賴希在提到情慾解放需要物質條件的時候,從不是為了消極的指出青少女情慾自主之不可能或困難,也不是憂心忡忡的擔心情慾解放有其經濟能力和階層限制;相反的,賴希正是要用這種對物質條件的強烈關注和具體要求,來指出青少女在情慾上的處境說穿了是代間壓迫的問題,是性別壓迫的問題,因此也是一個需要用更激進的情慾社會革命來改變的狀態。
[46] 196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初期性革命的浪潮中,美國的教育系統開始考量推動性教育時,女同志就已經在異性戀主導的婦女運動中清楚的看到(性)教育對再生產自我的重要,因此提出了非常前瞻的要求:「所有的性教育教程都必須包含女同性戀情慾,作為有效的、正當的性愛和性表達方式之一」(Echols 215),像這樣前瞻激進的運動策略在台灣本土尚有待生產。
參考書目
Adam, Barry D. The Rise of a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Twayne, 1995.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Altman, Dennis. “Political Sexualities: Meanings and Identities in the Times of AIDS.” Conceiving Sexuality: Approaches to Sex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World. Eds. By Richard G. Parker and John H. Gagn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97-106.
Asbell, Bernard. The Pill: A Biography of the Drug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5.
Bailey, Beth. From Front Porch to Back Seat: Courtship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U of Maryland P, 1988.
Berger, Peter & Brigitte Berger. The War Over the Family: Capturing the Middle Ground. New York: Anchor, 1983.
Bremmer, Jan. From Sappho to De Sade: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1991.
Bullough, Vern L. “The Development of Sexology in the US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cience in the Bedroom: A History of Sex Research.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4. 303-322.
D’Emilio, John. Making Trouble: Essays on Gay 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D’Emilio, John &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Dimen, Muriel. “Power, Sexuality, and Intimacy.” Gender/Body/Knowledge: Feminist Reconstructions of Being and Knowing. Eds. by Alison M. Jaggar & Susan R. Bordo.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89,1992. 34-51.
Echols, Alice. Daring To Be Bad: Radical Feminism in America, 1967-1975.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9.
Ehrenreich, Barbara. The Hearts of Men: American Dreams and the Flight from Commitment. New York: Doubleday, 1983.
Ehrenreich, Barbara, Elizabeth Hess, & Gloria Jacobs. Re-Making Love: The Feminization of Sex. New York: Doubleday, 1986.
Epstein, Barbara. “Family, Sexual Morality, and Popular Movements in Turn-Of-Century America.” Snitow et. al. 155-168.
Escoffier, Jeffrey. “Sexual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ay Identity.” Socialist Review 15 (1985): 119-153.
Evans, David T. Sexual Citizenship: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Faderman, Lillian. Odd Girls and Twilight Lovers: A History of Lesbian Lif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1991.
Faludi, Susan.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Crown, 1991.
Fine, Michelle. “Sexuality, Schooling, and Adolescent Females: The Missing Discourse of Desire.” Disruptive Voices: The Possibilities of Feminist Research.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2. 31-59.
Fiske, John.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Foucault, Michel.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1980.
Fout, John C. & Maura Shaw Tantillo, eds. American Sexual Politics: Sex, Gender, and Race Since the Civil War.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0, 1991, 1992, 1993.
Freedman, Estelle B.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the US.” Socialist Review 25.1 (1995): 31-46.
Friedan, Betty.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Dell, 1963.
—, The Second Stage. New York: Summit, 1981.
Grant, Linda. Sexing the Millennium: Women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Grove, 1994.
Green, Jonathon. It: Sex Since the Sixtie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93.
Greer, Germaine. The Female Eunuch.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1971.
—, Sex and Destiny: The Politics of Human Ferti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4.
Haag, Pamela S. “In Search of ‘The Real Thing’: Ideologies of Love, Modern Romance, and Women‘s Sexual Subje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40.” Fout & Tantillo 161-192.
Haste, Cate. Rules of Desire: Sex in Britain World I to the Present. London: Random House, 1992.
Hekma, Gert. “A History of Sexology: Soci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Sexuality.” Bremmer 173-193.
Illich, Ivan. Gender. New York: Pantheon, 1983.
Irvine, M. Janice. Disorders of Desire: Sex and Gender in Modern American Sexology.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90.
Jeffreys, Sheila. Anticlimax: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exual Revolution.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0.
Jenness, Valerie. Making It Work: The Prostitutes’ Rights Movement in Perspective.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3.
Kinsey, Alfred, et. al.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1953.
Kon, Igor S. The Sexual Revolutiion in Russia from the Age of the Czars to Today. Trans. by James Riordan. New York: Free P, 1995.
Kramer, Rita. In Defense of the Family: Raising Children in America Tod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Lasch, Christopher.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MacKinnon, Catharine A.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9.
Millett, Kate.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Patton, Cindy. Inventing Aids. London: Routledge, 1990.
Peiss, Kathy. “‘Charity Girls’ and City Pleasure: Historical Notes on Working Class Sexuality, 1880-1920.” Snitow et. al. 127-139.
Porter, Roy & Milulas Teich. Sexual Knowledge, Sexual Science: The History of Attitudes to Sexu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4.
Reich, Wilhelm.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Trans. by Vincent R. Carfagno.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0.
—. The Sexual Revolution: Toward a Self-Regulating Character Structure. Trans. by Therese Po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md Giroux, 1945, 1962, 1969, 1974.
Riessman, Catherine Kohler. “Women and Medicalization: A New Perspective.” Inventing Wo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Gender. Eds. by Gill Kirkup & Laurie Smith Keller. London: Polity, 1992. 123-144.
Robinson, Paul. The Modernization of Sex: Havelock Ellis, Alfred Kinsey,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Ithaca: Cornell UP, 1976, 1989.
Rorty, Richard.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9.
Rubin, Gayle.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Eds. by Henry Abelove, Michele Aina Barale, & David M. Halperin. London: Routledge, 1993. 3-44.
Sayres, Sohnya, Anders Stephanson, Stanley Aronowitz, & Fredric Jameson.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4.
Schur, Edwin M. The Americanization of Sex.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88.
Segal, Lynne. Straight Sex: Rethinking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London: Virago, 1994.
Segal, Lynne & Mary McIntosh, eds. Sex Exposed: Sexuality and the Pornography Debate. London: Virago, 1992.
Seidman, Steven. Embattled Eros: Sexual Politics and Ethic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Romantic Longings: Love in America, 1830-1980.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Smyth, Cherry. Lesbians Talk Queer Notions. London: Scarlet P, 1992.
Snitow, Ann, Christine Stansell & Sharon Thompson, eds.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London: Virago, 1983.
Stacey, Judith. “Are Feminists Afraid to Leave Home?: The Challenge of Conservative Pro-Family Feminism.” What is Feminism: A Re-Examination. Eds. By Juliet Mitchell and Ann Oakley. New York: Pantheon, 1986. 208-237.
Thompson, Sharon. “Feminism and Teen Romance: 1966-1983.” Sayres et. al. 296-299.
Vance, Carole S. “Negotiating Sex and Gender in the Attorney General’s Commission on Pornography.” Segal & McIntosh 29-49.
Vance, Carole S.,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92.
Weeks, Jeffrey.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85.
Williams, Linda. Hard Core: Power, Pleasure, and the ‘Frenzy of the Visibl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9.
Willis, Ellen. “Foreward.” Echols xvii-xv.
—. No More Nice Girls: Countercultural Essays. London: Wesleyan UP, 1992.
轉載本文請保留網頁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