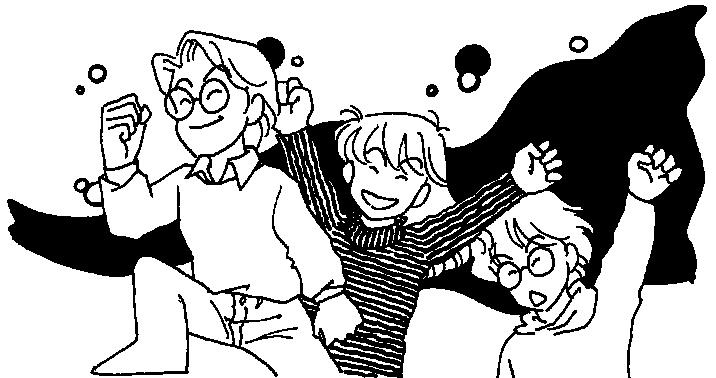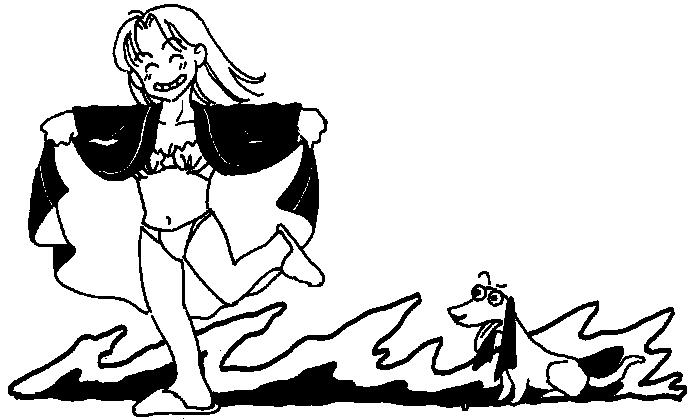
开学没多久,研究所的课程进度正如火如荼的开展,何春蕤老师来找我们几个过去在《性/别校园:新世代的性别教育》撰写小组中合作的成员,邀请我们再度共同合作撰写脚本,以便为桃园县的青少年学生生产一本128页有关性别平权的漫画。
听到这个邀请,我们都很兴奋,也有点徨恐。兴奋的是我们又可以象去年写《性/别校园》时那样聚在一起写作、讨论、打闹、玩笑;徨恐的是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大学时念英文系,研究所也念文学的人,对文本有相当的敏感度,可是讲到漫画,我们除了在国、高中时疯过一阵,现在大概也只是偶而看看好玩罢了。况且我们都没有尝试过以图象表达意念,现在要为漫画设计脚本,对我们而言,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经验,充满挑战性,也充满压力──我们很怕表达不出所要表达的东西。
不过,写作脚本,完成一本从青少年观点出发,属於我们自创的漫画书,这个挑战和梦想令我们都跃跃欲试,即使功课也蛮重的,我们最后还是同意加入漫画小组的工作。
按照我们的理解,五个月的工作时间,最后一个月是属於印刷厂的,要印14万本,倒数第二个月是教育局开会审核最后版本以及美工编辑制版的时间,剩下的三个月是我们的工作生产时间,哇!真是赶呀!不过,好象上次和教育局合作也是在几个月之中做完的,听何老师说,中间还有很多麻烦的文件准备及公文旅行过程,还好这部分不用我们小组成员费心,只要赶工就好了。
剧作家的痛苦
为了深切进入漫画的世界,在写作脚本之前,小组成员开始各自恶补一番。我们恶补的办法就是跑到漫画店里租来一大叠、一大叠的漫画书,堆在书桌上,不断的翻阅,一方面找寻想表达的主题,另方面想找到自己喜欢的画作风格,作为参考。大家以为从前为联考而恶补是苦差事,老实说,为写脚本而恶补漫画也很痛苦。倒不是因为漫画难看──事实上有些漫画还真是好看──真正的问题是我们预习恶补的时间只有一星期,就得在第一次开会时提出一些看法,那种日以继夜的猛看漫画,真是苦不堪言。
想而可见,第一次小组开会时当然是讨论很笼统,很简略,连我在报告自己的故事构想时都清楚的感觉到那种混乱的无力感。不过,讨论的好处就是有机会交换意见,也有机会脑力激荡,所以也谈出了一些可能的发展方向。我决定写一个有关变性的故事,好让男生女生都有机会想象变换了性别之后的感觉,金宜蓁决定写一个有关女生怀孕的故事,以探讨这个热门现象的背后,徐宜嘉则出于一贯对漫画的专业研究,决定写一个校园闹鬼的故事。和当初《性/别校园》一样,这本128页的漫画也是教育局出版的,所以在篇幅上先天就有限制,何老师说大概有10页左右的空间是用来提示本书主旨以及让县长、教育局长等官员写写序跋等等,真正分配到漫画的部份大约120页左右,三个脚本各负责40页。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人知道后来会发生什麽样的变化,也没有人知道这个写作经验会生成那麽多省思的机会。
第一次开会之后,我们继续一边恶补,一边想故事的类型、故事中的角色、以及故事的大概情节和走向,更回头去重读我们自己写的《性/别校园》,以便决定要传达的性/别消息和要处理的性/别问题,在第二周开会时提出讨论。我们都不是无所事事的学生,我们有学校的功课要应付,有支领奖助学金所需的工作要做,然而,凭着一股热诚支持,第二周开会时我们都交出了一个故事大要以及人物简介。但是我们也很快就发现个中的问题。

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剧本读起来不象是剧本,反而象小说;我们虽然说了故事,但是用的却是一堆描述性的语言,看不出多少可以表达动态的情节动作。可是漫画本身是以动作情节为主,照这样写下去,内容铁定枯燥无趣。何老师于是用我们熟悉的文学形式来说明,写个脚本就象写个剧本一样,要有场景,有人物,有事件,有action,有对话,有冲突,有细致的呈现,有剧情的发展。也就是说,所有的描述性语言都要转化为充满动态的图象,才叫漫画。何老师鼓励我们用图象的方式来想每一个场景,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经过这麽一示范,我们还真的好象看见了我们笔下的人物鲜活的在眼前经过。
另外,何老师也提醒我们,写漫画脚本不是写宣导文宣,要是宣导文宣,那就没人要读了。用漫画来讲性/别,目的就是要透过漫画的通俗形式,引发学生阅读和思考的兴趣,因此我们一定要避免呆板的“说教”,一定要模仿那些学生早就熟悉的漫画思考和语言,在他们不经意中传达我们想提供的信息。好在我们小组中的成员一向就不乏搞笑的专家,老师这麽一说,我们也就放心显露原形了。
还有,为了方便画漫画的人运行图象化的成果,我们的脚本将以分镜分场的方式书写,连每一格会有什麽场景、人物、对话都要标示清楚,对剧作家的我们而言,思绪一定要细密,想象一定要清淅。
这些的讨论改变了我们看漫画的眼光,我们不再只是看剧情,看人物,我们也开始注意漫画的语言图象特性,注意漫画的叙事方式,注意漫画的情绪欲望铺陈,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收获,也使得我们的阅读习惯更加细致敏锐。
当脚本作者碰上漫画作者
剧本写作的第三周,脚本已经“大致”成形。就故事类型来说,金宜蓁写的女生怀孕故事因为贴近现实,因此在故事风格上会比较写实,我的性别角色对换故事决定用外星科幻来串场,徐宜嘉的灵异故事则还在挣扎。由于这时人物角色、场景、情节都已大致完成,我们要求漫画家开始加入讨论阵营,以便测试脚本的可行性,也好让剧作家与漫画家沟通彼此的观念和想象。
这两群作者一见面开始共同讨论,就真正体会到“道不同”的差异--文本工作者和图象工作者观看表达方式的差距马上显现。差距最明显的地方就表现在漫画的分格上。
漫画分格有点类似电影“分镜”的工作,脚本作者呕心沥血的分镜设计,到了漫画家手中,却是颇有问题的。经过后来好几个礼拜的沟通和讨论,我慢慢领悟到,文本本身可能比较抽象,因此在短短的文本中常常可以包含很多的意含,可是漫画是具象的,他们根本不能容许这样的模糊,因此为了漫画剧情发展的合理性,漫画家和作家估算的格数常常发生不一致的情形。
其实,现在想来,计算分镜格数之所以发生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性:漫画家和文本作者的注意重心不同。
脚本作者写作的重心是以性/别议题的呈现为主,必要的时候可能尽量浓缩情节,但是在漫画家的眼中,故事的合理铺陈最重要,决不能因为主题的彰显而牺牲。也就是说,限于篇幅的关系,脚本作者所做的分镜格都是能省则省,看在漫画家的眼里,故事怎能这样演呢?作者可能认为,笑就是笑嘛!一格就可以了,漫画家却可能觉得要先烘托气氛,才能有合理的笑的气氛,或者,笑的动作要分三格以上才有“笑点”生成。问题是,如果完全依漫画家的分格方式,很可能就塞不进多少我们想要切入的主题,而这样也就部份丧失了画这本漫画的意义。
在后来的每周讨论中,这样的两难状态不断发生,作者和漫画家也就持续的在沟通的状态中,尽可能磋商找到两人都满意的解决方式。这种协商式的讨论经验对我们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宝贵的教育机会,让我们对艺术形式的差异有了更深的认识。
还有一个差异是在这个经验中浮现的,那就是性别∕个别差异。脚本组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女生,这不是我们阴谋如此,而是我们都对性/别议题有兴趣有研究,又恰巧都是女生;漫画组的成员则是两男一女,他们的画风也因此有很大差异,对场景和人物的刻划也有不同的见解。有时我们的脚本剧情设计到了男画者的手中就会遭遇质疑,他们说:“男生不会这样反应的。”这麽一来又开始一大段讨论和辩驳,大家各自表述,争执倒底这一段剧情要如何处理。
我从来没有在这麽多的自主讨论中斡旋过自己的看法,那种说服、对话、讨论、辩论,实在是个难忘的经验。我想这也是一种民主教育吧!
来自外界的压力
在我们工作了第一个月之后,就面临了第一次考验:我们写的脚本要由何春蕤老师带到教育局去接受审查,以便确定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合乎教育意义,听说有二十个评审委员,都是校长、主任、或大学教授。
然而,原本由三个人执笔的脚本,却在审查交稿的两三天前出了状况,徐宜嘉的故事在苦思後夭折。好在同时我们也发现,要成功的铺陈一个有剧情的故事需要不少篇幅,事实上,连我的性别角色对调故事都只有足够篇幅来说一半故事,我们讨论之后决定只让男生变女生,而把女生变男生的部份留给读者去想象。最后决议,这本漫画会以两个故事为轴线,各占60页。
剩下的两个作者的工作量,由一个人40页变成50到60页,而截稿日期迫在眉睫,最糟的是这时我们的电脑轮流感染病毒,所有辛辛苦苦打出来的文本稿全部流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一方面手忙脚乱的找人解决病毒的问题,一方面想办法按着原来列印出来的版本重新打字,重新打印,在最后一刻把作品交到何老师手中。
教育局的审查过程我们没有资格参与,但是老师回来时带了好几页抄写得密密麻麻的评语。从这些评语看来,教育局的评审委员可不只是颇有微辞而已。
就我的印象而言,评审们的理念还真的和我们相去甚远。例如,在人物的选择上,有评审不赞成故事之一的女主角是中辍生,说这样的学生没有代表性,也不适合做主角,做示范,这样会让大多数的好学生感觉不平衡。我们想不通的是,所有的课本都是好学生乖孩子做主角,别的孩子不平衡很久了,也该有机会上场吧!
有评审指出我们的漫画脚本包含了太多通俗商品文化的指涉,他们说麦当劳、肯德鸡、SOGO百货等名称,除了有广告之嫌,还可能让“乡下学生”看不懂那是什麽。(乡下学生没有吃过麦当劳?没有逛过百货公司?他们说:要切近乡下学生的“生活经验”,不知道是否要画烤番薯?)不过,我们也同意不要有那麽多现实的名称,以免被人家告。
另外,在名称方面,评审们也不欣赏我们费心想出来的幽默语句和人名,例如男主角“扬威”和女主角“梦怡”,或者他们的学校“三拔国中”等,坚持我们应该有点格调。我们想,修改人名大概也没什麽大关系,既然这些成人的幽默感很浅,那就顺从她们的意见吧!
在剧情方面,评审对我的变性故事没有太多意见,只是觉得有些剧情部分太夸大而已(例如女主角用捕鼠夹来教训骚扰她的男生),但是对金宜蓁的女生怀孕故事就有很多意见了。由于这个故事中的女生后来决定不跳楼而选择坠胎,评审们觉得争议性太高,要求我们多增加老师和父母的角色,让成人更正面的介入这个漫画故事,同时希望强调坠胎的严重性,免得青少年觉得太轻松。许多评审也提到他们觉得这本漫画很有创意,但是担心它太轻松,太轻挑,恐怕教育的意味不足。
对于这样的质疑,我们的回应是“适度修改,适度保留”。不能直接用现有的名称没关系,我们有的是迎接挑战的创意。所以,麦当劳的“M”招牌改成了“W”,总可以了吧!“扬威”改成“杨大威”如何?女主角则在健教老师的协助下坠胎,并学习了安全性行为的理念。
我们比较搞不懂的是,这些所谓的教育家(校长、主任、专家等)怎麽会对他们想要“教育”的青少年有这麽薄弱的理解,以为青少年会对任何的文本或漫画全盘吸收、照样模仿,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创意,成人们以为只要说教,说道理,单向的灌输一些教训和警告,青少年就会乖乖接收消息。我们生产这本漫画时,只是想给予青少年一本好看又实用的漫画书,这些评审的态度却让我觉得她们要我们生产“圣经”。
三个星期后,何老师应评审要求带去更新的版本,做第二次的受审。这一次,评审们对我们善意的回应和修改都给予肯定,但是有另外一些评语出现。其中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故事中有关家庭性侵害的部份。
我的变性故事中有两页描述了女主角被父亲性侵害的情节,也提供了一些坚决但轻松的应对方式,希望能明确的告诉青少女,她们可以严厉有力的拒斥父亲这种侵扰的行为。令我们惊讶的是,评审们这次对于这个虚构的内容非常介意,他们认为这样的情节描述会破坏一般家庭中父亲的形象,有可能会增加父女之间的紧张状况。他们的建议是,不要用父亲做为性侵害的可能角色(照他们的说法,一般父亲都不是这样的),而应该代以熟识的或陌生的“长辈”,否则好多家长都会抗议这本漫画。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正是因为大家比较看重维护父亲的神圣形象和权威,才使得无数青少女在家中受害而不敢披露,而现在在这些第一线的教师身上,我却看见正在继续强化这种让青少女噤声的态度,实在令我不敢苟同。不过听起来,她们的要求还十分坚定。我同意何老师的说法,我们不愿意放弃这个部份,因此我们决定不直接演出,而只透过人物的对话来“叙述”家庭性侵害,期望在另一个场合可以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安慰自己,官方出版品就是官方出版品,他们就是因为要担心太多事情,才会变成那麽蹒顸牛步的。
另外,许多评审也一直觉得很困扰,认为我们的漫画教育目的不清楚,她们希望这本漫画要很强烈的说明青少年行为的后果严重,惩罚严厉,最好多说法律上面的规范。我们的看法则是,这样的恐吓已经形之多年,显然没有多大果效,因为单向的、权威式的喊话根本就进不了青少年的耳朵,老实说,谁会注意听训话呢?而当青少年关掉通信的频道时,我们想要给他们的有用信息也被排除了。我们相信,要接触到青少年就要用她们的语言,说她们的需要,然后提供信息,从她们的角度来谈事情才可能接触她们。最后,我们还是决定用我们的开放方式来画这本漫画。
还有评审觉得我们的漫画有很多部分谈到性、身体、保险套、怀孕、卫生棉、谈恋爱,应该当成保护级,让家长老师等成人指导着学生看才行。听到这种说法时,我们只觉得惊讶这些老师校长怎麽都不去漫画店看看孩子们在看些什麽,怎麽都不去真正的了解孩子们已经知道了多少事,怎麽不面对每天社会版上层出不穷的青少年活动和行为。难道这些成人都假设孩子们是白痴?老实说,以我恶补时所看的流行漫画而言,我对今日的青少年充满敬意和羡慕,他们从小就接触那麽多充满创意的故事剧情,他们只是常常在成人面前装傻而已。可惜这些评审恐怕一辈子也不会接触到这一面了。
类似的评语在两度的审查中不断重复,不断的传递这本将要成形的漫画带给评审们的困扰。其实这样的忧心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这本漫画的特色、理念就是要破除某些既定的成见,破除成年人和青少年之间截断的沟通管道,而那些已有成见的人当然难以接受。也就是因为他们的焦虑,更让我们在必要的地方坚持我们的特色,而这些干扰也成了支持我们坚持理念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