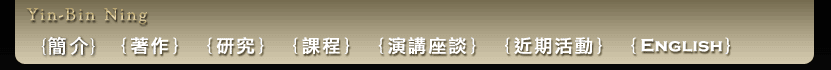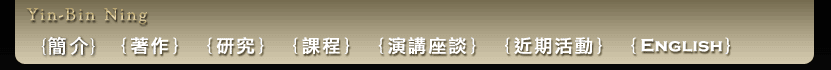魔術強生與B型肝炎
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在一個對「性」歧視、並且壓迫非主流情慾模式的社會中,如果一種疾病被歸類為「性病」,那麼得到這種疾病的人也會遭到被歧視與被壓迫的命運。這可以從B型肝炎和愛滋病的比較中看得出來。
在臺灣,曾有五分之四以上的人口被B型肝炎病毒所感染,其中,將近五分之一的人,變成帶原者。這個疾病有很多可能的傳染途徑,但是「無防護濫交(不安全性行為)」是非常有利於病毒傳遞的一種生活方式(這就好像胃潰瘍的成因固然不少,但是生活方式緊張的人易患胃病)。雖然「無防護濫交」是易患B型肝炎的生活方式,可是B型肝炎並未因此被視為「性病」。
B型肝炎和愛滋病的傳染途徑都同樣是靠血液或體液,它們都可以因為生育時造成母子垂直傳染,也可以經由輸血、拔牙、共用針頭、刮鬍刀、或者性交而傳染(AZT這種藥有時也同樣用來治療這兩者)。雖然兩者頗為相似,但是B型肝炎似乎不像愛滋病一樣,引起如此大的恐慌與道德義憤。
或許這是因為愛滋病比較「可怕」?可是相較之下,由於B型肝炎感染者多而且普遍,因此比愛滋病更具傳染的威脅性,而且和愛滋病一樣,也沒有任何有效的藥可以治癒。再者,即使愛滋病十分可怕,引起很大的恐慌,但又為何會引起道德義憤呢?如果說人們在道德上責備愛滋病,是因為他們責備「濫交」,那麼為什麼人們不責備B型肝炎呢?除了後者不被當作「性病」外魔術強生與B型肝炎,還有什麼可能原因嗎?
有人或許認為這是因為B型肝炎患者多變成慢性帶原者,這些人大體上與一般健康人無異,而且只在一段相當時間之後才可能演變成肝硬化,或甚至肝癌。可是就這一點而論,愛滋病也是一樣,其帶原者就是「HIV陽性」的人,他們也多半是健康的,直到一段長短不一的時間後,大部分人才開始發病。有趣的是,人們通常不會把B型肝炎帶原(表面抗原陽性)和肝硬化或肝癌混為一談,但是人們卻常把HIV陽性和愛滋病發作後的「可怕」病癥混為一談。日前被衛生署不準入境的美國籃球明星魔術強生就是一個HIV陽性者,據說由於他不是因為輸血方式,而是因為「濫交」而感染,所以衛生署覺得他是「錯誤示範」。
我在想,當衛生署面對B型肝炎時,是否會追究這個疾病是怎麼得到的?濫交還是輸血?會不會對因為無防護濫交而染B型肝炎者加以道德譴責,認為這種人得病是咎由自取、活該天譴?其實衛生署或者醫學界在面對任何疾病時,都應當嚴守價值中立的立場,不應該對任何生活方式作出道德判斷。例如,有人生活方式緊張,有人不運動、有人喜歡吸菸、有人不喜歡刷牙、有人喜歡「濫交」等等,這些生活方式都可能「不健康」,但是衛生防治者不能把這些生活方式當作道德問題來看待.而只能就某些生活方式和某些疾病之間的可能關連作出專業的判斷,如「濫交者應當戴保險套」之類,而不應該「要避免濫交、同性戀」這些超出醫學專業範圍的性道德及性政治言論。
再說,對於任何一種疾病,我們都應鼓勵病人表現出快樂、希望、自尊與勇者的形象,這不僅是人道的態度,也表現出人類對抗疾病的不屈精神,更可能是減低疾病痛苦的良方。所以我們應儘量呈現愛滋病患的這一面,魔術強生的英雄形象因此有助於改變一般人對愛滋病的誤解。
在另一方面,魔術強生之所以不能來臺,是因為他「現身」(Come out)自承是HIV陽性,而其他外國人只要不「現身」,就可以來臺,因此衛生署的做法等於不鼓勵帶原或愛滋病患現身。可是現在大家都知道鼓勵現身是一種防治愛滋的方式,透過當事人的現身及說法來消除大眾對愛滋的歧視與誤解,進而達到防止愛滋擴散的目的。這麼說來,衛生署在強森案上的做法倒是恰巧與其防治愛滋的工作目標反其道而行了。
原載於1995年10月16日《聯合報》副刊
附錄─一息尚存的尊嚴
愛滋電影《愛是生死相許》
過去有關同性戀的電影,除了得不到主流大製片廠的支援外,最常見的特色就是以同性戀個人為焦點,處理(例如)同性戀者與父母,與異性知己之間的關係。
美國片《愛是生死相許》則處理了同性戀社區或社群,以這個社群內某個小圈圈為中心。這個處理角度不是偶然的,因為影片主題是環繞著影響整個同性戀社群(而不只是個人)的愛滋病。自1980年代開始流行的愛滋病,活生生地將美國最有生機力、動機、多彩多姿、革命性的同性戀社群逐漸消滅殆盡。這不但是人類的悲劇,也是人類的損失。愛滋病把一個可能豐富人類(精神的、身體的、家庭組織的、愛情的)文明的重要來源扼殺了;扼殺的方法是用最殘酷的肉體摧殘、折磨及死亡。
在這整個消滅過程中,充滿了歧視、迫害與漠視。(如果愛滋病是上層異性戀的疾病,可能早就得到政府大力的財力支援,而發現治癒方法了。)然而在這部電影中,我們卻看不到憤怒與抗議。整部電影是低調的感傷和喟嘆;甚至連愛滋病者長期痛苦的煎熬,肉體驚心動魄地扭曲變形、病榻的呻吟與掙扎,都沒有著墨太多。為什麼要作如此低調的處理呢?
我認為「憤怒與抗議」是一個社群尚有能力反擊時的情緒和舉止;現在整個社群逐漸到了迴光返照的最後時刻,它所有的便是對過去美好的回憶,對奮鬥過程中的一個平實的記錄,以及一息尚存的尊嚴;這些也都表現在整部電影中。
用消滅肉體的方法只能消滅同性戀於一時或一代,因為同性戀原本就是人類性心理構成的另一面(被壓抑、被隱藏的一面),除非異性戀也被消滅(亦即,異性戀與同性戀的區別被消滅),否則同性戀永遠不會消失。
短視與漠視愛滋同性戀的人,將在1990年代發現愛滋病成為異性戀的噩夢,愛滋病與同性戀的關連甚至可能會被忘記。之後(就像片尾所象徵的),我們將期待同性戀社群的浴火重生。
原載於1990年12月3日《自立晚報》
後記
附錄短文寫於愛滋病在臺灣的初期階段,目睹國外同志社群由極盛轉為集體凋零死去,故而表達的是哀傷悲憂之情;後來出現了較多能控制愛滋病情的藥物,同時(不幸而言中)異性戀成為愛滋病患的多數。
《愛是生死相許》的中文片名是由電影人景翔從英文片名Longtime Companion翻譯而來。典故是早期在愛滋病盛行時,訃文中不知道如何稱呼逝世同志的「未亡人」,於是就以longtimecompanion(長期友伴)稱之;現在則多稱為partner(夥伴)。該片是西方第一部處理愛滋與同志的主流電影,在臺上映時賣座頗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