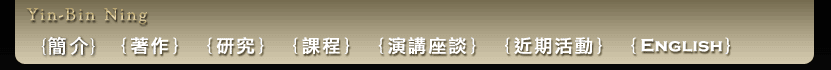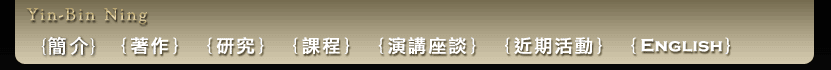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
SM不是性心理變態,也不是性虐待
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不論是大眾媒體或一般人的觀念裡,對於SM經常有錯誤的認識,例如將SM稱為「性變態」或「性虐待」,或視為「心理病態」,這些都是不正確的說法,這些錯誤說法也顯示這個社會缺乏性權利的意識。
把SM視為性變態乃源自西方基督教的傳統,隨著殖民主義與性學發展而擴散到非西方世界。基督教認為性的目的就是生殖,凡不是為了生殖的性行為都是不自然的,故而手淫、愛撫、口交、同性戀都是道德上的過錯。反對這個宗教傳統說法的早期性科學雖然一方面認為非生殖模式的性與道德無關,另方面卻同時將
SM這些非生殖的性稱為「性變態」,當作某種生理或心理異常。
在現代國家人口節育政策與避孕科技的發展之下,生殖不再是性的唯一目的,性更是為了愉悅與快感,生殖模式的性道德遂逐漸被廢棄,手淫不再被教育家與父母視為大敵,肛交也在很多國家被除罪化。更有甚者,如果在性活動中追求愉悅快感是自然的,那麼SM這些促進性興奮的非生殖性活動根本就是性常態,是一種性偏好或口味癖好,如同各種助興的性體位與情趣用品,更無涉道德人格。
很多人以為SM只是少數人的「特殊」性癖好,其實它一點也不特殊,反而是非常普遍常見的,只是很多從事SM的人不自覺而已。例如許多人會在性活動中包含各種形式和程度的抓咬捏捶或其他形式的激烈性愛,更多的人則使用角色扮演,用不同的配件裝置器具來營造氣氛。最常見的SM除了動作激烈狂暴外,還有口頭暴力,例如在性行為中使用禁忌的語言、髒話或者以語言自貶或貶低對方等等。除了這些幾乎人人均從事的SM「入門」外,SM還可以被進一步開發而達到更為繁複與儀式化的形式,媒體中常見的皮衣頸扣及捆綁等就是其中廣為人知的例子。
SM的普遍性有其心理基礎。弗洛依德認為在性壓抑社會中,人們對於性有羞恥、嫌惡、痛苦、恐懼等心理,這些心理阻礙了性愉悅。可是「性變態」(亦即,非生殖的性,包括手淫、裸體、愛撫等)卻有促進性愉悅的功能。
例如,原本裸露是讓人羞恥的,但是人們在性交時喜歡脫光衣服,就將羞恥轉化為性興奮。同樣的,喜歡口交的人可以把對性器官的嫌惡感轉化為愉悅;喜歡SM的人則把原本連結到痛苦、恐懼、無助等心理的性活動轉變成快感。這是一種很合理的心理機制。
弗洛依德認為性變態克服了性壓抑,因此反而不會因為性壓抑而形成精神官能癥。易言之,SM把侵犯與破壞的心理以儀式性的行為操演出來,反而比較不會有精神疾病。有心理醫生說如果性活動過度依賴SM則是「病態」,這其實仍是預設了生殖模式為性活動的典範。但是熱愛SM的人,就像性活動中熱愛口交或裸露的人一樣,沒有什麼心理問題或不妥。
照這樣說來,SM不應與性虐待混為一談。性虐待(sexual abuse)是枉顧對方意願而施行的身體侵害,SM卻是在雙方同意之下充分協商而進行的戲碼。臺灣許多性研究者將SM稱為「愉虐戀」是很有道理的,「愉」就是以對方的愉悅為主要關注,「虐」則是雙方在一定的儀式程式中建立起互動的角色和戲碼。絕大多數的人多多少少都會玩一些愉虐的活動助興,有許多人只有在某種清楚明顯的權力支配之下,感覺到自身的全然無助,才能放鬆自我的僵化而得到快感。
事實上,愉虐戀正是在這個充斥各種不平等關係的社會環境中模仿或諧擬(parody)暴力及支配,並在協商過程中建立雙方的信任感與親密感,這和真實的暴力與支配大不相同。有些女性主義認為SM展現了男女不平等或男性暴力,這是對愉虐戀的誤解,因為異性戀的SM並不一定男支配女順服,而且在SM中真正主導整個過程的人常常是那個看來被支配的人。SM中的複雜操作和互動模式還有待我們不帶成見的認識。
臺灣解嚴後,性開放的程度雖然很高,但是被稱為性變態的弱勢「性少數」族群卻沒有性權的保障,結果這些性少數經常成為被媒體偷窺、被商業剝削的對象,也承受著道德的污名與曝光後的迫害。很顯然的,性開放不等於性少數的解放(性解放)。面對這種不符合社會正義的性壓迫,除了對社會大眾進行更多的性權教育外,臺灣的愉虐戀者也應會和同性戀者一樣組織起來,爭取其不被污名與歧視的權利。
原載於:2002年1月7日臺灣《中國時報》時論廣場。並收錄於《性政治》,游靜編,香港:天地圖書,2006。頁242-245。
這篇文章的寫作脈絡是:2002新年期間爆發了臺灣立法委員黃顯洲在五星級大飯店遭強盜疑案,涉嫌女子詹惠華的弟弟詹富順向檢警供稱,黃顯洲喜歡玩多人的SM「虐待式性愛」遊戲。一時之間,SM被污名化。本文則說明SM是愉虐而非虐待,意圖在主流媒體上將SM的大眾通稱由「性虐待」改變為「愉虐戀」。好友小林epicure在這之前與之後也持續以實踐者身份向大眾正名SM為「愉虐戀」。在《島嶼邊緣》雜誌時期,愉虐戀也被稱為「悅虐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