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体交尾、互噬的双头蛇—— Jade 后设的小说把它的反抗置于小说自身的形式之内。[1] 本文拟针对洪凌〈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水晶眼〉两篇小说作析论。前半部份从一些小说中的关键字词出发,逐步讨论构筑这两篇文本的重要概念,接着挪用思想家布西亚的部分理论阅读洪凌这两篇小说,最后探讨理论与小说的交互作用。 1.
双头蛇的叙事结构、“绝对我”的生成 这两篇小说均采用两条平行的叙事轴线摹造故事——〈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以“后星历三三三年”与“后星历六六六年”,〈水晶眼〉则以“后星历九九九年”与“西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2]”。可分别视为四个独立的故事、两两对照形成一个故事,或是将两篇小说的四条叙事轴线参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阅读[3]。在此,多变的叙事技巧,给予小说更丰富的阅读可能性,在辑前【身为镜相的深渊】中也明载了作者将这两篇小说视为“最初与最后的阿烈孚”的系列故事。[4]在这样多重变异的叙事轴线的穿叉交会偶合散逸作用之下,开展了文本衍异变化的无限空间,使得阅读过程成为一块块断片的随机串连,瓦解了对于传统小说常见的单一叙事拼图集合的期待,而这样的莫衷一是,也令读者更进一步的共同参与了文本的产制过程。 暂且将这两篇小说视为同一系列的叙事文本,可以发现其中反覆出现一些蕴有重要概念指涉的字词贯穿于文本之中,而这些字词也均具有复义,隐含多重的指涉功能,诸如:水晶[5]、眼睛、玫瑰、晶片╱记忆、奥曼帝(Almighty)[6]、安斐斯宾纳[7](amphisbaena)╱双头蛇、阿尔法(Alpha)、奥梅嘉(Omega)、阿烈孚(Aleph)等等。因而,对这些关键字词的探究,恰为诠释肇始的可能所在。
“安斐斯宾纳”(amphisbaena)除了作为文本中故事的发生地,也可作为文本的叙事象征:那“双头蛇的互噬意象”[8]正似“后星历三三三年”与“后星历六六六年”、“后星历九九九年”与“西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这样两两相对的叙事轴线,而〈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与〈水晶眼〉两篇文本意义间的相互补足亦可作为又一两两相对的双头蛇意象。同样地,若将这两篇小说视为同一系列的叙事文本,则情节铺陈行进亦近似双头蛇的互噬,如同纪大伟已然提及的“莫比斯环”[9],这样的书写策略使得文本呈现出一无尽的空间,看似不同的两个平面实际上却又是“融媾合一”、“共生共灭”[10]的。 阿尔法(Alpha)作为“始初”相对于奥梅嘉(Omega)所象征的“终结”,是“安斐斯宾纳”的存在象征,形构着文本的环形迷宫,两者难以分割[11]既是同一却又各自分裂成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监视者/窥视者,与,另一个“被”叙事者/监视者/窥视者,也“触及主控(domination)与屈从(submission)角色之间的权力脉络[12]”,但这样的“主控与屈从”并非是单一行进,而是双向往复的。奥梅嘉的全知形象迹近无所不能,但却无法体验“次次替换的互异人生,无限量涂抹重述的后设机会,无穷尽的诞生快感与死亡高潮[13]”,奥梅嘉是至高无上的说故事者,却也只能倒楣地等待“三百三十三年的真相大百解说[14]”;阿烈孚赋予拉比丝生命,奥梅嘉(拉比丝)最后却也将那只因灌注了阿烈孚生命而生的红色眼睛挖出还给了阿烈孚(阿尔法)。主从关系中所包含的所有与隶属在文本中并非是恒立不变的。 从阿烈孚╱阿尔法与拉比丝╱奥梅嘉之间,“你与我”之间的互动,逐步展示着另一个使文本/游戏可以如同莫比斯环无限往复运行的重要概念:“执念与爱欲”。即令记忆沦陷在一枚枚晶片的更替植入中,但在那纵使时间已然失去可兹存在的线性座标的异质空间——网路——当中,“凝视的欲望”依然存在。 “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记忆包含着与身份所属相关联的一切认同,墓碑则是身份所属的一种变异固着物,试图标定认同所凝构的身份所属,但吊诡之处在于,墓碑恰恰昭示了身份所属者的不在。晶片从作为记忆的承载体最后成为记忆自身,一枚枚的晶片暗指了“本初”记忆的虚假与不可凭恃,如同在墓碑上头除了冰冷撰刻的姓名我们知道的不会更多。晶片抽换更替意谓着对于身份认同执着的瓦解,在〈水晶眼〉的最后,红色眼睛回复为白色的水晶石头,自己终结自我,自我解构,却也同时生成了“绝对我”[15]: “我”化身为一个无中生有的文本——自己就是故事,也是让故事产生的讲述声音。接下来,随着故事的崭新发展,白玫瑰将会恢复血色,而水晶也终会转化为肉眼,凝视着所有早已存在、或者无中生有的小说情节。 如今,我不想寻找已然失落的始初,但却想进入随时变形的身体与身份,重新拥有一双血肉构成的眼睛,重新爱上“凝视所爱”的绝顶快感。 (洪凌:2002c:154) 2.
从“具有”到“存有”,客体变成主人的回返过程
在阿尔法与贝塔的关系中呈显著爱欲与死亡的相互隐喻,而爱欲与死亡的战场则是那阿尔法与奥梅嘉所共有的,“一体两面的晶片[16]”。在〈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后星历三三三年的叙事情节中,两次阿尔法与贝塔的交欢均设定在满室嵌合的镜相场景之内[17],镜子做为空间的延伸,与终结,将对象物均反射到一封闭的系统内,而与贝塔在那自我封闭的空间内交合的阿尔法之欢愉,来自从镜中“窥见的各种姿态的自己[18]”,阿尔法的“性的客体不是对象的身体,而是自己的身体”,阿尔法更深沉的欢爱对象是“被对象化的自我影像”[19],一切都向内回指自身,是自我与自我的交欢、是身体在镜子内外的双重媾合。另一方面,贝塔作为阿尔法的“第二个自我、另一重自我[20]”,帮助阿尔法证成了爱欲与死亡的隐喻,不论是在后星历三三三年,或是后星历六六六年,在阿尔法交欢后酣睡的梦境中,紫色光球均爆裂成无数碎屑,鲜红色的玫瑰则自贝塔脑壳破碎的窟窿中汩汩涌出。爱欲通过梦的甬道指向死亡,死亡则丰美了爱欲的意象,一如文本中所谓的“哀伤促动更高层次的感官悸动”而“凶嚣的肉欲隐喻穷途末路”[21]。
贝塔协助着阿尔法的反叛,而这样的反叛则来自游戏最初“自己反对自己”的设定;梦境中的紫色星球也就是B级小行星“安斐斯宾纳”(amphisbaena),而紫色星球的爆裂亦即是双头蛇互噬的一种自我终结意象,鲜红色玫瑰妖异的生发狂绽可暗喻为自我解构后生成之“绝对我”更加昂扬的勃勃生机。于是回视阿烈孚与拉比丝的关系,阿烈孚╱阿尔法与拉比丝╱奥梅嘉之间的“执念与爱欲”,是驱动文本/游戏如同莫比斯环无限往复运行的母式[22],但此处的执念(obsession)并非是需要解脱的“我执”,毋宁可被视作“着魔”,而魔性本为“我”(双首共生的阿烈孚╱阿尔法与拉比丝╱奥梅嘉)所本有,是一种迹近超越但非超脱的本体观[23]。 游戏中反叛程式的设定需要胜利才能破解,如此一来阿尔法方能赢回原生记忆,然而原初的记忆在一次次拟真的生命历程已然无从追索,“绝对”令觉醒后的阿烈孚无比疲乏,他╱她拒绝回到一体共生的状态,于是拉比丝╱奥梅嘉先其一步执行了自爆程式,“我”意图中止,但“爱欲与执念”在自爆的自我终结过程中,从极度疲乏的质体产生了比先前自我愈益自足的“绝对我”——最极致的叛徒(形式)与反叛结果——更彻底地,不再是“具有”的结构,而是“存有”的结构[24],换言之,经过放弃与毁灭“我”的翻转过程,魔性不再仅是我所本有,魔性即为绝对我。 从“具有”到“存有”,拉比丝╱奥梅嘉经历了一场“客体变成主人”的回返过程[25]。雌雄同体又掌握着叙事的奥梅嘉看似无所不能,但由于阿尔法╱阿烈孚的拒绝使其成为带着匮乏的对象物,奥梅嘉成为外于阿尔法的客体性存在(做为客体性存在并非意指客体,依然是一主体存在),“我”原本光影共生、正负相谐的行动者、验收者互为主体的关系在阿尔法的拒斥下瓦解。奥梅嘉的匮乏来自阿尔法对她的亏欠,奥梅嘉“完整无比。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填补它失落的那些东西……”[26],看似矛盾的文本叙事恰好回应了奥梅嘉在文本中的悖论性,也预示了双头蛇互噬最后的毁灭终局,但执行自爆程式的不是创生了拉比丝╱奥梅嘉的阿烈孚╱阿尔法,而是拉比丝╱奥梅嘉主动扬弃了共生的关系,这样的主动扬弃所造就的自我生成,也就是其之所以能由客体彻底翻转成为主人的关键: ……奥梅嘉是阿尔法所抗拒以爱欲注视、在阿尔法的生命版图中悬吊着座落不定、在非阳即阴的堕落二元世界里如同冲出了滑梯的雌雄同体,一种被置于客体性的存在主体,于是,她之掌握叙事、成为注视者与故事的创造者,其实又是“客体变成主人”的回返过程。
(刘人鹏:2003:20)
于是从“一体共生的我”到“绝对我”,奥梅嘉不再命定的被设置为阿尔法的观察员与真相解说员,拉比丝也无须再孜孜等待阿烈孚的觉醒,主控/屈从的双向往复自此进入“狂妄的绝对状态”[27],“我”即为意念,即为欲望,奥梅嘉/拉比丝不再仅是掌握叙事、创造故事但又必然委身于客体的存在主体[28],而是拥有任意变异身体与身份力量的魔性存有,一握有单向操控能力的主人。 3.
另一种神圣的三位一体的比赋:拟仿、超真实性、内爆 在〈后现代(媒体)社会的解剖师——布西亚〉一文中括引了这么一段布西亚的话:“拟仿的特质在于模型的居先性;所有模型的居先都环绕着这么一个事实——模型先存在,模型中轨道的运转,设定了事件真正的磁场。事实不再具有自己的轨道,它们浮现于模型的交点,一个单一的事实可能是由所有的模型在一瞬间,共同制造出来的。[29]”以这段话语作为〈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水晶眼〉这“最初与最后的阿烈孚”系列故事的药引,可将前文所述及的“双头蛇式的叙事架构”视为这样的一个模型结构,同样地,小说情节中每三百三十三年的真相大解说的程式设定,亦可视为另一居先性的模型结构,而后无论是阿尔法与贝塔的热烈爱恋,或是阿尔法反覆奔命于对奥曼帝的反叛,皆为模型内部预先设置的事件,“拟仿预先铺置了轨迹及管线,来管制及制造即将发生的事件[30]”,也就是说,这两篇小说的叙事架构与情节书写都带有“拟仿”(simulation)的特质,亦即构筑出了一“拟仿的空间”,其中任何单一的叙事情节,可以自成系统,而众多纷陈林立的子系统可回到更高层次的系统中,也都是在双头蛇叙事模型内部进行的诸种反馈作用,自体交尾的双头蛇正隐喻了系统/模型本身不断自我再生产的完足性。 一旦进入此一拟仿的空间“任何事物都已经死亡,或是事先已经发生了[31]”,一如〈水晶眼〉最后在那“无始无度的异度空间”中的拉比丝/奥梅嘉,其存有的状态正说明了线性时间的瓦解,在未来死亡的拉比丝/奥梅嘉于过去诞生,诉说着一个已然发生的未来事件,因果倒旋,开始与结束无从分辨。于是,要在这样拟仿性的文本书写中探求真理或原初变成一错误的提问、一假命题,无法像面对传统叙事小说般追究真实再现,因拟仿“不需要原物或实体,而是以模型来产生真实:一种超真实(hyperreal)。[32]”模型结构已先行设置了一整套的拟仿秩序,而这也回应了第一部份讨论到的“莫比斯环”的书写策略,以及其所凝构出的那共生共灭、无穷尽的文本空间,。 〈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与〈水晶眼〉这“最初与最后的阿烈孚”的系列故事,其超真实性即在于藉由“自体交尾、互噬的双头蛇叙事模型”,在小说本身的情节虚构中,再度地模糊了真实与不真实的疆界,黑洞般吞食了文本自身产制出的意义——奥梅嘉的真相大解说吞食了阿尔法执着地反叛和爱恋,也吞食了那段“假”故事/记忆的意义;〈水晶眼〉里的拉比丝彻底地在虚构中拆解着种种真实与不真实,最后更是全盘吞食了“之前”的叙事书写。用布西亚的字眼则是“内爆”,整个小说叙事情节的书写便像是对一“全然能趋疲[33]”过程的描绘,指向各种界限、各类对立项的崩溃:诞生与死亡、身体与意识、肇始与终结、时间与空间、人与非人、真实与虚构……,字词原先承载的概念在叙事情节与叙事结构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翻转,但并非是单纯地反向占据了对立项的意义,而是向四方扩散、蔓延,衍异出驳杂非一的意义袭夺了所谓唯一的原初、本义;自体交尾隐喻诸般疆界的模糊,双头蛇的互噬最后则连文本书写所产制出的意义都一并吞食了。 小说中另一具体化的内爆隐喻是安斐斯宾纳,这颗由核子弹头堆叠而成的精致人工星球——也是一颗威力强大的超级核子弹,不断地自体增殖,随时都可能自体爆裂。拥有安斐斯宾纳的奥曼帝则是阿尔法命定要去对抗的,因而这颗紫雾光球也就是历经数回重新插入记忆晶片的阿尔法始终致力于要去摧毁引爆,只是无论是不断轮转重生的阿尔法(们),或是记忆觉醒后的阿烈孚都没能成功的引爆╱自爆“安斐斯宾纳”——也是奥曼帝,亦是奥梅嘉/拉比丝脑中的记忆中枢——游戏的终结是由奥梅嘉/拉比丝执行了网路自爆程式。由阿尔法/阿烈孚所创生的奥梅嘉/拉比丝反过来袭夺了阿尔法/阿烈孚的位置,在通篇的故事情节中,握有故事行进的主导权,直到最后更掌控了带有多重隐喻效果的“内爆”,这也是在第二部分中已讨论的,奥梅嘉/拉比丝之所以能由客体变成主人的关键。由于安斐斯宾纳也隐喻着那双头蛇式的叙事结构,因而内爆不仅在文本中情节书写的层次,也在自体交尾、互噬的双头蛇叙事结构隐喻了内爆的必然;内爆的不仅是文本书写情节中的安斐斯宾纳、奥曼帝或是奥梅嘉/拉比丝,更是整个文本意义的内爆,从这个角度看,这“最初与最终的阿列孚”的系列故事进行了一次对“叙事”的彻底反叛。 “…以后不再有历史了,我们被冻结于冰封的现在,而时间已然绝灭[34]”,布西亚笔下的拟仿空间,是一脱离了历史真实进入拟仿真实的世界,全然的能趋疲使得此一超空间失却了一切的意义,呈现一单调、呆板重复的惰性状态,不再是现代性情怀永无止尽的“前进”,而是一种后现代性的“停滞”,这是习于真实再现的人们所面临的一种崭新体验,人们跨入了与过往全然不同的经验领域——一种历史的终结状态。 在〈水晶眼〉终端执行了自爆程式后的拉比丝,进入了时间的线性法则所无法约束的人工异境,“我”(拉比丝)冻结在这则“最初与最终的阿列孚”系列故事的尽头,进入了时间绝灭、历史终结的空无状态,冷蓝色虚无、无始无终的虚拟网路空间也就是拟仿真实的超空间,拉比丝“失去了先前的身体[35]”,或可谓是扩展了对于身体存有样貌的想像,而像是旋转于拟仿天空中短暂辉耀的碎片,“不再有任何的指涉对象[36]”一般,拉比丝成为散落于交错网路中的意识。 〈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水晶眼〉均以虚构的年代历纪分割篇章的方式说故事:“后星历三三三年、后星历六六六年、后星历九九九年、西元一九九九年”,除了第一部份已提及的多重叙事趣味,可令读者进一步参与文本的产制之外,这样的叙事手法也收受了解构历史本质是纪实、小说本质是虚构的画外音效果。将作者在〈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一开始所引的“人没有本性,唯有历史”和年代纪实方式撰述的叙事手法、小说中不断翻转真实与虚构的情节书写,以及,小说主角的设难以确认究竟是何种“人”或根本仅为一股意念等等并观,这两篇小说亦质疑了习常对于“人”跟“历史”的看法,进一步来说,这两篇小说的虚构性反过来吊诡的挑战了真切的历史,体现了历史的不可确定性,也质疑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概念。没有什么是“人”存有的自然、本然状态,不论是在具体可见的身体构造或是抽象层面的精神意识,人的本质随时在变动之中,而人所拥有的历史就像是这则虚构的系列故事。[37] 4.
理论“与”小说 有必要先说明一下此处“与”字的概念及应用[38]。
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曾以黄蜂与兰花为例说明“变向”(becoming),而此二者的变向关系则系于“与”字的作用[39]:
对德勒兹来说,主导语变向少数语才有意义,反过来的变向只会制造另一个新的主流,对瓦解权力核心及架构毫无益处。同时,德勒兹也解释说,“变向”(笔者[40]按:becoming)不是模仿,也不是同化,所以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也不是二元对立的模式。他以黄蜂与兰花的变向为例:黄蜂与兰花相遇,黄蜂从兰花中采蜜,黄蜂变为兰花繁殖器官的一部份,而兰花也变为黄蜂的性器官一部份。两者形成一个独特的变向过程,是一种对话。它们两者的变向关系在于“与”这连接词上。“与”对德勒兹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连接词,而是近乎一个“张量”的符号,它包含着黄蜂与兰花交接的无穷变数。“与”本身就是变异,它不是非黑即白,而是非黑非白,也可黑可白。“与”是一个过渡,一种联系,也是一堵阻隔的墙、一块狭路争斗的领地。“与”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变项,一条逃走的线,从僵化的二元对立之中逃走出来的线路。
(罗贵祥:1997:67) 将以上的引述座落至洪凌〈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水晶眼〉,藉由“与”字的联系,或许也产生了另一种诠释的可能性,亦即,把“理论与小说”的关系类比为“黄蜂与兰花”的遇合,不是单向的将小说当作理论的展演,或是将理论视为小说的证成。如同水墨与纸片的交融渗透,“与”浸润、形构出了一个in-between的战场,“理论”与“小说”不再是可断然二分的场域。
在第三节,藉由对布西亚理论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挪用,笔者试图呈现这两篇小说与理论互涉所形塑出的一种交相缠绕、一种对话的复杂状态。经由“与”字所开拓出的这个难以被界定、随时随地都在流变的疆域里,〈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和〈水晶眼〉显露的不仅是逾越文类的可能性,也是一种变向的过程,一种对于现世的介入和政治性的实践[41]。 例如,将这两篇小说与性别理论做联系,可使得某一种特别的性别主体得以有现身、发声且被听闻到的可能性:奥梅嘉之于阿尔法,从后者的客体性存在到小说终局完全成为一个握有自我掌控权,不再依附任何外于“我”的关系,不再需要任何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主体来定义、证成自我。简单地说,“最初与最终的阿烈孚”这系列故事写就成的奥梅嘉/拉比丝,暗喻了一个在性别政治脉络中崭新诞生的能动主体,扬弃了对真实、原初一类固定不变本质性存有的追寻,转而积极拥抱、寻求随时可变异的身体与身份: 游牧并不代表无家,或者,强迫性的移位;而是一种主体的图像,她已放弃了所有对于稳定固着的想法、欲望或者乡愁。这种图像表达了一种对于变迁,持续的推移,协调的改变,所造成的认同的欲望,没有,也不要本质的统一。[42] 奥梅嘉/拉比丝在自爆后进入的另一种生存境域中,虽失去了原先那只因灌注了阿烈孚生命而生的红色眼睛,却依旧以仅有的“视欲”观看着一切。在交错的网路空间中,她变成散落的意识、一股“凝视的欲望”,迹近于布莱朵缇所指出的“游牧”生存状态[43]。欲求进入可任意变形的身体与身份,也直截表明了不再执守于一单一的认同,奥梅嘉/拉比丝的认同毋宁像是复杂的多条线路偶然交会出的某一点,其主体性是由多重的复杂面向所构筑的不透明体。这样的游牧表明了“对于疆界流动的肯定,一种在间隔、交界面与缝隙的实践[44]”,在这两篇小说中,正可读出这样的况味。另一方面,奥梅嘉/拉比丝在故事中总是自由无所顾忌的注视着一切,到故事终端更化作“一枚视欲”,就像是“当你注视着深渊,深渊也在注视着你”一般,这则“最初与最终的阿烈孚”,反转了日常生活境况中看与被看的状态,在回视的目光中,主、客易位。 回到一开始那句引文。书写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实践和对现实世界的介入,以双头蛇自体交尾、互噬的意象所形构出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情节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是策略也是目的,小说的反抗就置于它自身的形式之内。 [1] 帕特里莎.渥厄:1995c:13。 [2] 需略指出,是“十二月”而非其他月份。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过后便进入了千禧年,作者将故事发生的时刻设置在这个时间点,让读者生发了更多的联想。 [3] 纪大伟在《肢解异兽》一书的序中说:“〈记忆的故事〉中的双头蛇互噬意象,就不妨视为双线情节的象征。这一对对的情节,像是莫比斯环的两个面: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图案,实际上却共生共灭。”(1995b:9)。〈记忆的故事〉即〈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的前身,两篇文本没有太大的差异。 [4] 这样的写作手法与日本动画系列故事的操作方式强烈相仿。 [5] 文本中的例子:阿尔法与贝塔相互凿刺在左颈侧的“水晶徽记”、那玫雕镂着“玫瑰花形的水晶记号”、水晶党、“水晶眼瞳”、插在奥梅嘉脑中的“水晶磁片”、从“水晶石到红色眼睛”那无中生有的终极创造、“晶片也就是水晶碎片”……。在这两篇文本中,水晶、眼睛、晶片、记忆常常彼此指涉,但相互间的意义并无法完全叠合;从篇名即可得知这几个关键词的重要性。 [6] Almighty,字词本义是“全能的”。文本中“奥曼帝”公司化腐朽为神奇,实不愧为“宇宙时代的炼金术师”,文本中的“我”——奥梅嘉——就是奥曼帝公司(发音念得含混一点,奥梅嘉和奥曼帝还颇为近似),而奥梅嘉(拉比丝)又是炼金术师阿烈孚(阿尔法)以生命灌注而生。宇宙时代的炼金术师—奥曼帝,即奥梅嘉:古典时代的炼金术师—阿烈孚,即阿尔法;阿尔法(阿烈孚)又与奥梅嘉(拉比丝)既同一又分裂。字词的本义在文本中有多重迭生的复义。 [7] 或作“安斐丝拜那”(2002c:127)。 [8] 参见注1。 [9] 纪大伟:1995b:9~16。 [10] 纪大伟:1995b:9、11。 [11] “…我们的晶片是一体两面…”(洪凌:2002b:123) [12] 洪凌在眼镜蛇与神火鸟的地狱探戈一文提及说:“本篇(笔者按:即〈焚烧的星〉,收录于《异端吸血鬼列传》)的主角基度山公爵是我探索‘执念’的第一份抽样报告。除此之外,这里多少也触及主控(domination)与屈从(submission)角色之间的权力脉络(基督山与赫迪斯的关系)。”(1995a:210)。笔者以为洪凌这两篇小说一样展现着诸如“执念与爱欲”、“主控与屈从”等概念,详后。 [13] 洪凌:2002b:123、124。 [14] 洪凌:2002b:124。 [15] 纪大伟在〈莫比斯环的双面生活——阅读科幻洪凌〉一文中提及洪凌深好的一位德意志哲学家Max Stirner,相信在这两篇文本有许多与其哲学交互作用之处可进一步探究。 [16] 洪凌:2002b:123。 [17] 洪凌:2002b:104、107。这部份主要受惠于琬贻在“文学、理论与身体”的课前提问、晓惠的〈服食、感官、生化与再生〉一文,以及2003/4/29课堂讨论的启发。 [18]洪凌:2002b:104。 [19] 上野千鹤子:1995b:141。 [20] 洪凌:2002b:104、120。 [21] 洪凌:2002b:105、107、108、120。 [22] “我和你竟有如此的执念,把游戏玩到这个地步。”(洪凌:2002c:138)。 [23] 关于“着魔”还有一个联想可以帮助说明。电影霸王别姬中张国荣所饰的程蝶衣有句台词:“人不疯魔不成活”。Obsession反而是结构之所以能运行的根本,或该说是之使结构之所以为结构,成活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着魔,甚至当把着魔视作成活本身,取代成活。另外,奥梅嘉被设定为雌雄同体,而“恶魔具有两副性器官”(2002c:143)。 [24] 偶然在《物体系》中翻到这样的句子:“不是”具有”的体制”,而是”存有”的体制”(布西亚:2001b:115),得到灵感,挪用来作为“绝对我”的理解。另,文本里诸如“疲乏”、“自爆”等等的字词,以布希亚的理论作为进路,应该可以得到更贴切的诠释。 [25] 关于这个段落,请进一步参考刘人鹏〈在“经典”与“人类”的旁边:1994幼狮科幻文学奖酷儿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一文的页20及其下的注脚43。 [26] 洪凌:2002b:110。 [27] 洪凌:1995a:209。 [28] 同注20。 [29] 陈光兴:2001a:197。 [30] 陈光兴:2001a:196。 [31] 作者(陈光兴)括引布西亚的话,同注27。 [32] 见〈迈向后现代性的布希亚〉一文,页150(1994)。该文译者将simulation译为“拟象”,而〈后现代(媒体)社会的解剖师——布西亚〉一文的作者则将之译为“拟仿”,本文从后者。 [33] entropy。据〈迈向后现代性的布希亚〉一文的译者注解:“通常译为熵,热力学第二定律。其定理乃是指:物质与能量只能以一种方向改变其形式——由可用转变为不可用、由秩序到混乱。每当一个事象发生,就有一定量的能量永远地消散(不是消失)了。如果要回复其原本状态,只有使用更多其他的能量才能达成,但如此一来又会造成更多能量的消散。今从任觉民的译法——能量永远趋向疲尽。”(1994:151)。 [34] 布西亚语,见其于1988年写就的〈西元两千年已经来临〉。转引自〈迈向后现代性的布希亚〉一文(1994:170)。 [35] 洪凌:2002c:153。 [36] 布西亚曾为价值设定了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为“碎形阶段——已不再有任何指涉对象”。请参阅〈迈向后现代性的布希亚〉一文页173、174(1994)。 [37] 有些不合适在正文出现的联想。在这一小节中关于布西亚几个重要概念的理解主要来自〈迈向后现代性的布希亚〉一文对布西亚理论的诠释。在此文中读到几篇布西亚著作的篇名,两个例子:1983年的《宿命策略》(此文作者说:“布西亚建议我们要更加地像物、像客体,拨除我们自己那种主体性的幻觉与傲慢。”也括引了布西亚的话:“我们应该放弃这种主体的策略,改而采行客体的‘宿命策略’”。另外,据此文作者说,该书的封面就放了布西亚最钟爱的题句:水晶复仇!)和1988年的〈西元两千年已经来临〉(此文作者说布西亚详尽的在文中评论了历史的终结)。纯粹是种感觉,因为未曾真正读过布西亚这些篇章无从确认,但光是从这些篇章名和一些片段的语句,都像是跟正文里诠释的两篇小说跳着双人回旋舞似的,彼此证足。 [38] 这部分讨论受惠于刘人鹏〈游牧.性别.主体性——《庄子》用言方式“与”性别政治〉一文,收录于《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2000:229~282),对“与”字的讨论与使用,也请进一步参考此文。另一方面,洪凌〈水晶眼〉中有关于“花朵与蛾”(2002c:128~129)的书写,两相加乘之下遂产生了“理论‘与’小说”此节。 [39] 转引自刘人鹏〈游牧.性别.主体性——《庄子》用言方式“与”性别政治〉(2000)一文的页233,采用的是罗贵祥对于德勒兹的诠释,据该书注脚10:罗贵祥《德勒兹》(台北:东大,1997)页67。 [40] 此处的笔者指刘人鹏,参上注。 [41] 〈迈向后现代性的布希亚〉一文的作者对布西亚的理论有着强烈的批评与不满,处处可见嘲 讽,但却也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话:“不过,用超社会学(trans-sociology)——犹如科幻小说般地幻想潜在未来和形势的进展——一词来形容布西亚的研究可能更精确。有一种解读布西亚的方式是真正有用的:将他并列于赫胥黎(Aldous Huxley)、欧威尔(George Orwell)以及电脑叛客小说(cyberpunk fiction)之林,而将他的作品看成是对于潜在未来的一种逆乌托邦式(dystopic)的投射。”(1994:180)另外一段是:“我们可以将布希亚最好的研究与巴勒德(J. G. Ballard)、狄克(Philip Dick)、吉卜生(William Gibson)等人的小说、以及电脑叛客小说并列共读。它们都投射出未来学式(futuristic)的世界观,以说明现今的高科技社会。”(1994:182)。 [42] 布莱朵缇(Rosi Braidotti)语。转引自刘人鹏〈游牧.性别.主体性——《庄子》用言方式“与”性别政治〉一文(2000:266)。 [43] 参上注一文的页266~268。 [44] 同上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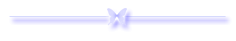
|
参考书目 洪凌〈眼镜蛇与神火鸟的地狱探戈〉,《异端吸血鬼列传》页209、210,皇冠,1995a。 洪晓惠〈服食、感官、生化与再生——洪凌〈记忆是一座晶片墓碑〉的身体与历史〉,2003a。 纪大伟〈莫比斯环的双面生活——阅读科幻洪凌〉,《肢解异兽》页9~16,远流,1995b。 陈光兴〈后现代(媒体)社会的解剖师——布西亚〉,《当代社会思想巨擘:当代社会思想家》页188~209,正中书局,2001a。 刘人鹏〈游牧.性别.主体性——《庄子》用言方式“与”性别政治〉,《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页229~282,学生书局,2000。 尚.布西亚《物体系》,林志明(译),页20~22、101~105、112~117、119~120、 139~143,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b。 上野千鹤子〈镜子国度的自恋〉,《裙子底下的剧场》,洪金珠(译),页123~157,时报出版,1995b。 史帝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迈向后现代性的布希亚〉,《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第四章,马彦彬(译),朱元鸿(校订),页141~183,巨流出版社,1994。 帕特里莎.渥厄《后设小说——自我意识小说的理论与实践》第一章,钱竞、刘雁滨(译),页1~23,骆驼出版社,1995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