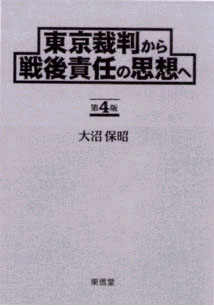|
評大沼保昭的《從東京審判到戰後責任思想》 |
||
|
作者:宋志勇(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大沼保昭:《從東京審判到戰後責任思想》(東京:東信堂,1997)。 日本著名國際法學者、東京大學法學部大沼保昭教授1985年出版了《從東京審判到戰後責任思想》,1997年該書已出到第四版,收集了大沼教授80年代至1997年關於東京審判和戰後日本戰爭責任的論文及評論。 大沼教授是日本研究東京審判的先驅,從70年代開始就從國際法角度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東京審判、戰後日本戰爭責任的論著和評論,在學術界和社會上都有很大影響。《從東京審判到戰後責任思想》主要從法學及思想角度探討東京審判、戰後責任等問題。該書由五編組成:第一編東京審判;第二編從戰爭責任論到戰後責任思想;第三編戰後責任思想的實現;第四編戰後補償與慰安婦問題;第五編爲附錄資料。由於該書所收文章主要是面向大衆寫的,所以不僅有學術性,而且淺顯易懂,受到社會各界好評。 一
東京審判與戰後責任 對於東京審判,日本乃至國際學術界長期存在著兩種對立觀點:一種是肯定論,認爲東京審判是反法西斯盟國對日本侵略者"正義的審判",是"文明對野蠻的審判",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法律上都是進步的,應該充分肯定。另一種是否定論,認爲東京審判是戰勝國對戰敗國日本的"勝者審判",它既無中立國參加,又無當時既存國際法的充分依據,因而是"不公正的審判",應予否定。在對比研究上述兩種對立觀點後,著者認爲,不能簡單地、片面地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東京審判,而要以積極的態度去看待。從客觀效果上看,東京審判揭露出大量不爲人知的日本對外侵略戰爭的歷史事實;從國際法的角度看,東京審判在法律適用上雖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其對國際法發展的積極意義也是不可否認的。如它提出、實現的國家領導人對發動違法戰爭負有刑事責任的新法律概念和實踐,對國際法的發展就具有積極意義。此外,東京審判還促使日本國民反省自身的戰爭責任,這是因爲日本發動十五年對外戰爭不僅僅是國家領導人的責任,它更是一場全民總動員的國家總力戰。在處理戰爭與國民的關係方面,東京審判也具有"重大意義",這就是協助侵略戰爭或屠殺平民等重大犯罪,即使它是按照國家法律行事,也不能免除實際犯罪者的罪責。 對於東京審判的評價,著者在積極地肯定其進步性的同時,也指出其中的不足,但給人的感覺是對東京審判的進步性的闡述仍然不足。評者以爲,東京審判的進步意義是巨大的,是東京審判的主流。縱使東京審判的精神後來被一些戰時盟國損害,但其確立的國際戰爭犯罪的基本原則已爲多數國家接受和認同,戰後聯合國大會及國際法委員會通過一系列關於國際戰爭犯罪的決議和條約,都體現了東京審判的積極精神,從原南斯拉夫國際戰犯法庭的設立到國際刑事審判法庭規程的制訂都能看到東京審判的積極影響。因此,應從更廣闊的視野去把握和評價東京審判。 著者在本書中闡明瞭自己的歷史觀,他認爲二十世紀30、40年代發生的那場戰爭具有兩個面相:一方面是英、美與日本之間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即便是帝國主義戰爭,日本也是戰爭的挑起者);其二是日本在對以中國爲首的亞洲國家的侵略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是不容否認的。面對這場具有兩面性的戰爭應實事求是,尤其不應以帝國主義戰爭性質的一面來掩蓋日本對中國等亞洲國家侵略戰爭性質的另一面,並以此推卸或否認日本的戰爭責任。對於80年代出現的否定東京審判的傾向,著者認爲其中的許多理論,"遠比三十五年前東京審判辯護方提出的理論還粗糙"。應該說,著者的戰爭性質評價和歷史觀是公正的。 但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在論及戰爭稱謂問題時,著者肯定了"十五年戰爭史觀"是正確的歷史觀,並批評了"太平洋戰爭史觀"和"大東亞戰爭史觀"掩蓋了侵略戰爭的性質,但他在文中卻主要使用了"大東亞戰爭"的稱謂,且無特別的說明,讓人感到費解。 二
關於戰爭責任論和 戰後責任的思想 戰爭責任論是戰後日本長期爭論的焦點問題,著者在書中表述了這樣的觀點:東京審判(包括乙級戰犯審判)雖然處罰了日本的戰爭領導人和重大戰爭罪犯,但是日本國民儼如旁觀者,忽視了自己參與戰爭的責任。此外,作者進一步反省,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民逐漸形成的"脫亞入歐"思想和蔑視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傾向,是日本侵略中國及其它亞洲國家的思想基礎。 戰爭結束後特別是東京審判開始後,日本就開始了關於戰爭責任的討論。著者認爲,戰後初期日本關於戰爭責任的討論,壓倒性地將之侷限於日本國內問題,"缺乏對其他民族的責任意識"。究其原因:一是國民長期遭受戰爭痛苦,大都有受害者意識,易於追究造成這種悲劇的日本方面的戰爭責任;二是日本發動的戰爭毫無疑問是罪惡的侵略戰爭,人們失去了深究的興趣;三是東京審判及乙級戰犯審判已懲處了主要的戰犯,有些人産生了既然有罪的都已受到處罰,沒受處罰的就沒罪的思想;四是在戰爭責任論的探討中,沒有進行嚴密的理論論證和操作。 作爲法學思想學者,著者還從思想深層論述了戰爭責任問題。他指出,戰後以來,人們往往把"大東亞戰爭"作爲日本歷史上一次異常、特殊的個別現象來看待,這是不夠的。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發動一系列侵略戰爭,其思想根源主要來自於日本社會的"脫亞入歐"意識。著者認爲,明治維新以後,"脫亞入歐"意識是"貫穿近代日本歷史的具有統治地位的觀念形態"。這種意識紮根於日本社會之中,建立在弱肉強食的原理之上,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歐美的劣等感(競爭),另一方面是對亞洲國家的蔑視感(侵略、利用)。"大東亞戰爭"即是"脫亞入歐"路線的無止境的延伸,它不惜以犧牲、侵略亞洲換取日本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因此,日本的賠償不應僅僅是面向個別受害者,更應清除引導日本走向錯誤方向的根源。應該說,著者從思想角度對日本侵略戰爭根源及戰爭責任的分析和追究是深刻的、有說服力的。 三
關於戰爭賠償及補償問題 戰爭賠償問題不僅是法律和歷史問題,還是政治和道義問題。戰後《舊金山和約》及其它相關和約解決了國家間的戰爭賠償問題,但民間賠償並沒有徹底解決,各國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及民間企業提出戰爭賠償的訴訟一直不斷。對此,著者認爲,日本戰後賠償存在著兩大問題:一是賠償額輕。據統計,到1977年結束支付戰爭賠款爲止,日本總共支付戰爭賠償額不過一兆日元,而到1992年,日本政府對日本戰爭犧牲者支付的補償達33兆日元,兩者懸殊莫大。二是法律問題,即國家間的賠償雖然解決了,但個人請求賠償的權利並沒有消失。這一點,在日本的國會答辯中也已承認。但是,日本的法院應如何判決外國受害者的個人訴訟請求,在法學家中也有爭論。一種觀點認爲,如果把個人的請求權作爲實體權利和手續權利來認定,國家間的權利和義務問題就永遠沒有完結。另一種觀點認爲,個人的實體權和手續請求權並沒有全部被國家吸收,仍掌握在個人手中。但實際上,日本的法院只是消極對應外國人的賠償權利請求,原告方獲勝的可能性很小。著者在書中的基本觀點是,從國際法角度,日本與戰爭受害國間的賠償問題已基本解決,但民間賠償問題仍現實存在,而且日本道義上的戰後賠償問題並沒有結束。 作者在肯定日本政府應對戰後遺留的戰爭賠償及補償負有重大責任的同時,亦提出"全體國民參加戰後補償"的口號,呼籲每一個日本國民都應認真對待並承擔戰後賠償或補償的責任。 著者十分重視亞洲,認爲日本應對亞洲戰爭負責任。他在著作中反復強調這樣一個觀點:在美國的左右下,東京審判無論在法庭組成、確定戰犯還是法庭審理等方面,都以日、英、美戰爭爲中心,反而對戰爭的主要受害者--亞洲國家--明顯不夠重視,這也是東京審判的不足之處。日本與英、美之間的戰爭雖有列強爭奪霸權的一面,但日本對中國的戰爭則完全是侵略戰爭;日本在朝鮮、臺灣實行的是殖民統治,對東南亞各國人民也犯下了嚴重罪行。但是,長期以來,日本對亞洲國家存在著輕視或歧視心理,仍擺出日本帝國主義時代"亞洲解放者"那種高高在上的姿態,對那場侵略戰爭缺乏罪疚感。著者還尖銳批評戰後日本對東南亞的賠償問題。1951年9月《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日本向東南亞的受害國進行了有限的賠償。對此,著者認爲,由於缺乏反省侵略戰爭的意識,此類賠償僅僅是經濟發達的日本對經濟落後的東南亞的"經濟援助",是日本向東南亞推銷過剩産品、擴大商品巿場的良機。著者認爲,這與戰前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理念同出一轍。 評者以爲,在戰爭責任和戰後補償問題上,日本應向德國學習。雖然戰爭已過去了半個世紀,但德國政府和國民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的戰爭責任和對戰爭的反省。納粹戰犯至今仍被通緝,政府和企業正在籌措補償勞工基金,用以救濟、補償那些戰爭受害者。這與日本以國際條約已解決了日本的戰爭賠償問題爲由,將民間索賠請求拒之門外的態度形成鮮明對照,嚴重影響日本的國際形象。日本政府和相關企業應積極考慮著者提出的對戰爭責任和戰後賠償的主張。 四
歷史教科書問題 說到80年代的中日關係,就必須談到日本修改中學歷史教科書的問題,這是當時影響中日關係的一起重大事件。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對日本史等社會科的教科書提出修改意見,要求將書中就日本對外"侵略"的記述改爲"進出"等,對南京大屠殺也提出了歪曲事實、避重就輕的修改意見,引起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對於這一問題,著者認爲教科書問題的發生,是日本在野黨、工人運動及新聞界等批判勢力弱化、保守勢力擡頭和政府指導力不足造成的。對於國際社會的嚴厲批判,日本的一些政府官員和右翼份子說是"干涉內政"。對此,著者指出,國際社會對日本修改教科書的批判與干涉內政是不同的兩回事。"所謂干涉內政,是對他國的政治採取強制或威脅的方式進行干預。僅僅進行批判並不非干涉內政"。而且,日本在《日中共同聲明》中正式承認過去發動戰爭對中國造成重大傷害,並對此"深刻反省"。如果日本在國內採取了有悖於共同聲明宗旨的政策,中國提出糾正要求在國際法上是理所當然的。而且,逃避使用"侵略"這種貶詞來表現日本歷史的態度,是明顯違反共同聲明精神的。 著者在批評日本政府及保守勢力強化對教科書的檢定的同時,也談到了新聞界、輿論界及一般國民所負的責任。指出教科書檢定問題由來已久,但並未引起社會輿論和普通國民的重視,當外國提出抗議和交涉時,大家才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時社會輿論又一股腦地批判政府,而忘記了自己監督和制止的責任。 對於歷史教育,著者提出應抱"直視過去"的態度,告訴孩子自己的國家在過去曾幹過錯事、惡事。"既然人會犯許多錯誤,而人運營的國家就不可能不犯錯誤。的確,我們的先人爲日本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這並不能勾銷日本對其他民族犯過錯誤這一事實"。"過去的歷史不能再現。正因如此,我們豈不更應把自己所犯的錯誤告訴我們的子孫後代,教育孩子們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嗎?"著者正確的歷史教育觀和坦蕩的胸懷令人敬佩。 五
薩哈林朝鮮人問題和補償慰安婦 著者不僅是學者,還是富有正義感的社會活動家,他把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落實到國民承擔戰爭責任的實踐中。著者曾積極發起、參與了對薩哈林朝鮮人的救濟支援和從軍慰安婦補償的活動,並且取得很大成果。 薩哈林的朝鮮人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戰爭結束時被遺棄他鄉。在著者及其同志的推動下,日本政府終於在戰爭結束45年之後決定協助薩哈林的朝鮮人回鄉探親掃墓及歸國定居。當2000年3月26日河野洋平外相來到漢城郊外,視察剛剛由日本政府出資建成的薩哈林歸國朝鮮人"故鄉村"時,那些飽經戰爭苦難的歸國朝鮮人雖然批評日本政府在戰爭結束了半個世紀之後才了結這筆歷史舊帳,但還是向河野外相表示了謝意。薩哈林歸國朝鮮人問題較爲圓滿的解決對我們有兩點啓示:一是日本的戰後責任問題並沒有結束,許多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亟待解決;二是戰後責任問題的解決需要朝野各方面的努力,尤其需要民間有識之士的積極推動。 慰安婦問題是戰後遺留的重要問題之一,也是日本侵略戰爭中可恥、罪惡的一頁。爲解決這一戰爭責任問題,著者與其同志多方奔走,宣傳募捐,爭取到村山、橋本兩屆內閣的合作,建立了"亞洲女性基金",向那些曾受日本軍國主義淩辱的慰安婦道歉並提供補償。儘管對"亞洲女性基金"有種種議論,基金的發展和運作也不盡順利,但著者作爲日本國民,其正義感和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值得欽佩。這與那些否定日本的侵略戰爭性質,否定慰安婦問題的罪惡性質,千方百計爲日本的侵略戰爭暴行辯護的日本右翼份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東京審判雖然已過去了半個世紀,但正像著者所說,日本的戰後責任還遠沒有結束。 原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1年4月號(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第144-148頁。 《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 上網日期 2001年06月01日 |
【臺灣論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