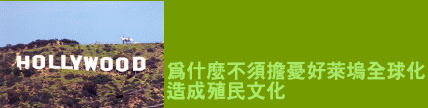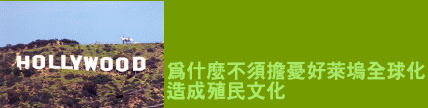|
廖咸浩/臺大外文系教授兼主任
最近,加入WTO的倒數計時,讓臺灣以至全球的全球化狂熱都沸騰到了最高點:似乎全球化已近在咫尺,太平盛世唾手可得。但同時,反全球化的風潮也在全球隱然成形。姑不論其是否有過激傾向,其對全球化(或曰第一世界所主導的全球化大計)的盲點,不容置疑的有深沉的開光作用。流行的全球化論述,完全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而且從第一世界位置發言,故總是一味的粉飾太平,把全球化的經濟未來描繪成前所未有的玫瑰花園。如此不但把各地下層階級在全球化中的命運置之不理,也把經濟以外(尤其是文化)的衝擊視若不見。
實則文化所面對的前景,即使未必如下層階級的經濟命運慘淡,也有大量可類比之處。最樂觀的研判是:非第一世界的文化已面臨了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大壞是必然,大好,則端視各地文化人的智慧與膽識。
晚近常聽到的全球化文化論述,不是經濟的附庸(如學好英文以增加國家競爭力)或經濟的假面(如加強包裝以將在地文化推上國際舞臺)。即使如在地化之類批判論調,也是從第一世界商機思考出發,與前述文化包裝論血緣極近,因此在地化論者對全球化的批判常淪為「全球就是在地,在地就是全球」這種對全球化的肯定。
較具文化層次的文化遠景則多半是植基在所謂後現代的「雜化」(hybridity)論述上。時代週刊曾在論及00七新片時,興奮的指出:亞洲出身的楊紫瓊能在好來塢電影中擔綱,證明全球化時代已然來臨。香港導演打入好來塢、李安得獎又強化此一論點。近期時代週刊對於亞洲各國的文化與種族混血,更是吹捧有加不遺餘力。
這種論述其實在世界各地的知識界俯拾皆是,但來源卻是第一世界。雜化本身無罪,但什麼人在提倡?該誰來提倡?應在那裡提倡?用什麼方法實踐?都值得深思。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都不缺對小規模混血的興趣,但也都對大規模的混雜心懷戒懼。但第三世界的戒懼有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創傷背景,第一世界則因其殖民時期以來的優越感作祟;第三世界樂於與洋人混血,見證現代性壓迫造成的自卑感之深重難消,第一世界則是因後期資本主義時代,需要善用混血人以加速資本的跨國流動。兩者之雜化雖早已有之,但如何在兩者的情境中繼續運用雜化,便不能不慎,也不可一概而論。
雜化這種大鍋熱炒的文化想像,在一定程度上或條件下,的確可以為文化帶來活力。但無限上綱的擁抱這種後現代暈眩,卻難擺脫雜化觀為跨國資本主義作嫁的初衷。一個遭全球化文化自二十世紀初開始衝擊至今,早已無根無本、漸趨衰頹的弱小文化(這是第三世界或「前第三世界」─如臺灣─的普遍的現象),若仍毫無警覺的與全球化文化這匹巨獸持續貼面共舞,最初或能陶然忘我,最後終不免失去自我。「自我」的說法並不意味著文化有一個僵固單一的主體。文化「自我」的意義在於:若在地文化沒有往四方八面深入紮根,雜化就不會是我們想像中的具有整合性的、操之在我的混雜,而是被全球化文化的全面吸收。
或曰:「有那麼嚴重嗎?」歷史上有多少文化也都消失了,而必如此在乎?更何況人類也總有自同中生異的能耐,普同化豈有如此可懼?當然,歷史若從百年後回顧,本來就輕如鴻毛。但若我們記取班雅民的說法:每一個文明都是野蠻的結果,那麼,歷史的演進或文化的變遷,就不能只論結果、不看過程。適度的普同文化固然可以增進瞭解的可能,但其過度擴張──我們從啟蒙思潮所得到的教訓是──就會造成壓迫,以致於野蠻(近例是西方殖民主義
)。更何況,當前人類所面對的資本主義普同化力量,是媒體科技不存在或初萌發期無法相
提並論的。
強調慎用雜化觀念,並不意味贊成保留地式的文化觀,更不是陳倉暗渡右翼的本質主義式文化觀或國族主義的櫥窗式文化觀。批判全球化是從救急救難角度、從文化生態的角度出發,就公義、活力與生趣等大原則進行反思。自然生態失衡會造成全球性災難,文化亦然。內容空泛的大型連鎖書店對專業書店的滅絕壓力,正是此文化危機具體而微的顯現。
迎向全球化是不可避免趨勢,也對世界的向上提升有一定的裨益(如透過像網路等全球化機制促進知識的民主化或批判力量的廣泛結盟)。但第一世界對此的過度美化,必然造成文化發展的野蠻進程。在全球化的前夜,如何回到(複數的)傳統,以增進在地文化(多元的)「紮根」能力,來強化在地對普同化文化的批判能力,及對另類全球化視野(如與非歐美主流文化的對話)的開拓能力,是知識份子份子不可掉以輕心的任務,也是政府必須從文化政
策角度加速思考的迫切議題。
【2001/11/12 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