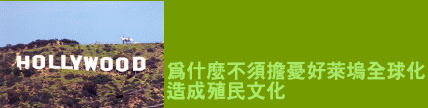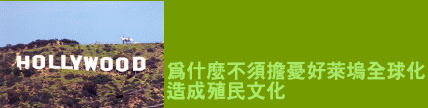|
好萊塢電影在世界範圍內大行其道,已是不爭的事實。愛德華-布拉尼根教授是當今歐美電影理論界的著名人物,作爲一個美國學者,他絲毫不爲這個現象感到欣喜,相反爲此而擔憂,擔憂其極端的商業化會阻礙電影作爲一門藝術的創新和發展,擔心這樣會使世界文化變得單調。在他以及很多西方電影理論家看來,很多亞洲電影是值得稱道的,他們認爲,當今世界最偉大的4位電影導演全在亞洲:中國臺灣的侯孝賢、中國香港的王家衛、伊朗的阿巴斯-基亞斯塔米(abbs kiarostami)及日本的北野武(takeshi kitano)都是大師級的人物,著名的電影理論家波德威爾正在寫一本有關侯孝賢的書。
專家自有專家看問題的立場和眼光,本報記者專程於美國聖芭芭拉市採訪了布拉尼根教授,並非想要以學術化的角度來衡定普通觀衆看電影的標準,但從這位美國學者的觀點中,我們可以換一種角度來看待好萊塢電影和它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或許還可以回過頭來對我們自己民族電影工業的發展做些許粗淺的思考。
■受訪者:愛德華-布拉尼根 ■採訪者:本報記者劉淨植
■好萊塢電影直接靠影像來吸引人,不需要人們動很多腦筋去思考內容,這與大多數觀衆看電影時想要放鬆、追求直觀刺激的心理需求是相符的。
記:您認爲好萊塢電影擁有如此衆多觀衆的原因何在?
布:好萊塢主流電影之所以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是由於其傾向表現簡單的喜、怒、哀、樂、愛、恨等情感,以及暴力、性愛等人類的基本行爲活動。這些電影在類型上已有定式,技巧上追求圓熟連貫、不露痕迹,觀衆熟知這類影片的套路,並從預期效果的實現中獲得滿足感。它直接靠影像來吸引人,不需要人們動很多腦筋去思考內容,這與大多數觀衆看電影時想要放鬆、追求直觀刺激的心理需求是相符的。這些主流的類型片往往把實際生活中的問題簡單地程式化了。要知道,好萊塢電影賺的錢有一半來自美國以外的全球市場,這樣當你面向全世界觀衆拍片的時候,便要注重挖掘人性中普遍的心理和需求,而很容易忽略一個國家獨立的歷史和文化,這種傾向性實際上損傷了電影的價值。
記:您的意思是說好萊塢主流電影的商業價值損傷了其藝術價值,藝術和商業之間真的如此對立嗎?
布:即使是像《美國麗人》這樣在好萊塢影片中顯得較有思想性的作品,裏面也有很多俗套的地方,過分地戲劇化,又涉及到謀殺……所以它和藝術電影是有區別的,我們可以拿侯孝賢的《海上花》來舉例,《海上花》的敍事結構非常複雜,表現也非常含蓄,它要傳達的資訊不是一目瞭然的,它的每一場戲不但需要觀衆重新理解敍事結構,同時還需要觀衆有歷史感。《海上花》表現出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蘊,而這是主流美國影片所缺乏的。美國影片大多不具有歷史感,不大擅於表現過去,沒有鼓勵觀衆去思考過去如何影響了現在的發展,他們太傾向於表現當前的生活狀態,而在這一層面上又過於誇大其辭。
■當好萊塢文化佔據優勢時,實際上是孤立了自己
記:多數觀衆看電影只是希望放鬆一下,這樣的藝術電影是否對普通觀衆提出了過高的要求?
布:若要真正嚴肅地探討生活中紊亂複雜的問題,就需要人們動腦筋加以分析,分析問題的電影向觀衆提出了超出基本視聽的要求,即此種電影需要被藝術地理解,觀眾必須推斷銀幕上沒有直接表現的東西,於未見與未聞處發掘隱含的深意。同時這樣的電影也需要觀衆有歷史和文化的眼光,站得高一點來審視現實,但絕大多數人很難做到這一點,因此這對於觀衆可能是一種超前的要求。隨著時間的推移,未來的觀眾自然會有和當今完全不同的視角,而一些在今天不能被充分理解和欣賞的電影,其藝術價值恐怕到那時才會顯露出來,但是我們今天往往難以分辨出究竟哪些電影在將來會被視為藝術,哪些在探討人們目前普遍思維之外的東西。
記:那麽藝術電影就是拍給未來的觀衆看的嗎?
布:因爲人的價值觀不斷地發展變化,政治、歷史、文化、環境會改變,一些實驗性很強、很超前的電影可能在未來會被更好地理解,比較嚴肅的藝術家總在探索如何用新的手法表現新的思想,來超越現在的侷限,這其中會有失敗,但電影和其他藝術甚至科學是相通的,總是在大量失敗的基礎上有所獲,如果不創新,就會倒退。而藝術家也有不同的類型,有人會創作主流觀衆喜歡的作品,有人則在不斷地探索,努力創新,正是這股力量推動藝術不斷向高處發展。
記:我還是想問您,您認爲既然電影要對觀衆負責,那麽它的娛樂性和思想性哪個更重要?
布:不同的導演永遠會做不同的選擇,即使有人做出硬性規定,也不能限制各種各樣電影的出現,永遠會有爲不同目的而拍出的影片。我在教學生時感到最困難的一點就是讓他們理解電影作爲一種藝術形式的內在價值,因爲電影在社會生活中普遍被當做娛樂而讓大家忽略了這一點。電影的內在價值體現在線條、色彩、剪輯手段、鏡頭運用等方面,同時也反映製片人和導演所代表和要體現的價值觀,更反映他們所處的社會、國家所代表的文化和價值觀。這些不同的價值觀被錯綜複雜地融合在影片中,有時候並非能一目瞭然。好萊塢強大的全球市場對美國觀衆而言是不利的,當好萊塢文化佔據優勢時,實際上是孤立了自己,因爲這減少了美國和其他文化的交流,使自己變得越來越單調。
■美國影評人實際上對觀衆指導性不大,最多影響到第一週票房,在這之後觀眾更願意相信親朋好友的評論
記:美國的影評人是否關注這一狀況?他們的聲音能對好萊塢電影生産産生影響嗎?
布:美國的影評有兩種:一是面對普通觀衆的,另一種是學者影評,絕大多數影評人爲主流報紙、雜誌、電視臺工作,他們和電影界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是好萊塢的喉舌。美國也經常傳出影評家因受各種好處而違心讚揚電影的訊息,這種不是從客觀的角度、而是牽涉了個人利益的評論往往價值不大,以至於會誤導觀衆。不過,評論家所表達的觀點實際上對觀衆指導性不大,最多影響到第一週票房,在這之後觀衆更願意相信親朋好友的評論,許多時候很多影評人衆口一詞評論某部影片差,但觀眾不予理睬,影片的票房依然很好。
而在電視節目上做影評的人還要考慮節目的收視率,在形式上要吸引觀衆,評論中要不斷找出詼諧有趣的話以博取觀衆的好感,而不是在於觀點有多麽深刻。這使得他必須對大多數影片採取積極的態度,如果不斷否定影片,容易使觀衆對節目産生反感。爲了討大衆的喜歡,在評論電影的過程中,評論家本人也在演戲,同時這些評論家的視野也受到很大限制,他們只能評論大多數主流電影。只要影評牽涉到商業利益,與電影工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就不可能作出獨立、冷靜、客觀的評論。學者所寫的影評則有很大的不同,但學者影評只能在知識界的小圈子裏流行,或者成爲教材。不僅電影,其他學科也是如此。
記:在您看來,比較有藝術價值的好萊塢電影有哪些呢?
布:提起美國電影,中國觀衆可能容易只想到好萊塢主流影片及其製造的神話,但美國電影中也還是有不少探索性強、思想性和藝術性都較高的作品,只是恐怕不易為中國觀衆所熟知。如斯蒂芬-索德伯格的《販毒網》、喬爾-舒馬赫的《老虎洲》、吉姆-賈木許的《離魂異客》、泰倫斯-馬裏克的《細細的紅線》、托德-海尼斯的《毒藥》、
葛瑞格-阿拉奇的《玩盡末世紀》等等。其中有些電影反映美國中產階級生活的陰暗面,比紅極一時的《美國麗人》更加深刻透徹。同時,美國還有很多優秀的紀錄片、實驗片及前衛作品,但這些影片在業外很難看到。
■我看張藝謀的影片比較多,是因爲他的作品在西方發行較廣
記:除了侯孝賢之外,您對中國電影還瞭解多少?
布:我很欣賞王家衛的影片,他的電影敍事結構非常豐富,表述比較含蓄,表現形式也令人耳目一新,鏡頭的運用、節奏、通過物象來影射主題等手法都有獨到之處。香港電影在西方非常受歡迎,非常具有獨創性。我也很欣賞張藝謀,我知道他是學攝影的,所以他的影片畫面很美,我幾乎看過張藝謀所有的電影,他的影片在用光、構圖、色彩上給中國電影開闢了全新的境界。我看張藝謀的影片比較多,是因爲他的作品在西方發行較廣,其他一些好的導演如果作品不在美國發行,我們也無從瞭解。這是美國學者和觀衆的損失。這種情況一直如此,比如在50年代,我們能比較多地看到黑澤明的影片,是由於他採用了西方慣用的技巧和莎士比亞名劇的內容,而其他重要日本導演的作品就根本看不到。我對此表示擔憂,別國導演的作品在美國發行是經過嚴格選擇的,這種選擇帶有嚴重的偏見和商業上的考慮,比如伊朗、南斯拉夫、法國等國家的優秀電影就這樣被擋在了美國的大門之外。(攝影/本報記者蕭揚 感謝張颯女士的翻譯和資料提供)
愛德華-布拉尼根教授
(Edward Branigan)
1945年生,美國著名電影理論家,西方電影理論界最新流派——「感知理論」派代表人物。此派理論反對後結構主義對觀衆被動接受與無意識的強調,十分重視敍事接受者在敍事建構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布拉尼根教授主要從心理學的角度研究觀眾對電影的理解和接受,他最主要的代表著作是寫於1992年的《敍事理解與電影》,該書在西方電影理論界影響極大,被視作電影專業及相關學科的教科書。中國最早對他的介紹見於1991年,在當年第2期的《世界電影》雜誌上,刊登了布拉尼根的文章《視點問題》(葉周翻譯)。布氏現爲美國加州聖芭芭拉大學電影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