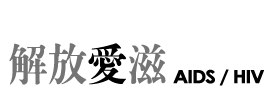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對於愛滋有四個層面的解放意涵。唯有透過這四層的解放 政略,愛滋相關議題才能被認真且有智慧地處理、對待。
第一、愛滋必須從醫學/科學定義的「疾病」解放出來。 愛滋絕非只是一個流行病,而是一個「表意的流行病」(an epidemic of signification)。 從歷史、社會、文化、語言學的角度切入, 我們得知愛滋擁有強大的象徵力量去生產多重鑲嵌卻又相互牴觸的意義與論述。 這些意義與論述的運作,都反應了人們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中如何理解愛滋, 以及不同的身體如何被愛滋這個表意符號 (signifier) 所建構。 愛滋社會文化層面所衍生的課題,並非醫學/科學能夠應對。 因此,我們拒絕把對於愛滋的詮釋權全盤交給醫學/科學「專家」。 對於「醫學/科學 = 客觀事實 = 愛滋的正確觀念」此等向軸線, 也是必須檢視、挑戰、且批判的。
第二、愛滋感染者必須從「受害者」(victim)、「受難者」 (sufferer)、 或「病患」(patient) 的身分角色解放出來。 「受害者」或「受難者」都指涉痛苦與衰敗等負面意涵, 而「病患」的角色定位也把感染者能夠獨立於「醫生」的能動性完全抹殺。 這並非代表政府/醫療單位不必提供完善的治療照顧服務給感染者, 也並非鼓吹所有感染者即刻停止服藥。而是強調我們必須更細緻地去回應 感染者之間的個別差異與權益訴求。 換句話說,這三個身份標籤 (identity labels) 都是以「愛滋」去定義人, 乃至於淹沒了感染者身為全人 (whole people) 的聲音、情感、與需求。
第三、愛滋防治的政策與行動,必須從中央政府/衛生主管機關的主導解放出來。 這意味著相當程度從公共衛生的視野框架跳脫。愛滋涉及的問題層面之廣泛, 絕非一個政府部門能夠掌握,也不是所謂的統計數據可以反映。 而是必須結合愛滋相關民間團體的社群知識與力量, 共同協商面對愛滋的策略。民間團體不但必須檢視、督導官方的防治動態, 更必須貼近社群/人群的真實生活,進一步達到社群內部自我培力 (self-empowerment)、凸顯感染者或易感族群的主體位置。 如此一來,愛滋防治不再只是政策制定者或醫學/公衛人士的操作, 而是大幅度地納入感染者/易感族群的發聲與生命經驗。
第四、愛滋法律的制定與實施,必須從懲戒性的罰則 解放出來。 至今沒有任何有力的證據能夠證實懲戒性的罰則對於公共衛生或愛滋防治有正面的幫助。 針對愛滋感染者所做的處罰 (如: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還蓄意傳播感染他人), 伴隨著媒體對於愛滋感染者的渲染報導,常導致社會大眾把愛滋恐慌以及愛滋防治責任 全部加諸在感染者身上,反而忽略了與感染者發生和議性行為 (consensual sex) 的另一方, 也是整體愛滋防治的重要一環。以懲戒性的罰則為基準,所運作的指控、審判、與定罪與其生產的論述, 常常都和愛滋真正的傳染途徑相衝突。這不但使得愛滋感染者的權益受損, 更給予社會大眾錯誤的愛滋防治知識。因此,我們必須擺脫「受害者/加害者」二元思考 (victim-perpetrator binary) 的束縛,才有可能顧及感染者以及其性伴侶雙方的人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