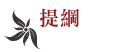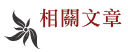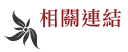摘自〈女性主義的色情/性工作立場〉,《性/別研究》第1-2期合刊,1998: 200-239。
在這次台北市廢公娼的過程中,父權的道德老調接合了帶著女性主義意味的新調,於是我們聽見廢娼人士說:「公娼制度是物化女人身體,把女人商品化」,再不然就說,「娼妓制度滿足男人原始的慾望,投男人之所好,養大了男人的胃口,因此也鞏固了父權對女性身體的操控」。這麼嚴厲的言語一出,廢娼好像是理所當然似的。
不過,在這種女性主義語言之下流動的,倒底是什麼血液呢?這需要檢驗。
第二波西方女性主義在當時左派理論的薰陶下,開始使用「物化」來描繪父權對女人生命的限制和塑造,從這個出發點來說,「物化」批判的現象非常寬廣,用本地的語言來說,包括了:把女人厚實複雜的北港香爐生命,窄化成單一作為滿足男人眼睛的冰淇淋、是準備男人宵夜的自動燉湯機、是孕育男人後代的子宮、是照顧男人親屬的免費看護、是清潔男人衣物的冷洗精、是為男人倒咖啡的侍女、是為男人安排活動的秘書、是為男人設計文宣的學者策士等等。換句話說,當女人缺乏自我的空間,當她的價值由她在男人規劃想像中的定位,以及她所能提供的服務來決定時,這種強制的一廂情願都是「物化」。換句話說,無論是任何狀況(例如台北市片面決定廢娼),只要女人的意願沒有得到尊重,女人的不滿沒有得到聲張,女人的志業無法實現等等,都應該會招來女性主義有關「物化」的批判。 (註一)
可是我們在本地聽見「物化」時,通常不是說女人的人生和發展遭到各種窄化和限制,而只是用來說女人的身體以性感的形象在影像中呈現,或女人的魅力以她的性來表達。換句話說,只要而且只在身體和性相連,並同時在影像中出現時,「物化」的大帽子才會被主流女性主義激情的祭出來。至於中國文化中常見的,把女人視為傳宗接代的功臣、把女人視為優雅溫和的動物、認定好女人對家庭和社區守護有其神聖職責等等非常「物化」女性的作為,似乎就引不起什麼對「物化」的關切。(是啊!我們幾時見到主流女性主義者抗拒國家把社區安全的責任推脫到婦女身上?幾時見到主流女性主義者寫文章支援那些拒絕被調教得優雅溫和的青少女?)
這種差別待遇不禁使我們懷疑,和物化相連的本地女性主義義憤,事實上想做的不是全面抗爭女人的生命窄化,不是全面挑戰傳統文化對女人生命的規劃和枯竭,而只是選擇性的針對一些新生的現象,也就是針對(新的社會經濟現實所促成的)性在女人生命中的逐步立足──不管是豪爽女人的「我要性高潮」,或是青少女的身體自主。而這種對於女「性」的焦慮,恐怕骨子裡和父權的道德老調相去不遠。結果,女性主義的「物化」沒有被用來攻擊父權對所有女性的生涯和身體的規劃侷限,反而被用來攻擊少數某些女人的開闊情慾人生選擇,這也夠諷刺了吧!
還有人說,從娼就是滿足男人的慾望,投男人之所好,養大男人的胃口,鞏固父權對女人的操控,婦女團體和女性主義者怎能支持娼妓制度的存在呢?
問這種問題的人真是找錯了對象,爬錯了樹,頭腦不清。張開眼睛看看你的周圍吧!好家庭主婦體貼她的男人,照顧他的日常生活需要,滿足丈夫的身體需求;好媽媽疼惜她的兒子,供給他各式各樣上進發展累積經驗的機會和資源;敬業的女文員、女秘書、女經理全力支援(屬於男老闆的)公司事業,幫助(男老闆的)公司賺錢,為男性掌權的台灣經濟撐腰;自命有腦筋的女學生、女助理,滿心敬重(一向以男性為主的)智識成就,仰慕(充滿霸權意識的)政治正確的理論辯才,鞏固(男性佔大宗的)學術師道的權威和名望;宣稱為女人謀福利的女策士們,替「號稱開明」的男政客出點子,拉票站台,寫說帖,搞論戰,打擊不同路線不同階級不同利益的女人,用救援之名廢掉下層女人的生計──這些都是在我們左右隨處可見的「體貼男人,鞏固父權」的明顯例子,怎麼就不見問話的人自我質疑一下,自我反省一下呢?
現代的性工業和過去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有愈來愈多女人開始對自己有足夠的自信以及對身體的泰然,以致於她們不怕投身性工業,正是這方面的變化使得我們在面對性工業時必須要有更細緻的策略。現在「已經」有女人──而且很多是年輕的女人──在性工作的領域中拼鬥(不管是做妓女、按摩、公關、陪酒、伴遊、檳榔西施),局勢不見得很好,但是她們最不需要的就是其他女人的自以為義。而當性工作者奮力爭取自主,爭取獨立的時候,女性主義者怎能落井下石,站在廢娼的(男性)政客背後搖旗吶喊呢?
在弱勢邊緣女人選擇她們的人生,選擇她們的抗爭方式時,女性主義只能有一個立場:肯定支持,提供支援。
在西方婦女運動早期,「物化」指的是男人「以性功能和性吸引力來衡量個別的女人,把女人當成物品,不談對等的關係,而把出於男人本位的狂想以及過度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投射到真正的、活著的、呼吸著的女人身上」,其中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絕非專指色情或暴露或性交易。參考Avedon Carol & Nettie Pollard, “Changing Perceptions in the Feminist Debate,” in Alison Assiter & Avedon Carol, eds, Bad Girls & Dirty Pictures: The Challenge to Reclaim Feminism (London: Pluto, 1993) 4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