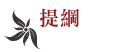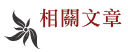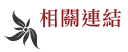物化、身體商品化、異化──這幾個不知所云、人云亦云的名詞,已經變成一切官僚政客、訓導人員、神棍和不學淺識的教授的口頭禪,變成一種毫無內容的空洞咒語或指控標籤。此間對於物化、異化、商品化等概念的歷史與理論之膚淺詮釋與誤解,我不能不遺憾地說,是來自對批判理論傳統的無知;是過去國民黨戒嚴時代思想控制的後果,以致於和左翼階級思惟隔離,再加上思想與研究的怠惰,以咒語口頭禪代替理論分析的結果。在此,讓我精簡地總結這些觀念:
物化──也就是客體化或對象化(objectification)──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物化就是透過人類的組織(社會分工)把某些東西當作和自己不一樣的物(區分物我),也就是把某些東西當作勞動的對象,是可以被控制、分解、操弄、改變、轉型、交換、消費、生產…的東西。一句話:物化就是人的改造自然,所以,物化也就是人化。但是人類的勞動不但物化了自然,也必然會物化自己的身體,亦即為了讓身體能物化自然,就必須也物化身體,使身體可以成為一個可以被控制、操弄、改變、生產…的勞動器官。因此人在改造或物化自然時,也必須順應自然來改造或物化自己。物化因而是一個歷史的進程,是個「人化/自然化」一切(包括自己身體)的辯證進程。當然,人類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採用不同的人類組織和社會制度去進行物化。當大部分人類採取市場機制和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時,也就是物化中的「交換方式」變成了主宰其他物化方式的組織原則的時候,物化就主要地採取了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形式,人們開始用商品化來改造自然與自身(身體、國家、經濟、文化等等)。商品化的形式大大便利了物化的深度、速度與強度,超越了人自我中心的想像,在人的意料與掌握之外物化人與自然。由於人們已經不能有意識地控制這樣的一種形式的物化或商品化,所以也被稱為「異化」(alienation),更有甚者,人們對這樣的「物化─商品化」的實際過程產生了虛假意識,看不出來這個過程依賴著社會分工的特定形式,而以為是交換物本身的特質才導致了商品化的過程,這個把交換背後的人的社會關係誤認為物的關係,這就是reification(有時也被翻譯成「物化」或「異化」)。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相信,當商品化發展到了一個相當高的程度,人類的物化便可以不必採用商品化的形式,並且能夠控制自身的物化進程,並且如其實的認識到這個過程依賴著人與人的社會分工關係。另外,有關女性主義者對「物化」這個名詞的使用與誤用,可參看:Avedon Carol and Nettie Pollard, “Changing Perceptions in the Feminist Debate”, Bad Girls & Dirty Pictures: The Challenge to Reclaim Feminism, eds. by Alison Assiter and Carol Avedon (London: Pluto, 1993), pp. 45-56.
從上述的分析出發,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物化,最原初的概念,是對於雇傭勞動(打工者附屬於老闆)的批判,對於婚姻家庭(妻子婦女附屬於丈夫男人)的批判,是對於掩蓋在勞動契約與婚姻契約中,工人與婦女作為生產工具的批判。物化,是針對社會結構與制度的批判,是對於「常態的打工/正常的婚姻」的批判。但是如今卻往往被扭曲為對於「性偏差」的批判,變成對於性工作、性感工作(女體模特兒)、婚外性愛、另類身體打造的批判,從而隱藏起主流商業、婚姻家庭與良家婦女的物化性格。
物化觀念在應用到性關係時,有著進一步延伸的意義,最為人所知的是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 (請參看相關連結),許多性哲學家也都探討這個觀念。Martha C. Nussbaum在Sex and Social Justice一書中對於性活動中的物化或客體化(objectification)提出了一些辯護,她要說明物化或客體化的某種形式其實是性生活中必要甚至美妙的特色,而且和平等、尊重、同意都能並存的(Sex 214-215)。
Nussbaum認為「物化(客體化)」概念在目前的使用中是多義的,她列舉與分析了「當作一個物或客體」的七種不同含意;「物化」可能意味著(一)「否定對象的主體性」(denial of subjectivity)(可忽略其感覺經驗),(二)工具化(instrumentality),也就是「將對象當作達到我們目的之工具」,(三)否定自主(客體無法自決)、(四)惰性(客體缺乏能動)、(五)可替換性(同類型的別的東西,或者別類型的同樣東西),(六)可侵犯(客體沒有完整疆界,可以打壞或分解),(七)所有權(擁有客體、能買賣)(Sex 218)。
很明顯的,許多上述意義中的「物化」是我們日常生活都常在實踐的。例如,我們不想認識或關心某個線上遊戲的陌生對手或同伴(這就是denial of subjectivity否定對象的主體性),也不認為他不能由別人或機器所替代(可替換性fungibility),或者這個線上遊戲的對手可以被收買或雇傭(ownership所有權),而且我的勝利或贏的快樂可能是建立在對手輸光被打敗的痛苦之上(violability可侵犯),總之我只是利用對方玩玩而已(instrumentality工具化)(以上這些例子雖不是Nussbaum所舉的,但是代表了她所提出的幾個物化的可能意義)。無論如何,只要這個線上遊戲活動是公平互惠性質的,那麼並不因為我們物化對方,或因為我們對待陌生人的「工具」態度,也不因為我們彼此對待方式不同、或所得待遇不同,因而就使我們的活動變成不道德。
還有,Nussbaum對「物化」意義做此細分的目的是顯示:有些物化的含意並不蘊涵其他。所以像SM女同性戀女性主義對SM的辯護就是建立在「可侵犯」但是不損及自主此一事實上(Sex 221),亦即,SM侵犯了對象身體,但是沒有否定對象的自主。此外,父母對待子女的態度上,也是有頗多物化或客體化成份,像將子女當作無法自主的、惰性的,這些當然都是沒問題的。不過另些父母對子女的物化也許就有問題,像可侵犯性、工具性、可替換性、否定主體性。但是Nussbaum自己也承認上述的「有問題」判斷畢竟是西方美國的觀念,在很多地區父母對子女的這些物化方式都可能被接受(Sex 222)(甚至包括擁有子女的所有權)。總之,物化不是一個觀念,而是好幾種相關卻未必彼此蘊涵的觀念。
那麼,Nussbaum要如何看待最常見的一種性客體化的指責──將人化約為性器官?Nussbaum分析D. H.勞倫斯的小說中描述雙方給性器官取名字、眼中似乎只有性器官、甚至將自己化身等同為性器官的場景,但是主張像這樣的情況其實不是給人性「減分」(就是把人簡約為性器官),反而是「加分」──性器官不是一般人認為的「可替代的、非人性本質」,反而是更彰顯人性、顯示獸性也是個人人格的部份(Sex 228-231)。
Morris, Phyllis Sutton. “Sartre on Objectificatio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Jean-Paul Sartre. Edited by Julien S. Murph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