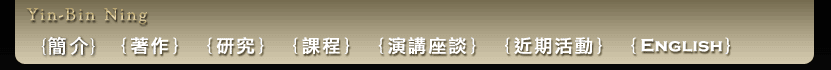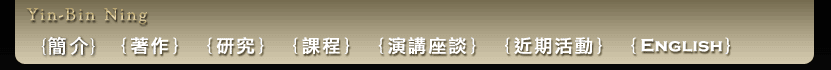代理孕母打破父權的母職觀
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在代理孕母的爭議中,有許多來自婦女團體反對代孕的聲音,但是其實也有一些女性主義者贊成代理孕母的開放。她們至少有兩個理由,一個是代理孕母使女性打破了父權所定義的「母職」觀念;另一個是為了保障代孕工作者的權益。
首先,代理孕母改變了傳統父權所定義的「母職」觀念,使得女人脫離了生物的宿命,免於必須懷孕生產的「天職」,可以和男人一樣,無須懷孕生產也能擁有自己的子女。人們不能再以女人的生物宿命為藉口來不平等對待女性。
其次,雖然代孕者必須和自古以來的女人一樣懷孕生產,但是和千古以來女人不同的是:她不但可以免於養育子女的「天職」,而且她的懷孕生產不是無償的生殖勞動,不是婚姻內的宿命,而是自願的人生選擇和職業選擇,有助於她改善她的人生境況。故而,代理孕母把女人的天職輕易的拆解了,這是古人無法想像的。因為古人沒想到:雖然懷孕生產是隻有女性才具備的能力,但是一旦懷孕生產專業化,就能改變傳統父權所加諸女人的生物「母職」。
「母職」就是包含生殖工作、照顧工作、性工作在內的家務工作,而當這個母職座落在合法婚姻家庭之內時,母職有著一定的正當性,並且受父權的某種程度的保障;父權願意提供有限的保障乃是因為唯有女人受限於婚姻家庭私領域時,才容易被男人所支配,但是這樣一來,女人也因此受限於家庭的私領域。在傳統社會中,企圖脫離私領域、不受限於婚姻家庭或家務工作的女人會遭受道德的指責,這就是性別不平等。
在傳統父權社會中,生殖工作使女人成為生育機器,女人是父權的生殖工具。而女人在婚姻家庭內所做的家務工作都是無償的勞動,是服務家庭中的男性的。但是女人因此也得到父權體制某種程度的保障,而當失去保障時,女人能以受害者角色哭訴,所以很多女人也覺得需要這樣的名分。
透過近代的婦女運動和進步的社會趨向,女性開始走出家庭、進入公領域,所以我們看到女性就業、受教育、參政、出入公共場所等等。而且女性可以不必進入婚姻、或留在婚姻中,她們可以離婚。當然,女性仍然不是完全走出私領域,所以有的職場女性兩頭燒,有些人學校畢業後就做起家庭主婦。
但是現代社會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趨勢,不但有利於女人進入公領域,也重新定義了傳統父權對「母職」的觀念。這就是家務工作的公共化,家務工作不再受限於婚姻家庭的框架、不再受限於私領域的範圍、不再受親密關係的管轄。
使家務工作公共化的最大力量來自家務勞動的商品化,女人過去替家庭中男人所作的服務和勞動,現在變成了職業和有酬勞的工作,這和女效能夠大量就業的趨勢相吻合,很多女人因而有了人生的新選擇─女人做同樣的家務勞動,但是現在可以不必替某個男人無償的服務,而是為自己獨立自主的工作。
故而,家務工作的商品化使女人從家奴的奴隸狀態中解放,而成為一個和一般男人一樣的受雇者、有酬勞動者、工人。這個婦女解放的趨勢是進步的,也重新定義了傳統父權對「母職」的觀念。
此外,家務工作的商品化也反過來證明瞭家庭中的無償勞動不是沒有價值的,而是值得重視的。故而,也是對私領域中的婦女有利。
任何工作的商品化都可能帶來剝削,但是不應該因此把人變回奴隸狀態,把女人趕回廚房,而是改變剝削經濟的模式,加強保障工作者的合法權益。例如當養育、生殖、烹飪、照顧、性、清潔等家務工作商品化後,如果有對女性剝削的狀況或男女工作不平等的狀況,我們不是去禁止這種工作進入公共領域,而是追求職場的性別平等,保障工作者的合法權益。更有甚者,當家務工作的商品化發達到一定程度,還可以進一步「社會主義化」,也就是社會合作的分工(例如有公營的照顧工作或性工作合作社等等)。
總之,代理孕母所從事的生殖工作,就是「女性的家務工作公共化、脫離私領域」這個大趨勢的一部份。代理孕母也因而改變「母職」的傳統父權定義、提供女性在職業和人生上的新選擇,也因此可以幫助女人脫離家庭婚姻的束縛(有婚姻家庭的女人可以選擇不生殖,沒婚姻家庭的女人卻也可以選擇生殖)。所以我們肯定生殖工作的商品化趨勢,這是個比生殖工作奴隸化(婚姻內的無償勞動)要更進步的趨勢。
代理孕母所從事的生殖工作,和父權定義的母職的生殖工作很不一樣:代理孕母不再是為婚姻關係中的丈夫服務,不必負擔家務工作,她是職業女性,她為自己的利益工作,她不是任何人的工具。如果說代理孕母間接的替某些男人完成了傳宗接代的願望,那麼她的角色也不過就像那些醫生、護士、男人的老闆、保育箱等一樣。
其次,代理孕母重新定義了母職,對所有女人都有利。這是因為代理孕母的母職只是生殖工作中的妊娠和生產而已,並不包括性交、養育等父權所定義的母職。在開放代理孕母的社會中,女人可以理直氣壯的說:「誰說做母親就一定要懷孕生產呢」?就好像因為廚師、清潔公司、托兒所、安養院、社會福利的存在,女人可以說:誰說做母親就一定要烹飪、做家事、養育幼兒、照顧老人呢?的確,代理孕母的母職觀念使女人擺脫了「性-懷孕生產-養育」的必然連結:喜愛養育子女、但不喜歡和男人性交和懷孕生產的女人,有福了,因為她們可有代理孕母。喜歡懷孕生產、但不喜歡養育子女的人也有福了,因為她們可以做代理孕母。
人為什麼會想做代理孕母呢?有人說,很多是為了錢,但是也有是為了同情、幫助親人好友;不過,在國外的調查裡面,也有人喜歡懷孕時被人重視的感覺、和只想嘗試懷孕生產的滋味。事實上,偽裝懷孕也是心理分析會研究的行為。在未來,當代理孕母變成一種正式的職業時,那麼就會和其他任何行業一樣,有千千萬萬種動機和理由進入這個行業,而不會有人覺得好奇了。所以「為什麼想做代理孕母?」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因為這個職業被特殊對待後的產物,是個無中生有的假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讓我們進一步想到:那些反對代理孕母的女性團體很少去替代理孕母的權益和需要來設想。或者,更陰險的是打著關心代孕者權益的名號,實質上卻百般刁難限制代孕實踐、企圖縮小代孕規模。而且這些女性團體常常把代理孕母或尋求代理孕母的人都當作被父權洗腦的受害者、傳宗接代思想的幫兇。這是對女性生殖工作者的輕忽和簡化。現代社會日形複雜,不能只是用「父權作祟」來涵蓋與解釋所有現象。很多單身女性、同性戀女性,以及各色各樣女人,都會對代理孕母有需求,而代理孕母所帶給女人的複雜利害和潛在機會,絕不能用「幫助父權傳宗接代」來一語塘塞。作為一個女性團體,應當尊重其他女性的生命選擇,應當假設代理孕母或尋求代理孕母的人都是生命戰場上的戰士與鬥士,女性團體要給她們更大的力量完成她們的選擇和心願,而不是拒絕與排斥她們,把她們當白癡。
總之,將代理孕母看成是替父權服務,或者把生殖工作商品化視為大惡,都是錯誤的女權分析。
作為新興行業,代理孕母是我們需要積極保障權益的工作。
今天無論有沒有禁止代理孕母的法律,代理孕母都會存在,只是處於地下化的狀態,這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我們必須正視代理孕母存在的現實,而思考如何積極保障代理孕母的工作條件和權益。
有人認為代理孕母會引發特殊的糾紛(例如在懷孕期不好好對待自己身體、會因為捨不得小孩而違約),但是我認為這種狀況是在一個行業比較不專業化、缺乏專業管理的情況下才容易出現的情況。還有人說代理孕母捨不得小孩是因為胎動會牽動母愛等等,我想女性主義者對這種母愛的生物性解釋一定會嗤之以鼻的吧。專業的代理孕母面對嬰兒不會那麼容易動情,就像在急診室或ICU的醫護者可以不動情一樣,不見得是沒人性,而是有專業的素養。
所以,代理孕母在未來走向專業化將是個進步的方向,這可以使懷孕過程更有嚴格程式,這些程式既保障代理孕母的權益也保障胎兒的健康,也可使代理孕母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職業。沒有污名的代孕者也較容易像國外的「白鸛」代孕者組織一樣,來爭取自己的工作權益。
有人說,那麼代理孕母不就成了生育機器嗎?確實。但是在避孕和人口控制的今天,一般女人已經不再是生了一個又一個的生育機器,代理孕母的生育機器形象未必是個負面的、污名的,而是可以帶著先民對生殖的崇拜心理,可以是代理孕母專業形象的一部份。如果女性主義者真的要幫助弱勢女人壯大,那麼是貶低她們好呢?還是提升她們的形象好呢?其次,「生育機器」之說是用來形容過去在婚姻家庭關係中的女人,就好像說家庭主婦是個「烹飪機器」一樣,但是當女人成為餐館廚師時,說她是「烹飪機器」又有什麼意義?專業工作者又有誰不是個效率機器呢?在生殖工作和許許多多的家務工作商品化、公共化的趨勢下,也有一些女性是反對這種趨勢的,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女性在家庭婚姻私領域中採取一種犧牲自我的策略,以便得到較多保障;簡單的說,這些女性將母職與家務工作變成無價的、不可交換的、絕非商品的「愛的結果」,易言之,一切都是為了愛,只有在愛的親密關係中,女人才向特定男性提供家務工作,否則多少錢都換不到此女人的任何家務服務,家務工作只能以愛來交換。把母職的家務工作當作無價,甚至提高到神聖地位,結果往往是犧牲自我也在所不惜。但是,這種犧牲自我或愛男人策略不應該是異性戀女性的必然歸宿,而且左右週遭都是這種策略失敗的例子。既然如此,何不放其他女人一馬,讓另外一些女人試試別的策略,也是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呢?
女人的不平等待遇從來就被歸諸於女人的生物性,認為女人的天職就是懷孕生產,因而要性交以便懷孕,既然生產了就要養育小孩,為了養育小孩就非要和子女的爸爸結婚,並且要服事丈夫,以換取飯票。但是,代理孕母打破了這些生物必然性的神話:雖然懷孕生產是隻有女性才具備的能力,但是個別的女人卻在生殖科技的幫助下離開了生物的宿命;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樣,不必懷孕生產,就可以有小孩可以養;女人也可以無須性交、無須養育子女,卻能夠懷孕生產,並且可以用懷孕生產為獲取生計的手段,故而懷孕生產有可能是擺脫男人、獨立自主的手段,這是千古所未見的─從來,女人的懷孕生產都是使女人依附男人、喪失獨立的行為,今天代理孕母打破這個宿命;所以女性主義當然支援代理孕母,並且希望早日看到代理孕母的專業化。
(1999年3月11日立法院「人工生殖法草案」立法公聽會發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