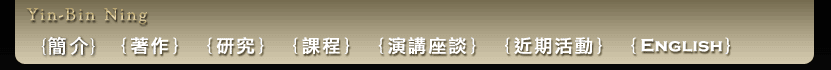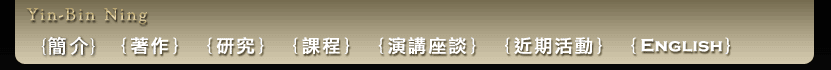性,無須道德:從性倫理到性批判
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附錄─貝里歐堤談「性無須道德」
一般美國大學供全校大一新生選修的通識課程中,通常有哲學系提供的「倫理學」,所用的教科書也冠以「倫理學」之類的書名,但是考究其課程與教科書內容,雖然偶而會穿插一些對於規範倫理學理論(如義務論、效益論)的介紹,但是大多數是屬於「應用倫理學」的範疇。應用倫理學之所以會成為哲學通識教學的主流,乃是因為其內容被認為貼切學生的現實生活,不會因為艱深的理論而嚇跑學生,畢竟,如果選課的人多,對於哲學系的經費或發展也會有正面的影響。
上述這個教學現象可以說是應用倫理學在美國的哲學機構內立足的現實原因之一,有了這種制度性的支援,才使得應用倫理學在傳統上重視理論思辨的哲學學門內至少有個邊緣的地位。
Richard Garner(1994)最近提到,1970年代初開始的應用倫理學熱潮,一方面是因應1960年代後期外界要求哲學面對社會現實,另方面也是因為大學紛紛開設這類課程,公眾注目這些話題,無數的選集教科書遂應運而生,這方面的出版於是大發利市(364)。
這些「倫理學」教科書大致上可以分為和專業相關的應用倫理學議題,以及另外一些不屬於專業倫理學的議題。專業相關的應用倫理學議題包括商業倫理、醫療倫理、生命倫理(墮胎、安樂死、死刑、基因工程等等),後者則包括了性倫理,以及一些政治性的議題(種族歧視、核戰、經濟平等、保障名額等)。這些分類都有其任意性,例如墮胎有時被歸類在生命倫理之下,有時則在性倫理之下;健保政策則有時在醫療倫理之內,或有時在探討人權與社會公平之內。
總之,至少在美國,性倫理在哲學機構內的制度性定位,離不開應用倫理學。事實上,性倫理在學院機構內的發展也和應用倫理學一樣,源自一個特定的時代社會背景。正如Richard
Fox and Joseph DeMarco(1986)所觀察的: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哲學家開始討論當代實際的道德問題,因而開啟了應用倫理學這個新的領域;1970年代中至1980年代中,應用倫理學是北美哲學界中成長最大的領域,Fox
與DeMarco二人並將「應用倫理學」稱為「倫理學的新方向」(2-3)。Peter Singer在他編的Applied Ethics(1986)的"Introduction"中提到:「先是美國的民權運動,然後是越戰及學生運動的興起,開始吸引哲學家去討論道德議題:平等、正義、戰爭及公民抵抗權。以『關心天下事的公民』身份加入辯論的哲學家逐漸覺悟到他們討論的其實是屬於哲學傳統中的倫理學問題」(3)。易言之,Peter Singer認為1960年代的動盪產生了應用倫理學。1960年代的動盪透過學生運動衝擊了學院制度;學院和「軍事-工業綜合體」的關係、學生權力(包括對課程及人事決策的參與)、學術知識和現實社會政治的關聯等問題,均被一一提了出來。Fox
and DeMarco提到,當時的學生示威者要求高等教育應該和現實相關,應該開設有關和平、環保、社會正義方面的課程,而醫藥倫理及企業倫理則在大學之外受到廣泛注意,等等(12)。同時,1960年代的動盪也在學術方面衝擊了人文社會科學,原本當道的行為科學取向和實證主義,受到了廣受激進學生支援、可以泛稱為「批判理論」的挑戰。而當時被視為社會科學中行為主義與實證主義之來源的分析哲學亦招致抨擊;分析哲學的後設倫理學,以及十分理論傾向的規範倫理學,都被認為是脫離現實、無用。在學院制度受到衝擊、原有建制必須考慮學生權力及社會氣氛的壓力的狀況下,分析哲學才開始發展觸及實際問題的應用倫理學。這個應用倫理學興起的同時,也是美國社會對情慾問題發生許多爭議的時刻。一個爭議焦點是當時由「性革命」風潮帶來的傳統性道德與性觀唸的改變,和這個相關的則是當時女性主義對身體情慾議題的關注(當時的女性主義者如Germanie
Greer等均偏向女性情慾解放,所以也對社會有一定的衝擊)。另一個爭議焦點則是同性戀問題,這是新左派運動所帶動的社會運動風氣以及認同政治開展的結果。這些爭議都反映在性倫理學內。事實上,應用倫理學議題的出現與轉變,和社會現實的變化是密切相關的:例如,冷戰結束後,核武的倫理問題逐漸消逝,但是基因與人工生殖科技的研究則帶來新的議題。性倫理議題的發展變化也有類似的歷史軌跡。
前面提到的「性革命」,根據Steven Seidman的講法,是「修辭」成份居多,實際的「革命」恐怕未必;但是他也接著指出,在1960到1980這段期間確實有三個顯著的發展,一個是女性情慾的出色,一個是同性戀認同與次文化的興起,還有一個則是公共領域的性化,也就是公共空間開始有性的言談論述和影像呈現(122-23),性不再只是私領域的,而可以變成公共討論(包括學術研究)的對象,性影像與色情書刊電影更大量充斥公共領域。
造成「性(革命)」這些發展的原因很多,有商品的力量,有避孕措施的普及化,有之前(二十世紀開始)自由派性意識在美國的成長,有社運的抗爭等等。對於這些「性」發展的前因後果與歷史已有許多研究,而且不同女性主義者對此種發展也有兩極的評價1
。
不論如何,在「性革命」風潮的1970年代初,當時的人很清楚的自我意識到「一場性革命正在發生」,傾向自由派的人文主義者將當時的風潮稱為「新性革命」2,相應而言,在文化界或準學術的領域中也有許多學者及作家對性開放之對立採應用倫理學式的辯論3
;在社會科學領域有許多針對當時出現的「新態度」(亦即對婚前性行為,外遇、裸體、一夜情、同性戀、女性情慾、豪放女、離婚、性交易等等出現的新評價)提出分析和準倫理學的討論4。在這種社會與學術氣氛下,哲學家自然也加入了對性的應用倫理學研究5
。
197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性倫理學選集是 Baker & Elliston 編的
Philosophy & Sex(1975),這本選集奠定了分析哲學之應用倫理學的「性倫理學」論述傳統和書目。這本選集及其相關文章除了常被引用外,之後的許多選集(特別是提供通識課程的倫理學教科書)也大多和這本選集的文章重疊。1980
年代初Alan Soble編的Philosophy of Sex(1980),以及另外一些性倫理學專書都進一步鞏固了這個論述傳統。
這些被視為「性倫理」的內容則視出版年代所關心的社會議題與時代氛圍而有些微的變化。例如Philosophy
& Sex在第一版時,Elliston所寫的「替放縱(濫交)辯護」(表達了性革命時代的某種氣氛)並未收入雷根年代出版的此書第二版(Baker
et. al., 1984),然而在愛滋風暴吹過西方之後它又重新出土於第三版(Bakeret. al., 1998)6。自由主義者
Fred Berger分別在1977與1984寫過兩篇反對查禁色情書刊影像的文章7,雖然都是反檢查,但卻反映了不同時期與不同性質的的敵人和論証,前者是批評1960及1970年代保守派對色情材料的攻擊,後者則是批評1970及1980年代女性主義者(夥同新右派)對色情材料的攻擊。
除了「色情材料」這個議題之外,性倫理學中一直出現的「墮胎」議題也反映了美國社會在墮胎爭議方面的變化。事實上,早年奠定應用倫理學寫作及論述形式的經典文章之一,就是由Judith
Jarvis Thomson所寫的"A Defense of Abortion",隨後出現的一連串的討論更使得墮胎形成了應用倫理學早年的重要議題。但是墮胎辯論的焦點在早期性革命時代時是女人的身體自主(隱含著「性氾濫」焦慮),並曾經和「家庭價值」成為美國政治的焦點,在後期則逐漸轉換到和生命價值、生命倫理學連結的議題。近年來,那些反對新生殖科技與代理孕母的女性主義者突然發現她們也必須邏輯一貫地反對墮胎(因為墮胎與避孕都算是廣義的現代生殖技術的一部份,也和代孕等一樣都改變了女人的母職意義,否定了女性與胎兒或懷孕的必然生物連結)。這個立場上的變化也反映在Soble的The
Philosophy of Sex(1997)第三版文章中。
雖然性倫理的討論和社會爭議與變化十分相關,以致於某些談法與論文逐漸「不合時宜」,但是哲學家對這個領域應包括什麼樣的問題似乎已經有了初步的共識──性倫理通常包括了「墮胎」、「色情材料」、「性變態」、「同性戀」、「婚姻(通姦、一夫一妻等)」、「賣淫」、「濫交」、「有性無愛」、「戀童」、「性騷擾與強暴」、「對性愛的女性主義批判」等議題。透過教科書,性倫理學這個領域多少已經被正典化了。
在這個論述傳統中,有關「性變態」的討論似乎占據了一個核心的地位。Soble 在 Philosophy
of Sex第二版與第三版序言中,甚至逕稱該選集中數篇關於「性變態」的文章是整個性哲學的最根本讀物。
「性變態」的討論為何對性哲學有此重要地位呢?當然,「性變態」的討論對於1960、1970年代出現的各種新的性實踐(如同性戀、有性無愛、以及其他「性偏差」)可以間接或直接地做出道德評估,故而其明顯的現實蘊涵是這個話題受到重視的原因之一。另外,就機構(institutional)的因素來說,參與這系列「性變態」的辯論者後來都是名重一時的、有地位的哲學家(如
Tomas Nagel, Robert Soloman, Alan Goldman, Janice Moultion等多人),這對於把「性」當作專業哲學的正當研究對像有所幫助,也直接強化了「性變態」這系列討論在性哲學中的正典地位。就「性變態」與「性哲學」內在的理論關係而言,這裡的重要原因則是:由於性哲學探討性的本質,故可以作為性倫理的堅實基礎,而對於「性變態」的分析可以界定「性」的本質、常態(normacy)、界限為何。這種從「病理」、「變態」、「偏差」、「邊緣」的研究入手,以探究研究對象的本質規範,是性學界常常採取的進路(這也是十九世紀以來生物學界常用的方法學,像弗洛依德在《性學三論》一書中即從「性變態」入手,並說明瞭這樣的方法學)。此處,性哲學家也採取了同樣的預設。總之,具有分析哲學傾向的應用倫理學,在「性」方面大抵發展出兩個密切相關的部份,一個是討論和現實「性(情慾)」爭議息息相關的性道德部份,另一個則是以「性變態」為中心的性哲學部份。一般說來,性倫理的論証與假設比較接近一般常識的辯論,所以有較大的「應用性」;但是就像整個應用倫理學一樣,仍然可能會引發專業的焦慮(亦即,似乎無須哲學專業亦可加入性倫理的討論)。
但是傳統分析取向的性倫理學也有其限制,這個限制就是:其論証方式經常訴諸「範例」(paradigm
case)與語言分析。然而範例往往會被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所滲透(這在傳統哲學講法中就是「訴諸常識/共識的危險」),因此用「範例」來做論證的前提時往往容易先預設了將要證明的結論。在另一方面,語言分析的取向則受限於靜態的語意現狀,忽略了刻意創新的語言和語意(甚至刻意的歧義模糊與含混誤用)也可以是推動社會變遷的一種力量,同時,社會變遷的力量也會積極的改變語意現狀。以那些環繞著Nagel的經典論文"Sexual
Perversion"的討論為例,這些討論固然開明地將同性戀劃分在性變態之外(就時代氛圍而論,這是Nagel論文發表時的一個重要蘊涵,因為Nagel一文初次發表於1969年,當時同性戀仍被視為性變態),但是討論中的許多作者仍然把某些性行為或性偏好視為性變態的範例。在這種性論述中認定的「常態/變態」的區分,不僅是像傅柯所見為性學知識與權力所建構的區分,而且也會隨著時代常識的變遷、社運的抗爭等而變化,性變態的「範例」因而會演變成爭議未決的問題,而非範例。這裡給我們的教訓是:性研究應當更具反身性(reflexivity),不論一個對象或觀念如何清楚確定,不論一種價值如何沒有爭議的被共識接受,我們仍然必須考察它們出現與存在下去的過程和條件。
除了以上所談的侷限之外,過去分析哲學傳統的性倫理研究很少去連結更大的社會脈絡或理論脈絡,這和人文社會領域的另一些性學術研究恰恰成為對比。在1960、1970年代的動盪時期,人文社會科學的批判理論也發展出另一些激進的「性」理論:弗洛依德及馬克斯主義者賴希(W.
Reich)的性解放理論對西歐學生運動頗有影響,在英美也影響了女性主義並激發了馬庫色(H.Marcuse)的回應。賴希與馬庫色的理論則構成了左派的性激進傳統。我想把這些不同理論趨勢的性研究通稱為「性批判」。
與分析哲學的性倫理取向相對比,賴希與馬庫色的性批判最大特色有四:第一,他們將「性」從個人心理結構連結到社會結構,把性問題視作政治問題,開啟了「性政治」(Sex-Pol)的架構。第二,他們(特別是賴希)反對禁慾的性道德,並將這種性道德看作威權社會的控制手段,所以替性自由的實踐提供了一種政治性的辯護。第三,馬庫色雖然對於性慾望的釋放採取批判態度,認為這種異性戀的性自由變成當代社會的控制手段,但是馬庫色承襲了弗洛依德學說提出「多元變態」的觀念,平反傳統上被認為「不道德」的性變態。第四,他們自覺地發展出不同於自由主義的性政治路線。
最後一點其實是所有左派的共同特色。例如馬克思、恩格斯的「正統」性政治路線,批評了資本主義下因為經濟的剝削而造成的「性剝削」。在他們看來,自由主義者所謂的「兩相情願」(consent彼此同意)的契約,不論是勞資雙方的勞動契約,或者男女間的婚姻契約,都因為雙方的經濟條件懸殊,而其實是掩蓋了剝削的實質。
在批判理論中,對於「性」議題介入甚深的另一思想傳統則是女性主義。許多左派女性主義原來便較傾向「性自由」路線,在第二波婦運的早期,左派女性主義參與較深時,此時的激進婦運對女性情慾解放持比較肯定的態度,但是隨著「激進-文化女性主義」(radical-cultural
feminism)的興起,以及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對異性戀情慾的完全否定,女性「性自由」便遭到了徹底的批判。
批判性自由與性解放的「激進-文化女性主義者」,和賴希、馬庫色等一樣也是從政治性觀點來看待「性」,但是將解釋架構從「階級」轉移到「性別」。她們認為性在一個異性戀父權社會中,基本上是完全被性別權力所滲透的,「性」就是異性戀的、男性性慾(陽具插入式性交的情慾),所以不論是從性壓抑或性解放來談性,只要是在這個異性戀架構之內,性都是男性權力的色情化。出於這樣的觀點,激進-文化女性主義將矛頭指向色情材料,認為色情材料是男性支配女性的重要武器。這個觀點受到另一批「性激進派」女性主義者的批評,而引起女性主義陣營內的「性辯論」(Sex
Debates)或「性大戰」(Sex wars)。(「激進-文化女性主義」則把「性激進派女性主義」一律戴上「性自由放任主義」的帽子,這其實是一種污名化對方的論述策略,但是未查詳情者卻往往被誤導,而將性辯論的雙方描述為「激進女性主義vs.性自由放任主義」)。
如果從純粹的「性別」(父權結構)角度來看這場「性辯論」,激進-文化女性主義似乎有一些說服力;然而,「性」的政治所涉及的,不只是「性別」而已。很快的,性激進派女性主義者就提出了「性」或「情慾」的獨立自主性,認為「性」政治不可以完全被化約為「性別」政治。此外,激進-文化女性主義的「父權結構決定論」採納的是類似教條馬克思主義「階級結構決定論」的論述,在後現代思惟的流行下缺乏說服力。事實上,新一代的同性戀理論與後女性主義不但是對於激進-文化女性主義的一些基本假設的反動,也受到傅柯的影響而開啟了1990年代的酷兒理論與政治。
在過去十年左右,有關性的學術討論在社會人文學界十分蓬勃,但是原有主流學科像社會學、哲學卻不是這些性討論發生的主要制度性場域(例如重要的社會學家對性問題的思考架構仍然停留在女性主義的挑戰與兩性的格局上,並且在這個格局上看待同性戀),大部分的性學術討論出現在一些歸屬不清楚的跨學科領域內,多半被冠上同志或酷兒研究、性研究、文化研究等等名稱,並且援引了許多社會理論與批評理論的新思潮。這些性的跨學科研究比較具有反身性質,並且如同過去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一樣批判既有的學科理論或後設假定,並且往往從特定的價值與政治立場出發,以發展出一個貫穿社會理論、語言、文化、歷史等研究的視野,其高度的理論性質恰和應用性質的性倫理學形成對比。
性倫理學固然是十分有價值的研究,但是如果性倫理能進一步結合上述那些跨領域的性論述,替代目前以性變態為中心的性哲學思辨,將可使目前「腹地狹小」、地處(哲學學科中)邊緣的性倫理研究具有更反身性質的理論資源,同時也可以發展出一個比較整體性的研究取向,從性問題延伸至整個文化與社會理論、哲學理論問題等等。我則把社會批判理論與性的結合稱為「性批判」。
分析哲學傳統的性倫理學中始終都有一些應用倫理學家選擇運用非分析哲學的理論,或者積極回應其他人文或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研究,並與之對話。例如,沙特的理論就對性哲學或性倫理學頗有影響(例如沙特對Nagel等人的影響),至於像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等批判理論對於性倫理這個研究領域的影響,也常見於性倫理的著作中,女性主義觀點的重要性也常被男性哲學家在口頭上或書目中承認或認可(雖然未必收入選集中),女性主義者本身也會自行編選教科書來影響正典的形成8。近年來也出現像Laurie
Shrage(1994)這樣的女性主義應用倫理學者,其寫作完全浸淫在女性主義的性論述與辯論之中。這些都是性倫理與跨領域的批判理論結合的例子,也就是從性倫理擴及到性批判的例子。
在這方面,貝里歐堤(Raymond Belliotti)的 Good Sex(1993)一書也是另一個典型例子。和以往的性倫理學傳統相較,它有以下的三個特點或貢獻。
第一,性倫理學傳統中被當作經典的那些以Thomas Nagel為首一系列論「性變態」或「性本質」的文章,在這本書中幾乎不被提及。另方面,此書雖然不再抽像的探討「性變態」或「性的本質是什麼」,但仍然處理了部份的性變態問題,而且是以貼近現實的方式,具體地對一些「變態」作出倫理學的評估。
第二,貝里歐堤倒也未完全脫離性倫理學的論述傳統,他像以往的著作一樣整理了西方性倫理論述的傳統看法,也探究了性倫理早年的一個重要話題──「性與愛」之間的關係;雖然這個「無愛有性是否不道德」的通俗爭議存在著一些可疑的假設(例如,什麼是「愛」),但是畢竟還有其在通俗論述領域中的重要性及應用性。更有甚者,貝里歐堤之所以延續這類傳統的討論,目的是為了把傳統論述所隱含的自由主義立場明白地顯露出來,他因此也清楚地架構出一個性自由派的倫理學立場。
第三,貝里歐堤在此書中以自由主義(性自由派)的立場,對批判理論的兩個流派(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的立場做出正式認真嚴肅對待的回應。過去分析哲學雖未忽略批判理論,但是此書卻是首次十分有系統的處理批判理論。貝里歐堤所提出的性倫理學架構,可以說是建立在契約論基礎上之自由放任主義的修正,也就是基本上認可建立在自願、未受蒙騙等狀況下彼此同意(consent)的性契約,並進而考慮所謂「彼此同意」的脈絡──如社會平等、是否「將他人只視為工具而非目的」,亦即,考量是否對人尊重,對互惠原則的肯定,對自尊的重視,對剝削的棄絕等等精神(87),由此作為評估性行為道德與否的標準。
貝里歐堤對性自由派立場的檢討以及對批判理論的回應,使我們清楚地看到性倫理學所涉及的,正是社會哲學的一個重要面向,亦即「自由主義vs.激進/批判思潮」的政治辯論(例如對於性契約、婚姻契約和sexual
consent的批判分析,自然也會蘊涵著對於勞動契約、買賣契約和consent的批判分析)。就這一點而論,貝里歐堤的貢獻是把「性」問題明白地放在一個「政治」的架構中。
就整體而論,分析傳統的性倫理學其實暗含了一個自由主義的立場,也就是「性自由派」這個立場。在面對批判理論或激進理論的挑戰後,究竟它將如何回應,如何吸納激進/批判的一些說法,如何修正原本的預設、框架或結論,都值得我們仔細觀察。
性倫理與那些跨領域的、批判性質的性批判論述結合,當然會是個有許多衝突的「婚姻」,首當其衝的或許就是性倫理本身存在的正當性。應用倫理學者很早就提出性倫理(或其他專門倫理)是否有其獨特指涉的行為領域,亦即,評估性行為道德與否的標準是否不同於評估其他非「性」的行為?或者更基本地質問:性是否具有道德上特殊的意義(Primoratz)?就某些性批判的論述來看,為什麼今天只有性倫理,而無性別倫理、階級倫理、種族倫理等等,本身就是個有待批判分析的問題。性與性別、階級、種族同為一種權力關係與社會範疇,也都曾在歷史的發展中出現過倫理問題,性別、階級、種族本身也曾被視為和道德相關,但是現代化中平等的意識形態已經將這些社會範疇去道德化,唯獨「性」這個最受壓迫、有待平等的社會關係仍然緊密地和道德相關。在這個意義下,性倫理本身便是一種意識形態。
當然,「性倫理」一詞其實有三種不同的含意,第一是指性道德,也就是專屬於性的普遍道德規範,例如有人認為同性戀或通姦不道德。第二是指性的合宜行為準則,像一夜情倫理(例如事後不應糾纏不清、要有安全措施等),這種意義的性倫理(ethic,字尾沒有s)不必有道德意義(即違反這種性倫理準則不是不道德,而是不明智或不合宜),也不是普遍的(即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可能只適用於某時某地的某群人。第三是指一種學術研究的領域,內容可包括前述兩種行為規範或準則,還可以更廣泛地包括(如本文所建議的)對性文化、性現象、性規範的社會批判,也就是「性批判」。一種性批判的形式甚至可以是置疑這個學術領域本身的存在價值,例如性倫理是否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意識形態或知識/權力的產物。
總之,我們可以質疑「性道德」的必要性。因為道德就是道德,不論是吃飯還是打球或者性交,所有行為都在道德的尺量之下,並沒有吃飯道德、打球道德,所以也不應該有性道德。例如甲乙丙三人要共同進行某個活動(可能是吃飯、打球或者性交),假設三人(明示或暗示的)互相允諾與期待這個活動是以相互的或者互惠的方式進行,而當活動不是相互或互惠時,亦即,出現違背允諾的欺騙剝削情形,那麼就可能是不道德的─重點是:此活動道德與否,跟違背允諾有關,而跟這個活動是否為性活動或者其他活動無關。性,無須道德,亦即,無須專屬於性的、只適用於性的道德。
可喜的是,近年的性倫理研究確實更明顯地看到結合那些跨領域性批判論述的發展趨向。在最新一版的正典化性倫理教科書上(Baker,
et. al., 1998),我們看到許多批判理論學者(女性主義者、同志與酷兒理論家)的文章被收入,像Luce Irigaray,
Helene Cixous, Edward Stein, Michel Foucault, David M. Halperin,
Ian Hacking, Linda Singer, Linda Martin Alcoff等,而且傅柯的影響顯而可見;性與性別之間的重疊與張力(酷兒理論與女性主義的對話)也持續存在。
展望性倫理及其外(sexual ethics and beyond),不但性倫理要結合性批判,而且我們今後勢必要從跨性別與酷兒理論的角度來批判地檢視前一時期女性主義與兩性研究(gender
studies)留給我們的理論遺產。
原載於《哲學雜誌》季刊33期,2000年8月,頁62-75。原標題為〈性倫理及其外〉
註腳:
1. 女性主義者對性革命的評估多是呈現兩極反應。例如 Sheila Jeffreys, Anticlimax: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Sexual Revolution (NY: New York UP, 1990)即是反對性革命的重要著作。下面這本則是對性革命持肯定態度的女性主義名著:Barbara
Ehrenreich, Elizabeth Hess and Gloria Jacobs, Re-Making Love:
The Feminization of Sex (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86).
2. Lester A. Kirkendall and Robert N. Whitehurst, eds., The New
Sexual Revolution, Preface by Paul Kurtz (New York: Donald W.
Brown Inc., 1971).
3. Ronald Atkinson, et. al., Sexual Latitude: For and Against
(New York: Hart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4. 這些書對性議題的分類方式十分類似性倫理的分類,可見它們在論述上的共通性。例如Herbert A.Otto, ed.,
The New Sexuality (Polo Alto, California: Science And Behavior
Books, Inc., 1971,以及Robert R. Bell and Michael Gordon, eds.,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Human Sexualit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2).
5. Ronald Atkinson似乎是最早將當時流行的「性」問題以專業方式處理的分析哲學家。(這本書又在一九九○年代出土重印,顯示近來性問題的持續爭議性)。Ronald
F. Atkinson, Sexual Morality (Hampshire: Greff Revivals, 1965,
1993).
6. 此文在1995年也同時收入Robert Stewart編的一本性倫理選集。
7. 1977年的文章後來收入Soble(1980)的選集:Fred Berger, "Pornography,
Sex and Censorship", Alan Soble (ed.), The Philosophy of
Sex: Contemporary Readings, first edition (Savage,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80) 322-347。另一篇的出處:Fred
Berger, "Pornography, Feminism,and Censorship", Robert
Baker and Frederick Elliston (eds.), Philosophy and Sex, second
edition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4) 327-352。
8. 例如Sharon Bishop and Marjorie Weinzweig, Philosophy and Woman
(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9.)
正文書目
何春蕤,〈性道德及其不滿:賴希的《性革命》〉,收錄於何春蕤編《呼喚臺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元尊文化,1997年。頁373-383。
Baker, Robert and Frederick Elliston, eds. Philosophy and Sex.
Second Edition.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4.
Baker, Robert and Frederick Elliston, Kathleen J. Wininger, eds.
Philosophy and Sex. Third Edition.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8.
Belliotti, Raymond. Good Sex: Perspectives in Sexual Ethics.
Lawrence, Kansas: Unversity of Kansas, 1993.
Fox, Richard M. and J. P. Demarco. "The Challenge of Applied
Ethics." New Directions in Ethics: The Challenge of Applied
Ethics. Edited by J. P. Demarco and R. M. Fox. New York: RKP,
1986.
Garner, Richard. Beyond Morality. Philadelphia: Tempel University,
1994.
Thompson, Judith Jarvis. "A Defense of Abortion."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1(1971): 47-66. Reprinted in Baker et. al.
Nagel, Thomas. "Sexual Perversion." The Philosophy
of Sex. Third edition. Edited by Soble. 9-20.
Primoratz, Igor. Ethics and Sex. London: Routledge, 1999.
Seidman, Steven. Romantic Longings: Love in America, 1830-1980.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Shrage, Laurie. Moral Dilemmas of Feminism: Prostitution, Adultery
and Abor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Singer, Peter. "Introduction." Applied Ethics. Ed.
by Peter Sing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isty Press, 1986.
Soble, Alan, ed. The Philosophy of Sex: Contemporary Readings.
Third Edition. Savage,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80, 1991, 1997.
Soble, Alan. The Philosophy of Sex and Love : An Introduction.
St. Paul, Minnesota: Paragon house, 1998.
Stewart, Robert M.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Sex and Love.
Oxford: Oxford UP, 1995.
Trevas, Robert, et.al. eds. Philosophy of Sex and Love: A Reade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6
附錄─貝里歐堤談「性無須道德」
雖然「性,無須道德」這個想法在性倫理學圈子中流通頗久,但是很少性倫理學家曾正式地討論「性無須道德」,前面提及的Primoratz也只是建議這個立場而無論証。相較之下,貝里歐堤(Raymond
Belliotti)在 Good Sex 一書,還多講了幾句。以下我將從他的討論脈絡來探討「性無須道德」。
首先,Good Sex此書的第一部份的前半是對西方傳統的「自然法」進路的批評。事實上,性自由派的性倫理學的大部分著作基本上都對這個代表傳統保守性觀唸的自然法進路提出批評。在這部份貝里歐堤基本上沒有新鮮的提法,只是承襲了過去性倫理學家的論證而已。例如,傳統的保守派認為「性」有一種「自然的」功能,像「生殖」、「人性實現」或「完滿的愛」等等;但是貝里歐堤指出,「自然」並不等於「道德(對錯)」,故不合乎自然,或甚至「變態」也不必然等於「不道德」。如果「自然」和「道德」之間能劃上等號的話,則必須進一步假定這個「自然」代表某種「理想」,也就是要假定某些關於人的本性或本質的形上學或甚至神祕主義教條,而這些教條均很難被證明。更有甚者,如果說「性」一定是為了愛,這也不能證明「無愛之性」會妨礙「性」的這種功能,
更何況,「無愛的性」也可能會達成其他道德上與實利上的有用功能(25-85)。貝里歐堤以上的這些說法都沒超過先前自由派的性倫理學者9;特別是那些企圖證明同性戀沒有什麼不道德的倫理學家,最常反駁這類「自然法」進路10。
貝里歐堤在第一部份的結尾,開始提出他的性倫理學架構。這個架構的雛形可以說是建立在契約論的基礎上之自由放任主義。其基本精神就是:「性」是否道德乃在於涉及「性」的各方是否在自願、未受蒙騙的狀況下彼此同意。但是這種自由放任主義傾向於對實際的性契約採認可的態度,而沒有考慮當事人是否在平等的狀態下自願同意,還是在不平等狀態下沒有其他可行選擇才「自願」同意的。「平等」的問題顯然涉及了當事人的「自主性」。換句話說,契約雙方可能是自願的,但不一定是在自主狀況下同意契約的;自由放任主義忽略了「自主性」層面,因此似乎有所不足;因為僅僅是「自願同意」尚不足以確立契約之道德性,貝里歐堤在此提出了康德思想來修正自由放任主義。
康德思想對契約主義的性倫理架構之修正簡單來說就是:自由放任派所認可的實際契約還要有其他道德原則的補充,像「不可將他人只視為工具而非目的」。在這個抽像原則的背後,是對人的尊重,對互惠原則的肯定,對自尊的重視,對剝削的棄絕等等精神(Belliotti
87)。
另外,貝里歐堤也提出:性行為是否合乎道德也須視其是否涉及欺騙、毀謗、脅迫、剝削等(104)。
有人或許會問,像貝里歐堤對性行為所提出的道德評估原則,難道不也一樣適用於性行為以外的其他行為嗎?的確。我們根本看不出來貝里歐堤對性行為所提出的道德評估原則,和人們對一般行為所提出的道德評估原則有什麼不同。而這正是貝里歐堤的主張:對性行為的道德評估,就像對任何其他人類行為的道德評估一樣,應採用相同的規矩和原則(103)。貝里歐堤會說:倘若對於任何一件行為,我們一般都是以其是否涉及欺騙、毀諾、脅迫、剝削,是否自願甚至自主地進入契約關係,是否將他人是視為工
具而非目的等原則來評估此一行為合乎道德與否,那麼為什麼在面對性行為時,我們要用另外特殊的原則或標準來評估呢?貝里歐堤這個主張(亦即,在對性行為作道德評估時所採用的道德原則,應和評估任何其他人類行為時一樣─因此,我們無須特別專屬於性的道德),是不是蘊涵著「性行為和其他行為沒有本質上的不同」或「性行為所涉及的契約行為和其他契約行為並無本質上的不同」?
換句話說,貝里歐堤在主張「適用於一般人類行為的道德評估原則也同樣地適用於性行為」時,是否必然預設了「性行為(契約)並非一種特殊的人類行為(契約),而和其他人類行為(契約)沒有什麼本質不同」?
這個問題既需要進一步澄清其語意,也需要從幾個方面來討論。有些讀者可能不明白為什麼我要討論這個問題,先讓我講一下這個問題的背景,然後再開始討論。
一般來說,性保守派要求性行為不能只用一般的道德原則來評估,可能還需要更嚴苛或特殊的道德原則來評估。例如,傾向於性保守派的人會覺得兩個人如果兩情相悅,固然可以在彼此同意且自願的狀況下,從事一般行為像共同進食、打球等等,但是卻不能從事性行為─除非兩人已經結婚。其所持之理由則不外乎視性行為為一極特殊之行為,和人性、人的本質或人格的極深處相關,性是人內心靈魂的交流,性行為對人格或人生都有極端與長久之影響;例如,保守派的性哲學家Roger
Scruton就斷言「人不能輕易地把他們的性行為當作一些孤立的行為??人很少能『放開』一次,而事後船過水無痕。一次涉及高度性興奮的特
殊『性經歷』,可能會終生迴響,和不斷蓄積著生命中每次渴望的點點滴滴」11。「性」既然攸關人格深處或甚至影響一生,因此兩人若無終生的承諾(並以法定婚姻形式來確定承諾),就率爾性交,將是視人格為無物,視雙方為洩慾工具,傷害自己與別人。至於那些以一夜情為家常便飯或以賣淫為業者,在這些保守派眼中恐怕就是「異化」,「不合人性」等等。事實上,性保守派最常見的主張就是:有性無愛是不道德的,違反自然的性是不道德的。
在上述性保守派的道德論述中,固然有許多十分模糊籠統的措詞,但其重要精神則是「性和其他人類行為相當地不同」,而這和自由派是對立的。由此而常被延申的保守派主張則有:一、性教育是一種「特別」的教育,不適用於一般教育的理念(例如教育一般而言應是民主、多元、開放、實用、人本、重實驗精神、知行合一等等,但是性教育則可以違背上述的教育理念,而變成權威、一元、封閉、不實用、非人本、不重實驗、不可知行合一等等)。二、性不能像其他行為在人生每個層面、在社會每個面向都被呈現。例如,性不可以在公共空間與公共論壇(或甚至學術與藝術中)出現。三、適用於性行為的道德原則不一定適用於一般行為。最後一點就是我們討論的焦點。
另方面,即使在日常有關「性」的通俗論述中,我們也常聽到傾向於性自由派的人強調「性和其他行為沒什麼不同」,例如主張「父母可以從小教育子女學習性的愉悅」的人便斷言:「學習處理性與學習處理其他事情有什麼差別???其實,性只是人生活動的一種,就像打球、游泳、吃飯一樣??」12。對於性自由派而言,在性自由的社會組織與文化中,性行為在目前所具有的特殊社會文化意義將會改變或不存在。例如,在性自由的社會文化中,強姦可能不會再是一種像現在被受害人視為羞恥的罪行,而只是視為「妨害自由的暴力行為」。或者例如,情侶之間的性行為在性自由的社會中,可以和其他的社會行為(共同進食、
打球)等一樣,並不具有特別不同的社會文化意義。故而目前性的社會文化意義也僅是現今社會的建構,而可以被改變的。性不見得一定會影響人格構成、人性、或人生。的確,這也就是貝里歐堤的看法(cf.
Belliotti 119-125)。
一般對於性保守派的駁斥就是以社會-歷史的角度來批判其本質主義。性保守派的本質主義就是認定性有固定不變的本質,這性的本質則是和男女兩性特質、愛與人格、婚姻、或者生物自然的目的連結在一起。但是人類學顯現了許多偏離所謂性本質的社會安排,社會學則顯示了性在不同社會的建構,性的歷史則顯
示性道德與性文化的不斷變遷。例如在性與兩性特質的關聯方面(例如男性藉著性來佔有女性),母系社會的性安排就和父權社會不同。還例如,有些社會對於排泄和哺乳等活動並不歸屬在性的範疇,有些社會則會沾染性的色彩。又例如,很多社會都曾經歷過女性失去貞操、婚前性行為、手淫等從「不道德」轉變為非關道德的歷史過程。如果性確實有本質的話,那麼這些偏離、差異、變化又將如何解釋?
以上論証的說法或許過於抽像,讓我用一個例子來說明:很多社會都曾經歷過婚前性行為被普遍視為不道德的歷史階段,事實上,這個歷史階段在西方大抵持續到二十世紀中期,臺灣則是二十世紀晚期。這個「婚前性行為不道德」的判斷,乃是根據著兩性特質(如女性貞操的觀念─婚前性行為會傷害女性),婚姻與性的關聯(這個關聯本身則蘊涵了理性控制慾望的道德人格、對所愛者的承諾與不傷害)等等。這個「婚前性行為不道德」的判斷在特定的歷史社會階段似乎是格外真實的,因為女性會為了失去貞操而失去人格與終生的幸福,婚前性行為會產生罪惡感與許多負面的情緒(如羞恥),男性無法容忍自己配偶的婚前失貞,等等。一切證據都顯示「婚前性行為不道德」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是性的無可改變的本質。然而,後來的社會歷史發展卻使得這個性本質煙消雲散。
自從19世紀末性科學與性改革興起後,建立在宗教與形而上的人性之性本質就逐漸在瓦解的過程中,但是保守力量也不斷進行反撲與挽救性本質的戰爭。性倫理與性批判則座落於性啟蒙的知識解放戰爭中心,呼應著各種性改革的政治解放戰爭。在今日,各種各樣的性道德依然存在,正如過去「婚前性行為不道德、
手淫不道德、同性戀不道德?」的道德真理無可置疑的存在一樣。因此在今日提出「性,無須道德」當然不是簡單的「詮釋世界」,而是要「改變世界」。
註腳:
9. 例如 Russell Vannoy, Sex Without Love: A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
Buffalo,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80.
10. 例如,Richard D. Mohr. Gays/Justice: A Study of Ethics, Society,
and Law.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34-38.
但是這些作者也不一定認為同性戀是不自然的。例如Michael Ruse就認為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同性戀是非常自然的:Michael
Ruse. "The Morality of Homosexuality." Philosophy and
Sex. Second edition. Baker and Elliston (eds). Pp. 370-390.
11. Roger Scruton. Sexual Desire: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London: Phoenix, 1986. p.290. Scruton在209-291頁引用詩人Constantine
P. Cavafy題目為〈一夜〉的詩,認為年輕時的一次性經驗會在多年後還留下印記,其實反應了他個人成長時期的「一性難求」的時代背景與保守社會文化。這和當代某些「一夜情達人」的經驗是相反的。
12. 何春蕤,《不同國女人》,臺北:自立晚報,1994。p.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