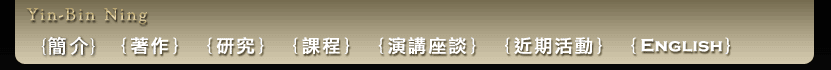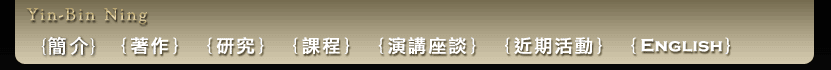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現場先播放一段有線電視臺裡吳宗憲主持的節目片段)
我為什麼要放這個呢?一方面來講,柯裕棻所講的其實就是我的意思,不過她講的比我的好,為了不重複,所以下面我要換個講法。其實我以前也跟馮建三溝通過「電視公共化後到底會生產出什麼樣的節目,會走向何方」這個問題,因為我覺得我看不到一個具體的未來,所以我們就有今天這個對話。
現在讓我先放一兩段電視節目,其實這個電視影帶是隨便抽樣的,目的在顯示今天電視節目在價值立場上的複雜性。我們先看到吳宗憲的節目,這是他在日前「箱屍案」之後的一次節目,把箱屍命案和SM配對都拿出來談。在來賓討論之前節目有先播一段片子,(播影片):
「[影片中旁白]….不過死者的死因和性傾向卻被媒體大作文章。死者因為在SM的交友網站上,結識了性伴侶而發生不幸,又被各種媒體加油添醋,種種不堪的臆測,紛紛出籠。什麼是SM?說穿了只是性虐待和被虐待的英文縮寫,一種危險的性虐遊戲。當然只要你心臟夠大,不分男女種族身高和性傾向,其實都可以大膽嘗試。將SM這樣不見天日的地下活動,今天能如此大鳴大放,百花爭艷,網際網路的功能可說不小。輕輕一敲,臺灣歐美大陸輕鬆串聯,….而這些管道一點也不特殊,他們都只是主流社會被壓抑的另一扇出口。這些網路上的性活動,就好像異性戀參加非常男女一樣,其實是再普通不過的事。的確,他們是出了意外,這個事件給我們的教訓,絕對不是封閉了網路各式各樣的性活動,它只是提醒我們,安全的性不只是要記得帶保險套而已」。(回到節目現場)吳宗憲:「 這就恐怖了,剛剛我們看到的內容….」
上面這一段內容很進步,但是我保證不是我或epicure寫的腳本。anyway,基本上,之後的內容就是節目現場四個人的對談。吳宗憲拿出一個SM玩法的表格,並且評論說:「軟骨地帶,疼痛度百分之九十,興奮度也有百分之九十。爽痛,這怎麼會那麼奇怪呢?」然後有一個來賓說:「爽痛,那不是綜藝節目你們常常在玩?夾住,一二三然後…」。之後就是他們四個人輪流,陳俊志,陳克華、陳文茜還有吳宗憲,四個人輪流在講SM如何變態,噁心討厭,四個人不斷地在那邊講,在一邊講的當中,也講到同性戀比較好,跟SM是不一樣的云云。總之,他們都在複製一些既定的偏見,如同多年前異性戀抹黑同性戀一樣,只是現在抹黑對象替換成愉虐戀SM。
這裡帶來的錄影帶可能有些小差錯,本來要讓你們看的也是吳宗憲的一段,他和幾個跨性別在一起,還請了一位跨性別的媽媽來,他們的對話也很好玩。吳宗憲等人先糗了一下這些跨性別的人,之後他就跟那位媽媽說:「請妳要諒解,因為我們做電視就是這樣子」。基本上,我的意思是說,電視很多時候會自我解構,比如吳宗憲這麼說的時候,也在自我解構電視製作的過程,告訴媽媽或觀眾這一切是在作戲。然後整個節目接下來就做了一些很令人感動的東西,例如鼓勵這些跨性別的人,為他們打氣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類節目對性多元既有抹黑,也有培力。
今天的主題是電視公共化,我先從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公共」觀念談起。
哈伯瑪斯在談公共領域時做了一連串的區分與對比。例如他認為「意見」和「公共意見」(輿論)是不一樣的:「意見」是一個文化內被當作理所當然的東西,例如集體的偏見與判斷等等;相反的,公共意見是公眾的理性討論,是針對公共權力的批評,而且有制度性的保障。此外,自由公開但理性的陳述各自意見,則是形成公共意見的重要條件。
這裡講的自由公開運用理性就是「公共」或「公共性」(publicness)。對哈伯瑪斯來說,唯有真正的公共性的要求,才能使公共權威受到限制,才能使政治的公共論壇對政府有比較制度性的影響。
哈伯瑪斯雖然區分了「意見」和「公共意見」(輿論),但是他還進一步指出當代「公共意見」被炮製的危機,也就是有可能出現虛假的輿論。同時,真正的與虛假的公共意見,也對應著真的公共性與假的公共性的區分。這個假的公共性很接近我們今天打廣告或搞宣傳的公開性,也就是publicity,其重點不是自由公開運用理性,而是搞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換句話說,publicity雖然是公開發出意見,但卻是發言者做公共關係的一部份,實質上也就是宣傳或打廣告。故而publicity由原本的「公開」轉向「公關」。
上述哈伯瑪斯的觀點當然可以被用來看電視與公共性、公共意見、公共論壇的關係。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監督臺灣媒體的主流知識份子(不論是否聽過哈伯瑪斯)其實已經採納類似思考作為改革電視的理想模型。
在針對被利益集團所操控的新聞、叩應節目、政治討論等等形成政治輿論的部份,哈伯瑪斯的批評顯然是很有效的。但是,我們能以同樣觀點來看待像娛樂新聞、八卦新聞播報、以及娛樂八卦新聞的叩應節目嗎?此外,又將如何看待像以模仿見長的「主席有約」、或是結合吳宗憲與陳文茜的「全民立法院」等等既政治又娛樂的節目呢?
一些自命「批判」的知識份子對娛樂八卦新聞節目持負面意見,認為這些節目把娛樂新聞或廣告建構為現實事件──或者,如果我用哈伯瑪斯的話來說,就是娛樂工業把公關促銷活動變成了新聞──因此這些節目並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只是publicity而已。
我基本上很不同意這樣的觀點。我認為這些電視節目其實有著很豐富的、複雜的面貌與社會效應。例如大小S主持的「娛樂百分百」,其實已經成為青少年建構次文化的一個媒介。她們在節目中不斷地重新界定主持人的「規矩言行」,雖然常常以道貌岸然的姿態出現,然而又旋即自我解構;她們也常常遊走於偏差言行的邊緣(但也有「失言」而引發風波的狀況),並且假設新聞局與道德成人正在監視其節目,這種自覺也引發她們「躲在亮處」與成人新聞局鬥智、玩弄青少年政治的情形。
標榜「媒體批判」的知識份子認為娛樂八卦新聞不應該變成重大現實事件的建構,理由是這使得大眾忽略了真正的國家大事。知識份子這種說法明顯地是預設了娛樂新聞的比較不真實、比較微不足道、與瑣碎(trivial)。可是,事實上,娛樂八卦新聞成為大眾的話題,就其社會功能而言,是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而其社會效應根本是非常異質多樣與無法預估的,例如費玉清的同志新聞和臥虎藏龍的新聞,對不同的群體不可能會有相同的社會影響與效應,故而我們不應該一概而論這類新聞必然會有什麼社會影響。
娛樂新聞把公關當作新聞,進而當成「國家大事」,在知識分子眼裡,是愚昧大眾的被洗腦,但是其實看娛樂新聞的人當然都清楚地知道許多新聞或訪問是打廣告、打歌、促銷、炒作等等,因為娛樂新聞也根本沒有嘗試隱藏這樣的事實。倒是看「真正」國家大事新聞的人並不清楚臺灣與國際新聞製作背後的利害與建構。此外,之前小董以及羅璧鈴都主持過八卦新聞的叩應節目,那其實已經形成某種公共論壇,因為之中有包括消費者的不滿,以及對於八卦娛樂新聞及明星的自我解構。當然,所有這些叩應意見的發表,都構不成哈伯瑪私心目中的理性討論。
至於「媒體監督」類知識份子對於綜藝節目的批評,像批評吳宗憲等等問題,之前何春蕤已經反駁過其觀點。大家可以在網路上看到。很清楚的,我們不是全盤地替吳宗憲辯護,因為這些主持人也常常歧視節目中的S/M、性工作者、跨性別、第三者這類性多元。而且我們應該看到每一次綜藝節目主持人被批評後,他們就要力圖表現很道德的模樣,而他們卻是以嘲笑和歧視性多元來表現自己站在主流道德那一邊。所以官方與知識份子對於電視節目的批評監督,反過來又製造了更多的性歧視。
但是不出現在電視上,會不會是件好事呢?你看那些性多元,像濫交的女人、外遇的或劈腿族的女人、扮裝的少年、厭食者等等,出現在曹啟泰主持的非常法西斯的「大老婆俱樂部」節目上,所有的大老婆都總是從童年的成長與家庭背景來找病因,性多元則最後接受道德的審判與被迫認錯。這麼說來,性多元不上電視也好?
可是,性多元就是想要上電視。他們要被看見。有時候是像公娼那樣為了抗爭,不得不被看見;有時候是像早期的同志一樣,被看見就是一種抗爭。這些性多元讓我不得不翻轉哈伯瑪斯的觀點,而接受Andy Warhol的說法:「每個人都有十五分鐘」。對邊緣人來說,publicity(公開/公關)才是重要的;publicity就是visibility(曝光/能見度),publicity就是某種程度上的「文化的可接受性」,就是和大眾做公關,推銷自己的認同與行徑。對於性多元來說,在電視上那十五分鐘與人鬥嘴辯論,表達了一種認同,比不被看見要好。這也是為什麼吳宗憲要比小野好,因為前者給了邊緣人介入的機會。
從這個角度來說,對於性多元或邊緣弱勢的這些主體而言,主觀意見的表達,遠好過公共意見的形成。Publicity(公關)遠好過於publicness(公共)。多樣的場域,遠好過公共論壇。次文化遠好過公民社會。惡性競爭的商業體制好過專家學者組成的電視委員會。
今天給邊緣弱勢主體提供公共空間的不是公共電視,而是財團控制的商業電視體系。這並不意外,正如同國家劇院不會提供電子花車秀。被公民社會排擠在外的鄉野舞臺上正在上演著另一種「公共性」戲碼,雖然也有很多人需要與認同這種另類公共,但是卻不能被認可為「公共」;這是壓迫社會的實相。「公共的」原本就屬於「公民」──屬於中產市民與主流價值。
換句話說,「公共性」不只是規範性質的,也是社會-歷史性質的,因為目前社會歷史形構下的「公共性」恐怕已經預先設定了某種civility、禮儀、規矩、規範。這就像在目前的公共場所內你不能有某些言行,否則會被視為瘋狂、不尊重他人、不懂禮貌等等。
換一個講法,有人或許會問:難道不能有個公共性的電視來實現哈伯馬斯式的理想溝通?讓邊緣人能夠闡述其理念與想法?其實這個理想已經在某些地方實現了,在剛才吳宗憲、陳文茜的全民立法院談SM節目中,對於同性戀的善意呵護,將同性戀和SM撇清,也就是把同性戀經過淨化,然後納入公民社會的同性戀。這讓我們看到了邊緣人在這類公共論壇的未來。在公共論壇內,這些邊緣人必須以公民的身份發言,可是事實上邊緣人並不是公民,而且「非公民」也是目前邊緣人認同的一部份。公共論壇卻要邊緣人認同一個公民身份。
邊緣人說:不能放映A片的電視沒有公共性,但是A片卻被認為不應該有公共性。這是我們目前的矛盾:邊緣人在civic space不能顯示其uncivil的面貌。By definition,邊緣行徑不符合public civility, public decency。所以我對建立真正公共性的電視會抱持懷疑的態度。剛才管中祥提到各種弱勢主體自製節目的可能性,我則認為還不如簡單的說電視改革目標的第一步是放映自拍的A片來得更簡單明暸。不,這第一步太難了,回歸到第零步吧,請新聞局不要檢查干涉電視內容。沒有第零步的可能,那電視改革對邊緣人來說的意義是什麼?在節目存在著底線限制與尺度檢查的狀況下,邊緣主體經過淨化的自製節目,也不過是把邊緣人收編到公民社會內的一種機制而已。
如何改革電視?我的想法很簡單,我要我的電視臺。那就是,每種主觀意見,不論如何不符合公共的理想與標準,都要能有publicity的機會。Publicity不是透過理性討論以形成共識,而是公關──要求被接受、被承認、被看見;要在公共內也有一席之地,因為非如此不能改變「公共」的意義、civility的意義。易言之,呈現所有的意見本身就是目標,而不是達成公共意見的手段。
所以,我要我的電視臺,我要那十五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