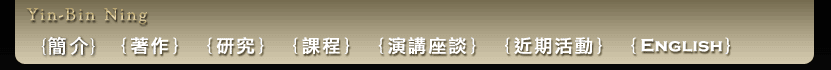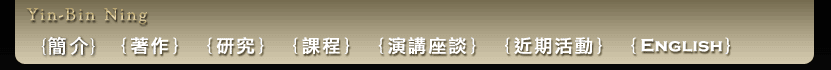我們需要妖魔化強姦犯嗎?
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被稱為華岡之狼的強姦犯受刑人考上臺大後申請假釋被駁回,今年(2001)無法出獄進入臺大社會系就讀1。可是就在同時,曾搶劫藝人白冰冰的受刑人假釋通過,臺大社會系表示歡迎入學,也沒有引發社會恐慌。為什麼兩者有這樣不同的待遇呢?
從刑期來看這兩個個別案例的犯罪嚴重性與道德上的惡性,顯然法律上並未認定前者的強姦案遠超過後者的搶劫案。故而兩者的差異必然是來自社會心理。
當前對強姦的社會心理認知主要源自西方犯罪心理相關研究之影響,然而考察西方的性倫理發展歷史,我們驚訝地發現,十八世紀以前,強姦並未被視為非常嚴重的道德缺失,手淫才是各種性罪惡之首;因為當時的性道德主要建立在生殖功能的考量上,無法達成生殖目的的手淫在這種社會背景中當然是大惡。這個例子顯示,強姦之惡性重大不是個客觀事實,而是社會因不同需要而產生的知識論述變化所帶來的結果。
今日中西社會對強姦犯的心理想像主要來自西方十九世紀所「發明」的「性變態心理」說法;讓我說明如下:起初人們認為,性行為原本就只是生理的需要,就像吃飯排泄一樣沒有什麼很深奧的道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至於不道德的性行為雖然有社會因素,但也沒有深奧的道理,例如強姦就是男女不平等下的性衝動犯罪,賣淫就是社會不平等下的貧窮犯罪,都是「社會的自然史」。但是十九世紀的快速社會變遷使得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成為急迫需要,某些意義曖昧的性行為於是在這個新的秩序中被特殊地看待(包括同性性行為以及其他今日被大眾視為變態的行為﹐如愉虐、反串等等),被視為源自某種特殊的心理人格或某種童年心理發展的障礙。行為成了個人人格的表現,某些性行為則被「病理化」,成為變態心理的表現。這種把性行為賦予心理人格意義的做法,在二十世紀到達了高峰,許多行為只要是不符合社會的需要或道德,就被賦予一種心理人格,被妖魔化。接下來,對於偏差行為的社會控制便可以透過對這種行為的心理化、病理化來進行,用心理治療來輔導矯正那些不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
最近二十年,隨著同性戀、跨性別等等主體以社會運動來抗爭洗刷心理變態的污名,新的「病態心理人格」又紛紛被「發現」:慣性外遇者、濫交者、戀童者、酗酒者、家庭暴力者、網戀上癮者等等都被病理化,這些人也在各種治療機構或團體中費力地追憶其家庭關係與童年,期待拼湊出一個合乎病態心理的劇本。強姦者就是這個犯罪病理化浪潮中比較晚近加入治療大家庭的成員。
其實,就再犯率高而言,竊盜、吸毒、黑幫、賣淫都超過強姦;任何慣性犯罪者的「慣性」,都可能變成某種心理人格的「證據」,然而有的慣性犯罪是「社會自然史」的一部份,不會被病理化(例如中年婦女賣淫),有的則被視為需要矯正其心理人格(如未成年少女賣淫);這說明瞭病裡化沒有客觀標準。強姦原本也可能像搶劫一樣只是一種「社會自然史」的犯罪行為,但是慣性搶劫不被視為心理變態,強姦卻被病理化,強姦犯被妖魔化。
強姦的病理化和妖魔化真的創造出來一個嚇壞人的妖魔。有人想到要和強姦犯一起上課就不寒而慄,但是卻可以和搶劫犯同堂共處,差別就在於後者沒有被病理化和妖魔化,因此也不會造成長期的心理創傷。然而妖魔化的代價同時也使得女人的心理更脆弱,恐懼的陰影更隨時隨地存在,更使得受害者難以走出陰影。以這些真正長期深遠的後果來看,我們還需要繼續妖魔化強姦犯嗎?
《破周報》復刊176期 2001/9/14-9/23;對於當前強姦論述的完整深入批判,請參看《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何春蕤編,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出版,1999年6月。
1. 這位楊姓受刑人自2001年後每年都申請假釋,卻都被駁回,直到2007年9月才假釋出獄,並戴上電子監控腳環。這個事件從2001年8月初開始鬧的沸沸揚揚,直到9月初才告一段落。在這個事件中,保守的婦幼團體與學者專家則趁機推銷美式心理學有關強姦的論述,建構了本地關於強姦的「常識」。這個常識論述把強姦簡化為單一本質,也就是強姦犯的妖魔心理人格所導致,而非因人而異的多樣成因,還有情境、文化、人格、犯罪機會等因素。這個常識論述的副作用當然就是加深了強姦對於受害人的傷害與恐懼;關於這一點可參考下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