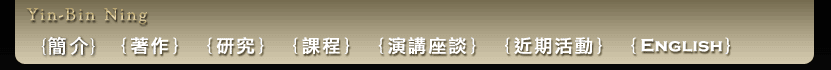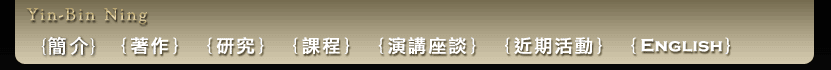當動物遇上性
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教授)
為什麼狗不能假裝痛苦?是因為牠太誠實了嗎?教導狗假裝痛苦是可能的嗎?也許可能教牠在某場合嚎叫,彷彿牠真的痛苦一樣(雖然牠不覺痛苦)。但是使狗這種行為成為真的模擬痛苦之必要環境,是不存在的。(維根斯坦,《哲學探討》)
常見的反對獸交說法認為獸交好像誘騙兒童或甚至強姦,因為動物無法「同意」性行為,其實這個論証乃是出自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與謬誤。以下我將說明,把獸交當作一個需要被普遍質疑的問題,這個「問題化」本身就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而且是忽略性壓迫關係的。
在討論動物議題時,人類中心主義觀點的特性之一,就是將動物賦予牠們所無的心智慧力或特性,或把動物行為的意義不當地去和人類的文化範疇比擬。上述引用維根斯坦對「狗因太誠實而不能假裝痛苦」說法的批評,既涉及了賦予狗所無的心智慧力(假裝),也謬誤地比擬了狗世界中所無的真理誠實的範疇。當然有些動物會裝死,但是這種能力畢竟不是人類假裝的能力,因為後者也同時預設了能夠分辨自己是否真誠的心智。(這裡不排除可能真有少數的動物有特殊的心智慧力,我的重點只是指出賦予動物所無的能力之錯誤)。
一個行為對於當事者(動物或人)具有什麼意義或影響,既當動物遇上性和其心智慧力或特性有關,也和其心智所座落的和所感受到的文化有關。因此,性行為對於動物的意義或影響,既和其心智慧力有關,也和其動物文化(如果有的話)有關。可是最常見的人類中心觀點,卻是以人類文化的範疇去比擬並解釋動物的性行為意義。
人與動物在性方面的差異隨著人類文化社會的發展而變異。在現代,人與動物在性方面的最大不同,在於人類的性是充滿價值與文化意義的行為,所以人類會對一切和性相關的行為有極大的關注,認為其影響深遠重大。但是性對於多數動物顯然並非如此,多數動物既無性文化,也無心智慧力將性行為賦予特殊意義。獸交在人類社會或許引發嫌惡的感覺與文化震撼,但是對動物而言,獸交只是動物與人諸多互動形式的一種。絕大多數動物既無心智特性也無相關文化來把獸交特殊化對待。由此來看,獸交會比其他人獸互動議題更引發倫理問題,乃是出自人類中心主義的產物。
從維護動物觀點來批評獸交的人,常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沒有深入認識獸交,而把所有獸交都當作同一種行為,想像它必然涉及了動物的痛苦或甚至虐待。(這種一想到獸交就想到痛苦和虐待,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反思檢驗的傾向。)但是獸交就像任何一種人獸的互動或關係,例如,就像豢養寵物,有許許多多不同的面貌與互動方式,絕對不能一概而論。我們譴責惡待動物的行為方式,不論那是獸交、養寵物、養殖、或者任何一種人獸互動;但是我們不能絕對地全盤否定所有的獸交,正如我們可以譴責某些飼養寵物(或個別獸交實踐)的惡待行為,但是卻不應該將飼養寵物(或獸交)視作單一整體而全盤否定。
然而飼養寵物中的惡待行為,和其他造成大規模動物更加痛苦的行為相比,嚴重程度與數量又小了很多,所以對於各種惡待動物的批評與關注程度應該和惡待的嚴重程度與數量成比例,否則只是反映了人類中心主義的選擇式關懷。人類文化超乎尋常的關切與批評獸交(雖然獸交中的惡待數量與程度恐怕比飼養寵物的惡待少很多,畢竟飼養寵物的情況較為普遍),只是因為它冒犯了人類(而非動物)的性倫理以及對人獸有別的情感堅持─這也是Peter Singer文章1所指出的(但是本文的哲學觀點和Singer稍有不同)。
再舉一個淺顯的例子。如果動物配合進行人獸交,反獸交者會說,那是誘騙或變相強制;但是如果動物配合人類的撫弄或餵食動物,就沒有人會譴責這是誘騙或強制。換句話說,哄狗進去狗籠睡覺,是可以的,但是哄狗跟你上床睡覺,是不可以的。這一切都是人類中心主義在作祟,反映的是人(而非動物)對性的焦慮。因為對動物而言,性和它其他的生物本能並無二致,除了發情期之外或許更不重要。
獸交常常很直覺地被某些人當作對動物的傷害,而這種直覺則是建立在性壓迫社會中的否性(sex-negative)文化心理上面─也就是把性當作傷害、虐待、貶低、侮辱的傾向。性被當作「有問題的」或壞事(傷害、貶低等),乃是人類(而非動物)性文化的特色,因此獸交也就被直覺的認為是對動物的傷害。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文化把性被當作正面的好事,今天我們根本不會覺得有需要討論(甚至批判)獸交問題。
輕易地質疑獸交整體是錯誤的。畢竟動物不都是一樣的,某個人與動物的關係也可能是獨特的,工具化動物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與不同動物發生愛的、性的、友好的關係所需的控制技巧都是不同的。考量這些複雜面向,知識份子怎能在充滿社會成見的氛圍中也普遍化地去質疑獸交呢?其次,由於主流女性主義目前接合了否性文化,因此在面對獸交時也很輕易的就套用簡化的性別權力公式,認為女人獸交圖反映了女性被性別歧視,男人獸交圖則是男性欺壓雌性的動物。這其中不但暗含了「性與獸都會貶低女/雌性」的假設,也暗含著「真正(好與正常)女人/男人」絕不會獸交的假設。
有些人或許可以接受人獸有文化差異的說法,可以承認人類中心主義的眼界侷限,甚至可以理解否性態度的深層影響,但是他們還是堅持,性必須有雙方的同意,而既然動物無法真正行使同意權,那麼獸交還是不可取的。不過,現代社會以「同意」(consent)為基礎的性倫理根本不適用於動物,因為現代契約論的「同意」預設了大多數動物所無的心智慧力。人可以在恐懼、厭惡、逃避、不情願、痛苦的情形下行使「同意」(如同意手術開刀),但是動物沒有這種能力;同樣的,人可以在期待、想望、需要、歡喜、願意的情形下行使「不同意」(如心裡很願意但仍因顧忌而不同意),動物就沒有這種不同意的能力。基本上談論動物是否「同意」性行為,乃是範疇的錯置,就如同我們不應該說狗能假裝痛苦或能不假裝痛苦一樣。
多數現代社會的法律基本上也不認為幼小的兒童具有「同意」或「不同意」的心智慧力,故而餵食幼兒等活動並不涉及幼兒是否「同意」的問題;兒童拒絕接受餵食,並不構成「不同意」,同樣的,兒童即使看似快樂地接受性行為,仍然不被法律視為有效的「同意」。以「同意」來談幼兒(或狗),就像談「狗假裝痛苦」是個笑話一樣。有人會問: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將狗當作兒童來看待呢?講「同意」的契約論者會認為,兒童被視為具有人格,分享成人的文化,並且預期兒童終究會具有同意的能力;但是動物則不然,成年的狗也無法分享人類文化。兒童成年後強姦他人是罪行,但是幼狗成年後仍然無所謂的強姦罪。這就是差別。(如果不能把狗當作兒童,那麼能否把兒童當作狗來看待呢?)
總之,在道德評估個別獸交行為時(前面已經說過評估整體獸交是無意義的),從現代性倫理的「同意」角度來評估,乃是範疇的錯置。道德評估應該是將個別獸交與其他獸交比較,與所有其他人獸互動去比較。這些比較的指標可以是動物的苦樂感覺(程度與數量等)或生存機會與處境等;同時這個比較評估也應該是歷史的,而且是具有文化相對論觀點的。我有理由相信,在這種評估下,許多獸交不會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沒有很顯著的動物權侵害問題。
比較不習慣抽像思考的人或許會在此問:大多數動物在獸交時會表現出逃避或配合、苦與樂等等,雖然這不同於人類性倫理所依據的「同意」能力(前面已經說過人類的「同意」可以和苦樂或逃避配合與否無關),不過這不也是一種動物式的同意嗎?但是發問的人忘記了,如果這種「動物同意」會成為道德問題,那麼每一次人類限制動物的行為範圍(如把鳥養在籠子中或者用鏈子拉住狗不讓它走自己的方向),每一次人類侵犯動物的自然生活(如釣魚或飼養寵物或喝止寵物在地毯上大小便)等等,無數的人獸互動都會有這種「動物同意」的道德問題。正如我在上一段所說的,若是撇開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性文化偏見來對所有人獸互動都加以比較,那麼獸交根本就不是什麼顯著的問題(畢竟人是天天都在關、殺、吃所飼養的動物,但不是天天與之性交)。
從動物權的運動觀點來看,比起動物恐懼者或恨動物者,動物戀者顯然是更「天然的」盟友─至少從動物的角度來看。但不論是否「天然」,運動努力的方向當然是要促進動物戀能朝動物權理念方向發展邁進,去影響動物戀者的論述與重新詮釋其實踐。這意味著不能如俗世一般地抹黑動物戀這個異己牠者。就好像在過去同性戀或性工作被社會抹黑誤解的時刻,女性主義運動應該平反同性戀與性工作,而非只是「問題化」(problematize)同性戀與性工作中的嗑藥、愛滋、濫交、通姦、戀童;這些現象並非不存在,但是婦女運動應該要在整體上肯定同性戀與性工作的可能價值,並創造出一個寬容出櫃的社會條件,而非附和著簡單的成見指控,或覺得同性戀與性工作在抗爭時所依據的女性主義理論高度不夠等等。同理,動物權者應該做的,是幫忙創造動物戀者出櫃的社會寬容條件,對其面貌有更多的真實理解;這樣一來,動物戀者也可能因而能幫助動物權者自我反省殘存於其性觀念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偏見,以及根深蒂固的反性/否性意識,而為動物權者創造出新力量的契機。畢竟,沒有經過性權洗禮,動物權者也往往是和保守大眾一樣反性否性的。
在現有少數的動物戀者出櫃文獻中,我們看到的並不是虐待動物或讓動物痛苦,相反的,有些動物戀者可能具有比動物權者更多對動物的愛戀慾望。動物權者不要重蹈歷史上污名化各種性多元(性少數)的覆轍。
在目前臺灣社會的脈絡下,動物權有正當性,性權沒有。動物解放沒有污名(因為臺灣的動物權人士並沒有像英國動物權武裝鬥爭派那樣行動),但是性解放有污名。這是兩者在目前社會權力位置上的一個重要差別。但是我認為,既然動物戀與獸交是動物權運動與性權運動的交集點,那麼,重點似乎不是急著去批評獸交有無或者如何曲解了動物權理念,而應是批判反獸交者如何利用了動物保護的說法來進行緊縮言論與開放風氣吧!
人讓馬牛驢騾駱駝大象馱重物,以奴役的方式對待,飼養雞鴨鵝豬羊牛,宰來吃掉,反獸交的大眾很少反對,更不會成為新聞或討論關注焦點。唯獨當動物遇上性,一切都突然變得猙獰起來,連衛道人士也人人「動物權」朗朗上口。動物權論者能不警覺乎?
(原載於2003年4月25日─ 5月4日《破報復刊》256號。本文寫作脈絡是針對何春蕤的動物戀網頁事件所引發的動物權與動物戀之爭。)
2006年後記
本文的最後一段原來是某位朋友寫給我們的信的內容,現在才有機會註明一下。此外,我講的「動物權」在狹義上指著主張動物有生命權等諸權利的派別,有著動物解放的烏托邦衝動,是近幾十年興起的基進思潮。另方面,「動物權」在廣義上或鬆散的意義上還可以泛稱至少回溯到十九世紀的人道對待動物、動物保護、以及動物福利等運動思想。在運動與哲學思考中,由於狹義的動物權的基進性,故而比較有理論上的旨趣;同時,狹義的動物權也和性解放運動共享了烏托邦衝動。
對於這個動物權與動物戀關係的討論,我覺得還有一個方向可以在未來繼續探索:社會運動彼此雖有差異矛盾,但是也有很多共振通識之處。傳統批判理論對於結構的支配關係的設想(例如激進女性主義對男女支配關係的設想),總是把支配關係設想成單一巨大的(monolithic),宰制壓迫則是一面倒式的全面性籠罩、沒有任何縫隙或逃逸餘地,被支配者則是絕對弱勢、完全無力的受害者,這些錯誤設想在後來批判理論的發展中逐漸被修訂(正如那些曾和激進女性主義論戰過的人所習知的)。動物解放論述在設想人獸之間的支配關係時,當然必須避免重蹈過去批判理論的錯誤。
更有甚者,由於動物解放處理的是人獸之間的支配關係,而非人與人之間的支配關係,因此動物解放所面對的異己他者(獸),和其他解放運動或批判論述所面對的異己他者(人)有所不同。雖然一般批判論述中的異己他者是被貶低為次等人、非人、具有獸性的人等等,但是在解放運動中還需要恢復異己的人性(這是人人平等的基礎)。因此,如果以一般解放論述的支配關係來設想人獸之間的支配關係,忽略獸性(animality),則可能再度落入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就是完全從人類價值與經驗來詮釋世界。(以上想法是來自我和一位對「獸性」有興趣的研究生的討論)
(我所謂的「獸性」不是所謂的「自然天性」(nature),因為「自然(天性)」是和「人工(人性)」抽像對立的,兩者隔絕互不相涉,但是「獸性」卻是可能在人獸互動中被消蝕或被喚發。我認為解放性質的人獸互動就是能喚發人的獸性、喚發在文明化過程中被消蝕的獸性、置疑了「人性尊嚴」。)
以激進女性主義所設想的性別支配關係模式,套用在人獸的支配關係,固然是一個錯誤,但是另一個常見錯誤則是訴諸動物的「自然(天性)」來評估人獸關係,就像傳統主義者訴諸「自然」來評估同性之間的性關係一樣的錯誤(傳統主義者認為同性戀是不符合自然的)。有些人(如林逢祺)會認為人獸的性關係不自然、不順應動物的「自然天性」,因為動物的天性並不是想要和人發生性行為的;不過在人獸關係中(不只性關係,還有很多其他關係)訴諸自然是很模糊的觀念,例如餵食、豢養、寵愛、馴服、家畜(domestication)等是否自然?畢竟,所有的家畜行為都涉及「限制」(限制野性、限制活動範圍等),這些是否順應自然?同時,訴諸自然是否對動物有利呢?例如,是否應該讓動物「自然死」,還是去看獸醫?當動物自殘時、或者傷害他人時,是否應該制止這種「自然天性」?當某動物反抗「強姦」時,是否應該協助該動物反抗,還是順其自然?(另方面,有些飼主卻會制止「兩相情願」的交配)。許多傳統主義者(例如基督教)訴諸「自然」這樣的模糊觀念,並且堅持著人獸的「自然」支配關係─亦即,訴諸動物的自然天性也可能會成為支配動物的說詞。
總之,自然/不自然之分不是適切的觀念來評估人獸互動,同時,性或非性之分也不應該是評估人獸互動的基準(例如,吃飯時看著動物的獵食,或者手淫時看著動物的交配,以上兩種人獸互動都應該用同一尺度評估,而不對性互動另眼相看)。從這些評估原則出發,以人類互動的總類與數量而言,人獸的性互動在人類文化中不成比例的被著色渲染,從而掩蓋了日常例行的與系統制度的各種人獸互動(但是這意思不是說,我們因此不要去檢視人獸的性互動,而像是說,在反思勞資關係時,檢視老闆持槍搶劫工人財物的偶發案例,和檢視老闆剝削、貶低、控制、規訓工人等作為,應該在文化呈現中有適切的比例)。其實人獸互動越是日常例行性質、越是系統制度性質,就越值得我們檢視反思;即使是「愛護」、「寵愛」的人獸關係也不是沒有問題的(這種互動可能消蝕人與獸的獸性);有時新的人獸關係所需要的實踐與情感資源可能反而來自現在仍處於邊緣或不循常的人獸互動(像有少數人自認為是某種動物,其認同喚發了此人的獸性)。
易言之,提出「獸性」這個範疇與視野,並不是為了與「人性」對立,也不只是為了確立動物在自然存在中的獨特位置,而同時是為了批判性地看待「人這種動物」(human animal)如何在文明化過程中確立其「人性(尊嚴)」,並且以種種法律與社會控制繼續消蝕獸性,包括了對動物的支配控制,以及對人類獸性的支配控制(如對人類飲食、排泄、互動??與性活動的控制)。
最後順便一提的是,對於「動物戀是既存現象」的說法,有些人質疑「存在是否合理?」、「存在是否就具有價值?」,這些對動物戀的質疑其實都只是從既存道德出發所作的判斷。然而,對一個「既存現象」,最不應該的就是匆促地以「既存道德」來作判斷,因為現有的既存道德或既存體系(價值、功能)未必能經得起歷史與社會變遷的考驗。既存體系所肯定的事物,我們要存疑;既存道德認為是錯的現象,我們也不能盲信從眾。對那些被既存體系與既存道德所貶低譴責的事物,我們要先檢視這些事物的內在價值與可能功能。像颱風地震等自然現象、癌細胞、宗教、突變、稀有動植物? 等等似乎對人類有害或無足輕重的事物,其存在往往具有內在價值;若沒有內在價值,也往往是在一定的系統內有其功能(例如,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故而其存在也可說是合理的。然後,我們要從社會正義、歷史與跨文化比較的整體視野來檢視既存現象。如果只從現有既存的道德或體系來判斷事物的價值和合理性,往往會因為本身道德或體系的歷史眼界和社會屬性之限制,而做出矇昧狹隘的判斷;尤其是,當人們對某類事物(如動物戀這些性多元)不但還沒有充分理解,而且由於在社會結構中有著深層的壓迫關係(如性的不平等關係乃建立在歷史、社會、政治、法律、文化、經濟、心理等多方面長期深入的支配壓迫),此時對動物戀做出的負面價值判斷其實是缺乏反思的。正如同,「有些人主張不殺生」乃是一個既存現象,人們當然可以用現有常識說「人類需要生存所以必須吃動物的肉、以動物做實驗等等」,從而質疑「不殺生」這一既存現象的存在合理性與存在價值,但是這種質疑是否忽略了人獸之間長期與深入的支配關係呢?以及,「不殺生」是否有可能為下一階段的人獸關係的進化提供了必要資源呢?同樣的,在性愛沒有禁忌與壓迫的社會中,動物戀也可能會對人獸關係的進化提供必要資源的。總而言之,我們不應該以「既存道德」來輕巧地論斷「既存現象」。
(包含後記的全文收錄於何春蕤編著《動物戀網頁事件簿》(臺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