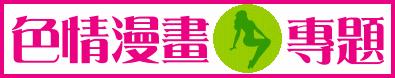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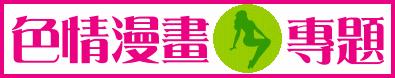
| 漫畫的原罪 | ||
| 2003.11.27 中國時報 | ||
|
◎李衣雲 看漫畫看了二十多年了。常常想,跟漫畫的不解之緣已經到了根深柢固的地步了吧。當學生的時候背著老師父母,和同學們分享著絞盡腦汁弄到手的漫畫書,那種記憶回想起來是那麼的溫馨。老朋友見面了,幾段寒暄之後,總會問起:「對了,『千面女郎』和『尼羅河女兒』完了沒呀?」漫畫、卡通已經是我們那個世代以來的人共通的記憶了,就像我們的上一代講起布袋戲的雲州大儒俠、漫畫的諸葛四郎一樣,那樣溫馨又會心一笑的溫暖。 漫畫與動畫是我們這個世代的童年與成長的歷史,所以,我們也牢牢地記得總放在漫畫最後一頁的「國立編譯館審查通過 熊先舉」的字樣。也許終我們一生,這個名字都會在我們的腦海裡,伴隨著漫畫被塗改、被打壓的歷史。 漫畫有著它被強附上的原罪。因為它以圖畫為基礎容易接受、因為它的閱讀難度低而廣布性高,所以,它被視為兒童的讀物、被視為煽動性的出版品。於是,兒童、青少年的問題總就輕易地與漫畫連上了關係。這是當然的。對社會來說,它是多麼容易的代罪羔羊,讓其他一切問題都遮掩了起來。 於是,經過漫畫審查制十多年的桎梏後,每隔一時期,漫畫總要被拿出來韃伐一番,彷彿這已是一種慣性,一種不把漫畫當成創作的慣性,抑或是即使漫畫是一種創作也不得享受創作自由的慣性。 只是,在彷彿民主自由的氛圍中,我幾乎以為這樣的慣性已經消失了。 幾天前忽而在長鴻出版社的網頁上,發現了一個叫作「臺北市漫畫及人體圖片出版品租售管理自治條例」,也就是臺北市政府單獨規定,以後在臺北市出售的漫畫,封面上一律必須放上封面大小十分之一尺寸的「普」或「限」的字樣,以保護青少年。 反反覆覆看了這條新聞四、五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限制級的漫畫封面上不早就有「限制級」的一條標示了嗎?什麼時候,漫畫分級制的落實,竟與標示的尺寸大小有了決定性的關聯?如果「限制級」這一行字沒有辦法阻止未成年人閱讀不適齡的作品,那麼,訂定法規的官員們憑什麼認為巨大的標誌就有嚇阻的效用呢?標誌的尺寸除了破壞了創作與封面設計的自由外,大概也只剩下滿足做官的人那種「我有做事哦」的心態吧。 頓時間,那段「漫畫審查制」中漫畫受盡打壓的過去又浮現在眼前。激動的我寫了抗議的信件投進了臺北市政府的信箱。臺北市府的效率很好,第三天就收到了迴音,只是,令我瞠目的是,回信裡暗指著我反對了大多數民眾要求分級的民意,同時表示分級制是中央的規定,叫我去找行政院新聞局抗議。然後,告訴我這法案已到了市議會,與市府早無相關了。 從頭到尾,對「標誌尺寸大小與傷害創作自由」這個重點,隻字不提。 再一次反覆看著自己的文字與對方的文字,看對方是從何處看到了我是反對分級制的。當然,語言學家說的,文字語言就是為了誤解而存在,就像做官的總是打官腔一樣吧。 其實想說的只是,漫畫不是青少年的專利。而青少年的保護也不是做做樣子的標示就能達成。 分級制的立意是好的,但好的立意不必然成為「善」的結果。沒有辦法落實的好的立意,只是一場官場走秀的徒然。而利用一個善的名義,去實施違憲並侵害人權的作法,不免讓人杯弓蛇影,擔心起下一步又會是怎樣的恐怖傷害。 蠶食總是一步步開始的。 也許有一天,臺北又會回到那段看不到漫畫的空白日子。 最終想起的是那句法國大革命裡的名言,只是,這一次變了個樣子:「保護青少年呀,多少罪假汝之名而行之。」 (作者著有「私と漫畫の同居物語」一書,現於日本東京大學社會情報研究所進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