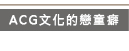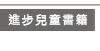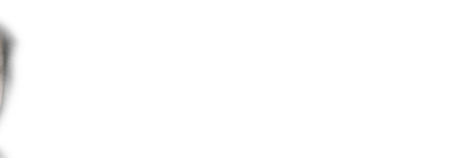
作者:斯塔西·希夫
【40年來,人們一直在問究竟是什麽激發了《洛莉塔》這個令人震驚故事的靈感。斯塔西·希夫相信自己已經最後找到了出人意料的答案。】
1956年10月的一天,來自美國文學雜誌《隱士評論》的一群編輯們跟一位叫弗拉迪米爾·納巴科夫的大學教授坐在紐約的一個公寓裏,討論他們關於連載他最新一部長篇小說《洛莉塔》的計劃。
納巴科夫被問及是如何瞭解到這麽多有關小姑娘隱私的。這部曾經被一系列出版商所拒絕的書描寫了一位中年人跟他12歲養女的一種戀童癖愛情。納巴科夫的妻子回答了這個問題。據她所說,他曾經坐在公共汽車上仔細聆聽人們的交談。他還曾經常出沒于小孩子的遊戲場所,直到他的行徑引起了非議。除此之外,他的生活中就再也沒有別的小姑娘了。
這些都是真的,但並非是全部的真相。弗拉迪米爾·納巴科夫並非《洛莉塔》中有戀童癖的亨伯特·亨伯特,但他卻寫下了衆多有關中年人迷戀小姑娘的作品。
等到《洛莉塔》問世時,他跟維拉的關係已經經受了很多波折,包括一次當真的私通,好幾次逢場作戲的調情,還有跟他的一位十幾歲女學生近乎通姦的戀情。他還對青少年的性成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維拉·納巴科夫以前所未有的投入程度參與了丈夫的工作。在她於1991年逝世以前,納巴科夫的傳記作家們就是圍繞她的作用來寫的。現在,根據大量尚未出版的材料,我們已經有可能講述《洛莉塔》創作的全過程--以及維拉和其他女人對弗拉迪米爾所産生的影響。
維拉於1923年在柏林第一次遇見弗拉迪米爾以前,曾經在聖彼得堡度過了一個富裕的童年,並與她的家人(和47件行李)爲逃離布爾什維克政權而有過一段夢魘般的經歷。弗拉迪米爾也是"俄國難民潮"的一員,並爲爭取其作家生涯而努力奮鬥過。當時他正好24歲,風流倜儻,頗具貴族氣質,女性對其趨之若鶩。在剛開始追求維拉時,他曾列出了一個近30位過去女朋友的名單。
有情人終成眷屬,他與維拉於1925年結婚。他倆都純真而熱烈地依戀著對方。到了30年代中期,他們已有了一個嬰兒,並試圖爲了逃避納粹統治而移居法國(維拉是個猶太人)。但直到1937年,他們才真正逃離德國。弗拉迪米爾首先借文學巡迴演講的機會,出訪了布魯塞爾、倫敦和巴黎。
一周以後,當維拉與他會合時,弗拉迪米爾向她承認自己已經迷戀上了一個住在巴黎,名叫艾琳娜·尤麗埃夫娜·格達尼尼的俄國姑娘。他當時正沈醉于私通的甜蜜感覺之中,並以爲自己會離開維拉。
艾琳娜比維拉小3歲,是一位活潑和非常情緒化的金髮女郎,曾有過一個短暫的婚姻,現在已經離婚。她的笑聲像銀鈴般悅耳,並具有很強的幽默感;尤其喜歡玩弄文字遊戲。弗拉迪米爾曾經向她說過自己以前的風流韻事--在格呂內瓦爾德畫廊裏跟一位德國姑娘的邂逅;1933年跟一位法國姑娘的四夜浪漫;一位眼神憂鬱而迷人的悲劇型女性;一位曾經向他提出過猥褻性要求的前學生;以及其他三、四次毫無結果的邂逅等。然而艾琳娜卻癡心地崇拜他的頭在她枕頭上留下的印痕和他丟在煙灰缸裏的煙蒂。
"納巴科夫的學生們注意到老師完全被這位漂亮姑娘迷倒了。"
弗拉迪米爾淚流滿面地公開承認沒有艾琳娜,他就無法再活下去。他對她的那種渴望是以前從來沒有體驗過的--但與此同時,他跟維拉一起度過的歲月也是"晴空萬里"的。納巴科夫酷似自己小說中的一個人物,完全被激情所壓倒,無法逃避自我的深淵,令人心碎地脫離了他的自我形象。
他寫給艾琳娜的那些信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搬了14年前他寫給妻子信中的話。他談論冥冥中的性格相符,對倆人的印象一致而驚歎不已。他的坦白並沒有使他停止寫情書。如果說有什麽變化,那就是他對艾琳娜的思慕變得更加絕望了。
維拉對丈夫這次婚外戀的反應是責怪自己。她覺得自己忽略了丈夫,後者則向艾琳娜報告妻子正想方設法彌補對他的忽略。"她的微笑使我痛苦欲絕,"他苦澀地宣稱。然而當維拉發現丈夫還在給情人寫信時,家庭裏爆發了劇烈的爭吵。弗拉迪米爾描述說他恐怕這樣的風暴會使自己最終被送進瘋人院。
艾琳娜的反應是提出願跟弗拉迪米爾私奔,去浪迹天涯。他回答說維拉已迫使他結束婚外戀。他不能再給她寫信了。這使得艾琳娜跳上了去戛納的第一班列車,納巴科夫就住在那兒。到達戛納的那天早上,她徑直找到了納巴科夫的公寓,並守候在外面,直到她在納巴科夫帶兒子迪米特爾去海灘時截往了他。他跟她約定那天晚些時候再見面。
當他們在下午漫步朝港口走去時,他解釋說他雖愛她,但還做不到對生活中的其他東西關上大門。他懇求她耐下心來,保持不介入的態度。艾琳娜第二天就傷心欲絕地去了義大利,認定維拉已經設法將弗拉迪米爾騙回到了婚姻之中。她在第二年年底出席了他在巴黎舉行的一次朗誦會,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見過他。
納巴科夫仍然是她生活中最偉大的情人。20多年以後,當讀到《洛莉塔》前半部分時,她報告說這小說寫的就是她和美國。
納巴科夫對於他跟艾琳娜戀愛一事的反應就是創作了《禮物》。這部長篇小說被描述爲他對忠貞愛情的頌歌。這個有關一位青年藝術家的故事讀來就像是他對一位女人充滿感激的頌歌,而那位女人從各方面看都很像是維拉。一位給主人公引來"無望的絕望"這一熟悉標簽的年輕姑娘轉瞬即逝地出現在小說結尾處。到了1939年底,他還寫過一篇題爲《邂逅》的中篇小說。關於它不尋常主題的流言不脛而走--40多歲男人誘姦青春期前小姑娘的故事在當時還不多見。
維拉喜歡相信弗拉迪米爾的意志力跟她一樣堅強,但真相並非如此;他最後一次偷情並非是跟艾琳娜·格達尼尼。
當法國陷落於德軍手中時,納巴科夫夫婦逃到了紐約,在那兒他們被以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和作家瑪麗·麥卡錫爲中心的一個文學圈子所接受。弗拉迪米爾在麻塞諸塞州的韋爾斯利女子學院找到了一個教職。他被要求起一種"籠統的激勵學生靈感"的作用。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但並不完全是像校方所設想的那樣。 "我上學時學習法語、俄語和納巴科夫先生,"一位學生回憶道。 "我知道每次上他的課,我總是塗上睫毛膏,"第二位學生記憶如新。 "我們都愛他愛得神魂顛倒,"第三位校友如是說。
對於許多女學生來說,他是她們所見過的第一位歐洲人;他完全符合歐洲波西米亞藝術家的浪漫概念。最妙的是他似乎身體虛弱,急需有人來照料他。假如說姑娘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他的異端邪說,那她們馬上就能看出他本人不太正統。"他是我一生中所見過的唯一一位穿藍色和粉紅色襯衫的人,"一位學生評論道。他興高采烈地告訴一位嫵媚的金髮女郎說他總有一天要把她寫進小說。
有關他的一切都反映出另一個世界,一個保留了舊世界溫文爾雅和淵博學識的,遠離無數小圓領、馬靴和短襪的遙遠國度。很少有女學生相信他的心思是放在那些基本的俄語語法上。有一些女學生更清楚地知道他的心到底在哪里。
他的大部分學生都用愛慕的目光注視著他;差不多同樣數目的學生觀察到,他的注意力是爲班上最漂亮的姑娘而保留的。假如說他沒有公開調情的話,那他的殷勤卻是異乎尋常的。"啊,羅傑斯小姐,我看到你添了些什麽新的東西,"當一位塗著染睫毛膏,顯然是很得寵的女學生手指上戴著訂婚戒指從春假回來時,他這樣評論道。
"他確實是在調情,但其物件總是些木訥的啞鈴,"一位女校友回憶道,她跟其他人一樣意識到他的目光越過了自己。
"我選修了俄語課,並連帶修了一門關於弗拉迪米爾·納巴科夫的課,"一位於1943年爲院刊採訪過這位新教授的三年級學生凱瑟琳·裏夫斯·皮布林斯後來回憶道。"他的確喜歡年輕姑娘,不僅僅是小姑娘。"
那年秋天,他倆開始牽著手在校園裏長時間散步,互相接吻。皮布林斯這位出生于孟菲斯的美少女感情豐富,生性傲慢,精通於調情的藝術。她並沒有忽略了戰時燈火管制的內在美。"我當時非常年輕,男人是我研究的物件。我喜歡這個男人是因爲我讀不懂他,"她這樣回憶起他倆的互相引誘。
納巴科夫很快發現他的學生知道《愛麗絲漫遊奇境記》,倆人在校園裏散步時開始互相援引書中的段落。他們"蹣跚又踉蹌"地穿越漆黑的冬夜,在學生會咖啡廳和城裏的咖啡館之間漫步盡可能長的距離。納巴科夫用他又長又厚的大衣將倆人裹在一起。
他們的交往中有相當數量的接吻和愛撫。校園裏的私通在當時很難找到合適的場所,也不能爲周圍的人們所接受。在皮布林斯的竭力鼓勵下,納巴科夫無疑渴望能從這次婚外戀中得到更多,這使得皮布林斯的朋友們都感到驚愕。
那些認識他的人評論說,納巴科夫就像一個"喜歡偷聽的貪婪人類學家"那樣在校園裏到處打探;皮布林斯發現他抄襲她的美國俚語,老是蹦出幾句自己不太熟悉的詞。(她在他後期小說中看見了1943年冬天的影子。)
這場感情遊戲在暮冬時分戛然而止,納巴科夫的貪婪開始使皮布林斯感到膽戰心驚。有一天下課以後,她對教授不認真擦黑板一事進行了評論。至少有一層西裏爾字母跟下一層字母混淆在一起。"那麽你能讀這幾個詞嗎?"納巴科夫一邊問一邊在黑板上潦草地寫下了三個詞,然後又同樣迅速地把它們擦掉。他所寫的是俄語"我愛你"。結果皮布林斯退出了這門課,同時也甩掉了教授。
人們對他後來泡妞的反應並不是那麽熱烈,儘管這並不是由於納巴科夫缺乏持久性的緣故。有一個曾爲他塑了半身像,並且他數次試圖與之調情的女學生用談論自己男朋友的方式來回敬他的獻殷勤。但與此同時,她又感到自己深愛著他,爲他的明顯無助而怦然心動。納巴科夫始終持玩世不恭的態度,並不因遭到拒絕而感到生氣。另一些人覺得他是一位極具挑逗性的人,但由於她們的天真無邪,對他的獻殷勤並不在意。
有一次他向一個學生建議,他倆同坐在一張狹窄的長沙發裏來研究一組紀念"美麗的美利堅"的壁畫。"你知道這有多奇妙嗎?"納巴科夫煽情地說道,表面上他是在談論藝術。當時的那種熱情似乎是真誠的,但回想起來,則顯然是一種手段。
只有少數女學生知道其教授是結了婚的。那些看見過維拉的人認爲她長得很美,"漆黑油亮的長髮幾乎落到了肩膀,白裏透紅的皮膚顯得非常光滑。"
維拉肯定知道女學生們對丈夫的崇拜,但她舉止中沒有迹象表明她還知道些別的什麽事。納巴科夫流露過自己對凱瑟琳·皮布林斯輕盈而修長身材的讚賞,並且告訴過妻子:"我喜歡小乳房的女人。"多年以後,維拉否認他說過此類的話。"不,從來沒有!"她抗議道。"一個俄國人不可能這麽說。"
1947年,弗拉迪米爾開始創作一部"有關男人喜歡小姑娘的中篇小說"。他還找到了一個新的教職,在紐約州的康奈爾大學任俄國文學助理教授。到了1951年,他和維拉的經濟狀況出現了危機。弗拉迪米爾的書銷路不好,他已在朋友那兒欠下了幾千美元。
《洛麗塔》的誕生歸功於弗拉迪米爾,但她的生命依賴於維拉。
沒有別的更能像這部新的小說那樣挽救他們的困難,據他所說,它"描寫一位極其注意倫理道德的中年男子的窘迫。他非常不道德地愛上了他13歲的養女。"一個真正頭腦清醒的妻子也許會勸丈夫把注意力放到某個更能成爲賣點的主題上。當時在大都市之外,人們還都比較保守。然而對於藝術而言,至少是對弗拉迪米爾的藝術,所有的賭注都會失靈。
維拉用打字機打出《洛莉塔》的草稿,而她的丈夫則規劃著男女主人公的性成熟,並研究了性變態,他從圖書館借出了《青春期少女》一書,而且還翻閱了《最佳青少年故事》、《美國姑娘》、《正確預測所有少女》等書籍,爲消除粉刺軟膏和但佩斯月經棉塞作了筆記。到了1953年秋天,弗拉迪米爾每天伏案寫作長達16小時。
《洛莉塔》的誕生歸功於弗拉迪米爾,但其生命卻有賴於維拉。有好幾次書稿都差點被燒成灰燼。早在1948年,維拉有一次出門時看見丈夫在後臺階旁邊的鍍鋅鐵皮罐裏點起一堆火,正要開始將手稿塞進去燒掉。她大驚失色,急忙從火中救出了殘存的幾頁手稿。
她丈夫開始抗議。"快從那兒走開!"維拉命令道,當她奮力踩滅手稿上的火時,弗拉迪米爾乖乖地服從了命令。"我們將保存這些手稿,"她宣佈說。人們至少在另外一次場合看見她將丈夫認爲寫的不好的手稿整理歸檔。納巴科夫記得維拉在1950年和1951年中有好幾次阻止他"因受技術性難題的困擾和對自身能力的懷疑"而試圖將《洛莉塔》付之一炬。
只有維拉一個人知道她丈夫正在製作一個"定時炸彈"。它的內容是如此具有煽動性,以致他塗掉了日記中所有關於性變態和跟未成年人結婚的研究性摘錄。大量的文學作品手稿曾經被燒掉,包括《化身博士》和《死魂靈》的初稿。《洛莉塔》在納巴科夫於50年代創作該作品的環境和大氣候下沒有遭到同樣的厄運,正如他所說,完全驗證了維拉將常識拒之於門外的能力。
她並非完全順從他所有的計劃。當弗拉迪米爾向同事們宣佈他將寫一部有關一對暹羅雙胞胎互戀的小說時,維拉斷然阻止了他。"不,你不會寫的!"她規勸說。
1953年12月,維拉請求與《紐約人》雜誌的凱瑟琳·懷特單獨會面,其原因她不想直接見諸文字。她攜帶手稿來到東48街懷特的家門口。那卷手稿上沒有寫退稿的地址。弗拉迪米爾不敢使用郵局,因爲用郵寄方式來散佈淫穢品是違法行爲。維拉解釋說手稿沒有使用作者的真名,因爲她丈夫想以一個筆名來出版這部小說,這個"亨伯特·亨伯特"的筆名很快就被泄露了出來。懷特看完了手稿以後告訴弗拉迪米爾說,她自己有五個孫女兒,假如她不說自己被小說弄得心神不安,那就是在撒謊。此外,她絲毫不能同情精神變態者。
維拉沒有此類疑懼。這並不意味著她對於丈夫出版有關中年歐洲人瘋狂追求青春期前少女這樣一部充滿色情味的小說--以及公衆的誤讀--所帶來的危險毫無知覺。她詛咒公衆無法區分作者與主人公之間差別的天真和無能,同時也承認出版此書可能會造成某種"不愉快"。
她告訴嫂子埃琳娜:"在你從頭到尾讀完它之前,不要輕率地下結論。它根本不是色情作品,而是對一種可怕躁狂症的深度所進行的最微妙探測,它探索了一名無助少女的悲慘命運。"她非常理解書中所描述的50年代美國。埃琳娜絕不能將此書到處亂扔:"把它藏起來,不要讓你的兒子看見。"它不是兒童適宜的書。
第一個讀到這部小說的出版商帕特·科維西甚至認爲《洛莉塔》對成人也不適宜,至少是對那些不願意去坐牢的成年人。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商的華萊士·布羅克韋在讀完小說後說他的同事們認爲此書只能算是色情作品。
新方向出版社的詹姆斯·勞克林也拒絕了它。他說出版此書無論對於作者還是出版社來說,都是一種自我毀滅的行爲。法勒、斯特勞斯和揚出版社的羅傑·斯特勞斯斷定在美國出版此書肯定會引來一場打不贏的官司。
弗拉迪米爾跟朋友們討論了該書手稿。瑪麗·麥卡錫和她的丈夫鮑登·布羅德沃特都認爲"這可憐的傢夥顯然是發瘋了。"
"我認爲它是如此噁心,以致於它使我跟他疏遠了,"有個小女兒的埃德蒙·威爾遜說。另一對文學夫妻哈裏和埃琳娜覺得小說寫得很出色,極具挑逗性。他們也開始理解弗拉迪米爾早先爲何對他倆的小女兒有興趣,把她帶去刨根問底地盤問她。
在賈森·愛潑斯坦讀完小說,並代表道布林戴出版社拒絕它以後,維拉寫信給長期以來在法國代理納巴科夫作品的那位元足智多謀的俄國文學經紀人道西亞·厄加茲。"我丈夫寫完了一部非常獨特的小說,可由於刻板的道德約束,它不能在這兒出版。它【用英語】在歐洲出版的可能性有多大?"
厄加茲讀完《洛莉塔》之後非常喜歡它。她將它推薦給了奧林匹亞出版社的主人莫裏斯·吉羅狄亞,後者是《帶鞭子的天使》、《風塵婦自傳》等一系列其他經典書的出版商。吉羅狄亞立即喜歡上了《洛莉塔》。他的唯一先決條件就是要求弗拉迪米爾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假如出版商提出優厚的報酬,我將會考慮准許以我的名字出版此書,"作者讓步說。
1955年夏天,雙方同意爲此書預支40萬法郎或1,000美元,但無論作者還是出版商都不認爲小說具有任何商業價值。
在簽署協定以後,弗拉迪米爾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他在康奈爾大學的唯一密友,莫裏斯·畢曉普,後者向他妻子吐露說,"它有關一個喜愛小姑娘的男人……他說書中沒有一個髒字,而且它確實是一個悲劇性的可怕故事。我真不希望它會引出醜聞。"
畢曉普的告誡是納巴科夫夫婦倆都不願意聽到的。在康奈爾大學,"道德墮落"這一罪名足以使一個人被開除。莫裏斯·畢曉普發現維拉焦慮得要命。她丈夫56歲了,他怎麽還能找到另一個工作?
小說於秋天在巴黎出版以後,剛開始的反應很平靜。但格雷厄姆·格林在倫敦給納巴科夫夫婦贈送了一份耶誕節禮物:在《星期日泰晤士報》請他提出1955年的三部最佳書籍時,小說家的名單中包括了一部人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在美國和英國都買不到,但卻可以在巴黎買到的綠封皮兩卷本的書。它就是《洛莉塔》。
在被一家報紙提名爲1955年最佳書籍以後,《洛莉塔》卻在另一家報紙上被譴責爲最肮髒的書。《星期日快報》主編約翰·戈登稱它爲"肆無忌憚的色情作品……任何在這兒出版和銷售它的人都肯定會坐牢。"
當有關這一場爭執的消息傳到美國以後,維拉立即收到了大量出版商的詢問。她委婉地告訴印地安納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這部書不適合於他們。對於每一個對《洛莉塔》提出疑慮的朋友,都有一個出版商寫信來表示對此書有興趣。
最後,普特南出版社的沃爾特·明頓獲得了該書出版權,但只是在最奇特的情況下才得到的。明頓早就聽說了《洛莉塔》,但只是在遇見一位名叫羅斯瑪麗·裏奇威爾的酒吧舞女之後才讀到了它。裏奇威爾有一部這樣的小說,並且就像明頓所回憶的那樣,"有一天晚上她陪我坐在東67街她公寓裏的時候,我讀到了它。"
《時代周刊》登載了這位出色書探的一幅照片,並且把她描寫成"一位身上滑溜溜的前拉丁區舞女,脖子上套著一根金攪酒棒,臉上挂著興奮的笑容。"這以後的形勢變得更加怪誕。兩個星期之後,明頓的妻子在吃飯時告訴維拉,她只是在讀到《時代周刊》的文章以後才得知丈夫跟那個舞女有瓜葛。當天晚上,維拉從明頓本人那兒獲知他還跟《時代周刊》那篇文章的作者有瓜葛,後者竭盡全力把她的情敵描繪成醉醺醺的應召女郎。
幸運的是,維拉還未曾得知故事的另一半,這個故事的結尾是在巴黎一個女同性戀的夜總會裏,裏奇威爾用一個威士忌酒瓶痛擊明頓,而吉羅狄亞則在一旁作壁上觀。裏奇威爾對《洛莉塔》的發現也許爲她賺取了20,000美元,假如明頓的定金已經支付的的話。
當該書的出版臨近時,維拉和弗拉迪米爾知道他們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將改變。他們在洛基山脈度過了1958年夏天之後,回紐約參加了在哈佛俱樂部召開的,被維拉輪流稱之爲《洛莉塔》和弗拉迪米爾問世慶祝會的記者招待會。那兒態度友好的記者們承認自己沒想到作者會攜帶典雅出衆的妻子光臨。"是的,"維拉鎮定自若地含笑回答,"這是我出席記者招待會的主要理由。"她丈夫輕輕一笑,說他曾想爲這次聚會雇一位小姑娘作爲陪伴。
給作者照相固然重要,但尤其重要的是必須把維拉這個有血有肉--而且已人到中年--的女人納入鏡頭,她就站在那個喜歡小姑娘的男人後面。第二天,《紐約郵報》特意評論說維拉是"一位身材苗條,皮膚細膩的白髮女郎,與洛莉塔相距甚遠"。
維拉的存在證明了小說的虛構性質,使那些對《洛莉塔》的題材感到焦慮的讀者可以放心地認爲納巴科夫的變態性質不同。公衆尚未讀過在《洛莉塔》之前那些充滿其原型,但大多未經翻譯的作品,這無疑是一件幸事。
《洛莉塔》於8月18日出版的那天,其作者正如維拉所描述的那樣,顯得"平靜而又淡漠"。當天早上就售出了300本,到了下午三點左右,數目猛增到了1,000,當明頓發來祝賀的電報時,售書已達1,400本。第二天又售出了2,600本。到了九月初,已經有80,000本小說印刷並上市。
正如納巴科夫夫婦所極其敏感地意識到的那樣,這個數目恰好是弗拉迪米爾以前用俄語和英語出版的所有作品數目的總和。到了月底,該書就成了《紐約時報》暢銷書單上的頭號暢銷書。
小說拍電影的版權以15萬美元的價格轉讓給了斯坦利·庫布裏克和詹姆斯·哈裏斯的導演攝製組,這相當於弗拉迪米爾在康奈爾大學17年的薪水。納巴科夫夫婦都顯然爲自己成爲這筆鉅款的接受者而感到局促不安。對於康奈爾大學校園裏的許多人來說,就連《洛莉塔》封面上的5美元標價也是高得令人望而卻步。
記者們紛至遝來。當第一群吵吵嚷嚷的採訪者坐飛機離去以後,維拉開始注意到他們提問中的熟悉主題,"他們都希望找到某種駭人聽聞的內容。"
她對於《洛莉塔》接受情況的一個抱怨就像是《紐約郵報》一位評論家早先所指出的那樣:"洛莉塔被人攻擊成一個可怕的小孩子,一個淺薄、邪惡、淫蕩和極其令人討厭的頑童。"評論者往往傾向于憐憫亨伯特,而維拉卻專注於洛莉塔的脆弱性,強調她的孤單無助,在世上連一個親人都沒有。
"報紙從各種可能的角度討論了《洛莉塔》,但卻忽視了一點:即她的內在美和傷感力,"她在日記中寫道,"評論家們寧可去尋找倫理象徵、辯解理由、譴責理由,或對H·亨伯特進退兩難境地的解釋……然而我希望有人會注意到書中對於孩子的無助,她對惡魔般的H·亨伯特的可悲依賴性,以及她令人心碎的勇氣等充滿柔情的描寫……"
當小說在倫敦出版時,英國的每一個記者都想採訪弗拉迪米爾。他對其中的原因並不抱任何的幻想,並告訴一位元記者說,他知道他們在尋找那本能證明《洛莉塔》並非虛構的日記。
真相是納巴科夫夫婦共同造就了《洛莉塔》。他們來來往往都是相伴而行。他們不僅形影不離,而且說話也口徑統一,無論是印在書頁上,還是在當面接受採訪時。他們的筆迹也會出現在對方的筆記本中。他從筆記本的一端開始寫的話,她就會從另一端開始。
無論她丈夫做什麽,維拉都是一個富有創造性的搭檔。她需要在生活中做出一件大事。而且就像他從一開始就表明的那樣,弗拉迪米爾也非常需要她。他認爲他將會因兩本書而青史留名--這就是在維拉建議下他所翻譯的《葉甫蓋尼·奧涅金》,以及她所搶救出來的《洛莉塔》。
他晚年最看重的兩個專案是《洛莉塔》俄譯本和他的修訂版自傳《說吧,記憶》。維拉合譯了第一本書,並爲第二本書撰寫了文章。
納巴科夫夫婦的經歷被許多人看作是一個偉大的愛情故事。律師、出版商、親戚、同事與朋友們都一致認爲:"沒有她他將一事無成。"
來源:文學大講堂
上網日期 2002年03月18日
資料來源︰http://www.csdn618.com.cn/century/wencui/020318200/020318202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