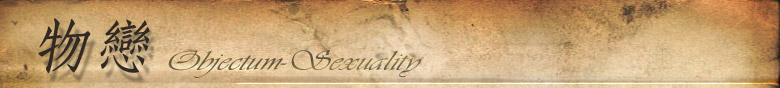物戀〈維基百科〉 我愛故我在?!
十七世紀,笛卡兒(René Descartes)說了句名言: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表達理性之於人類思考與存在之重要;十八世紀,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說了「我感受故我在」 (I feel, therefore I am.),用感受置換理智,重新思考人類「存在」的可能;那麼,在倡導女性權益、種族平等、同性戀解放等運動蓬勃,如此著重多元化的二十一世紀社會,藩籬一個個被打破,禁錮一個個鬆脫,那麼「愛」呢?我們對「愛」的觀念是否也須解放?「我愛故我在(I love therefore I am.)」的存在可能,是不是同樣也可以是讓世界更豐富多元、更自由的選擇之一?
|
「自由」、「平等」、「博愛」 是的,我愛上了艾菲爾鐵塔!
英國BBC電台在2008年拍攝「與艾菲爾鐵塔結婚」 (Married to the Eiffel Tower) 一紀錄短片,片中兩名主角──與法國艾菲爾鐵塔結婚的美國女子Erika Naisho Eiffel,以及與德國柏林圍牆結婚的瑞士女子Eija-Riitta Berliner Mauer──是物戀界的兩名先驅者,也是頭兩位出櫃的物戀者。BBC的紀錄短片一問世便引起廣大討論聲浪,影片的拍攝手法卻也引起「物戀國際官方網站」(Objectum-Sexuality Internationale)的不滿,公開譴責該片不當利用物戀者,譁眾取寵,傳達錯誤印象。事實上,BBC的影片一方面大大打開了物戀的知名度,使物戀者有更大的舞台向世界發聲;另一方面,也在呈現初始同時開啟主流價值觀與物戀價值觀的衝突,社會上質疑物戀者心裡問題的聲音從未間斷。
回頭一看,類似的情況在歷史上實不少見,從古代被譏為瘋子言論的地圓說、從近代同性戀出櫃後的奮鬥歷程、甚至是近期台灣性工作從非法到合法的辛苦進程。因著不理解、驚恐形成的排斥、排擠與打壓,因為缺乏理解導致的藩籬、鴻溝、排擠隨處可見;但人類同時也因著願意理解的心理,打破一個個藩籬,一次次溝通。所以現在,我們知道地球是圓,外面還有整個宇宙;所以台灣終於在2009年6月宣布公娼合法化;所以現在同性戀者得以參政、結婚、養子、發揮長才,像目前國際時裝大牌的一線設計大師多為公開的同性戀者,就是一例。物戀,作為一種新興議題,正逐步展開一條艱難漫長的爭取「自由」、「平等」、及理解其「博愛」的道路。她們不躲在角落,選擇勇敢出櫃,是要發聲!而發聲,是為了建立「理解」這個橋樑,是為了出櫃的以及未出櫃的物戀者,甚至更多被邊緣化、消音化的性少數,是為了爭取身為社會一份子所應被賦予的「自由」、「平等」與「尊重」。
此「物戀」,非彼「戀物」─懷疑論者:子非物,安知物之感?
物戀者:子非我,安知我不知物之感?
物戀(Objectum-Sexuality)取自拉丁文,由物戀者Eija-Riitta Berliner Mauer首先提出,也稱為Objectophilia,縮寫為OS,意指愛上物體(objects)的情感狀態。物戀和戀物癖(fetishism) 相異的是,戀物者(fetishists)並不將物體當成生命體或戀人看待,和物體的互動多為獲取性刺激及性滿足;對物戀者來說,物體是具有靈魂及自然精神的(Animism),因受到某一物體的吸引自然而然進而愛上對方,在與伴侶(物體)的交流,甚至親密關係中,她/他們更在乎對方的感受與彼此的互動,而非僅止於自我單方面的滿足或性需求。
物戀者表明自己在童年或是青春期就開始意識到本身有物戀傾向,不過物戀有時不走一對一的戀愛關係,她/他們可能同時愛上幾個不同的對象,(當然也可能移情別戀)。不過物體不會彼此打架,所以不會造成人人戀中劈腿被抓包的傷亡慘況,這也算是物戀特有的優點之一吧。物戀對象可能是遠方知名的地標,也可能是生活中長相伴隨的物件,如柏林圍牆、籬笆、蒸氣火車頭等,依對象的遠近順勢發展成遠距離戀愛或近距離戀愛模式;遠距離物戀者習慣將愛物的照片、模型放在身邊;近距離戀愛就幸運的多,可以和所愛長相左右。目前比較麻煩的是,如果物戀者想要與所愛對象結婚,只能像 Erika Naisho Eiffel或Eija-Riitta Eklöf Berliner-Mauer一樣,只能在親友的見證下舉辦私人婚禮。因在法理上婚姻關係需奠基於雙方同意的狀況下使得生效,而物體無法回應,也因此物戀婚姻目前仍不具法律效力。
根據2009年物戀國際官網的統計數字,目前出櫃的40多名物戀者中以女性居多,但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男性站出來承認自己的物戀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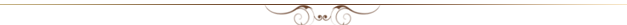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