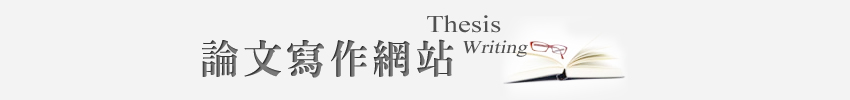
為何我們無力批判?
「批判閱讀」是一種主動的閱讀,是一種不斷檢視閱讀材料和讀者本身既有認知的閱讀。由於東方的教育模式往往講求強記背誦、墨守成規、服膺於閱讀材料和教師的權威,因此並不鼓勵讀者對閱讀材料保持距離,更不會激賞讀者對閱讀材料的質疑。以下的文章展示了其他文化的教育模式,他山之石應該可以刺激我們思考,反省我們所受的閱讀教育。
人家是在培養能力,而我們是在灌輸知識
我兒子正在讀高二,考了一道歷史題:「成吉思汗的繼承人窩闊臺,公元哪一年死?最遠打到哪?」第二問兒子答不出來,我幫他查找資料,所以到現在我都記得,是打到現在的匈牙利附近。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美國世界史這道題目不是這樣考的。它的題目是這樣的:「成吉思汗的繼承人窩闊臺,當初如果沒有死,歐洲會發生什麼變化?試從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面分析。」 有個學生是這樣回答的:「這位蒙古領導人如果當初沒有死,那麼可怕的黑死病就不會被帶到歐洲去,後來才知道那個東西是老鼠身上的跳蚤引起的鼠疫。但是六百多年前,黑死病在歐洲猖獗的時候,誰曉得這個叫做鼠疫。如果沒有黑死病,神父跟修女就不會死亡。神父跟修女如果沒有死亡,就不會懷疑上帝的存在。如果沒有懷疑上帝的存在,就不會有意大利弗羅倫斯的文藝復興。如果沒有文藝復興,西班牙、南歐就不會強大,西班牙無敵艦隊就不可能建立。如果西班牙、意大利不夠強大,盎格魯─撒克遜會提早200年強大,日耳曼會控制歐洲,奧匈帝國就不可能存在。」
教師一看,說:「棒,分析得好。 」但他們沒有分數,只有等級, A! 其實這種題目老師是沒有標準答案的,可是大家都要思考。
不久前,我去了趟日本,日本總是同我們在歷史問題上產生糾葛,所以我在日本很注意高中生的教科書。他們的教師給高中生布置了這樣一道題:「日本跟中國 100 年打一次仗,19世紀打了日清戰爭(我們叫甲午戰爭), 20世紀打了一場日中戰爭(我們叫做抗日戰爭), 21世紀如果日本跟中國開火,你認為大概是什麼時候?可能的遠因和近因在哪?如果日本贏了,是贏在什麼地方?輸了是輸在什麼條件上?分析之。」
其中有個高中生是這樣分析的:「我們跟中國很可能在臺灣回到中國以後,有一場激戰。臺灣如果回到中國,中國會把基隆與高雄封鎖,臺灣海峽就會變成中國的內海,我們的油輪就統統走右邊,走基隆和高雄的右邊。這樣,會增加日本的運油成本。我們的石油從波斯灣出來跨過印度洋,穿過馬六甲海峽,上中國南海,跨臺灣海峽進東海,到日本海,這是石油生命線。中國政府如果把臺灣海峽封鎖起來,我們的貨輪一定要從那邊過,我們的主力艦和驅逐艦就會出動,中國海軍一看到日本出兵,馬上就會上場,那就打!按照判斷,公元2015 年至2020年之間,這場戰爭可能爆發。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做對華抗戰的準備。」我看其他學生的判斷,也都是中國跟日本的磨擦,會從東海開始,從臺灣海峽開始,時間判斷是2015年至 2020年之間。
這種題目和答案都太可怕了。撇開政治因素來看這道題,我們的歷史教育就很有問題。翻開我們的教科書,題目是這樣出的:「甲午戰爭是哪一年爆發的?簽訂的叫什麼條約?割讓多少土地?賠償多少銀兩?」每個學生都努力做答案。結果我們一天到晚研究什麼時候割讓遼東半島,什麼時候丟了臺灣、澎湖、賠償二萬銀兩?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背得滾瓜爛熟,都是一大堆枯燥無味的數字。那又怎麼樣?反正都賠了嘛!銀兩都給了嘛!最主要的是將來可能會怎樣!
人家是在培養能力,而我們是在灌輸知識。天啊!不能完全責怪孩子,應該反省的是我們大人。
原文由家長chihjen0323刊登於http://tw.club.yahoo.com/clubs/TSHO/
中華民國學生反髮禁自治協會
法國高中就考思辨〈原標題:人能否不要國家?〉
中國時報 2007.07.08
蔡筱穎/巴黎
同樣是聯考的季節,在台灣的大學聯考以及在法國的高中畢業會考都是媒體報導的焦點,不同的是,基於兩百多年的會考傳統,法國是以哲學科目的考試展開,而且年年的哲學題目都會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和討論,媒體更是請哲學家或是作家就此題目作答,並在平面媒體上大篇幅刊載,或是在廣電頻道中作長時段討論。
哲學考試是法國高中畢業會考的一大傳統特色,不同於歐洲其他國家僅是聊備一格的哲學史介紹,法國是歐洲唯一在高中教授哲學課程的國家,選擇文科的學生每周要上七小時的哲學課,而經濟社會科和理科的學生也分別要上四小時和三小時的哲學課,教育部強調哲學課程的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並建立理性分析座標以領悟時代的意義」。
法蘭西院士應考「無法改」
也就是因為這個法國文化的特殊性,所以每年會考時,哲學科是必考科目的第一科,在四小時內寫一篇二、三千字長文,今年的五十萬名學生每人都須在三個考題中,就其中兩個問答題選一題作答,另一題則為一篇哲學相關文章的閱讀心得評論,不同科別的哲學考題難度略有不同,占總分的比重也不一致。
考題公布後,馬上成為新聞媒體報導評論的重心,如費加洛報就邀請作家參加哲學考試,貪玩的法蘭西學院院士德奧梅嵩寫了四小時後出場說「我不敢保證有六十分」,費加洛報刊登了他的應答考卷,結果不像其他作家有分數,閱卷老師的評語是「無法改的」。
眾多平面媒體都以多頁篇幅刊登哲學家或作家的解題論述,廣電媒體則以三到四個小時針對哲學考題請哲學家講解辯證概念。
今年的試題反映了政治現實,例如經濟社會科的試題「工作能夠讓我們贏得什麼?」回應了此次總統大選中有關工作價值的辯論,理科的試題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對比有什麼意義?」或者「欲望能夠從現實當中得到滿足嗎?」技術類舞蹈音樂與技巧專業科則有「人能否不要國家?」
一如往年的題目,較少針對心理學和形上學出題,而是涉及高中哲學課程討論的主體、文化、理性與現實、政治、道德等大綱,如「能否將自由視為一種拒絕的權力?」「什麼是公眾輿論能承受的真理?」「藝術是一種語言嗎?」「不服從法律是否可算是理性行為?」「是否一切問題都應依靠國家來解決?」以及歷史的「如果是你,會往廣島長崎扔原子彈嗎?」等考題,在左右派對社會福利和自由經濟路線的辯論越來越激烈時,自二○○二年起強調「自由」和「國家」的概念也多成為考試的主題。
歷年考題屢見科學反思
對科學的反思也常被提出,如「我們對現實的認識是否受科學知識的局限?」「經驗可否表明什麼?」在生活上「我們是否有可能成為某種科技產品的奴隸?」「經濟學家是否應當寧要幸福而放棄真理?」等都是目前每年的出題範圍。而穆勒有關《信任乃社會之基石》的文本解釋,以及洛克關於《私有財產》的文本,都在近幾年隨著題目的政治色彩增加被強調出來。
由於哲學的訓練是要讓學生負起個人以及公民的責任,以哲學分析顯示演繹推理的理性力量,及在日常生活中的相應推論。所以,改卷的教師都傾向在哲學的作答中瞭解學生的邏輯性,對題目的分析和比較、有質疑文本思考,以及就此文本發展辯證思考的能力,因此擺脫陳腔濫調以及背誦哲學史的束縛,以理性思考解釋批判成為必要。
薩科奇也只拿了九分
不過,最著名的例子是有一年的考題中,有一題僅有「風險」兩個字,一位學生冒著極大的風險,僅以四個字回答:「就像這樣!」卻得到了高分。
哲學考試的傳統對法國人而言是一種「文明賭注」的驕傲,就像密特朗總統晚年和友人談到他的私生女瑪薩琳時,會以她高中會考的哲學分數是十六分,非常驕傲「從來沒有見過這麼高的哲學分數」!不過,新上任的法國總統薩科奇的哲學考試在二十分中僅得到九分的事實,也讓學者正視到學生面對抽象問題的焦急,菁英式的哲學課程教學理念是否要改革,或是如頑石般的抵抗現實,則是每年哲學考試後,教育界自己的考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