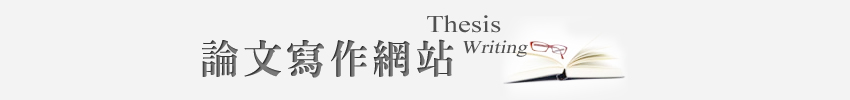
不註明出處就算抄襲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什麼時候,我們寫文章,必須不斷地給自己喜歡的東西、自己認同的東西,加一個注?那是晚清才開始的。”
不久前,我們一個學生,受老師批評,說他的碩士論文跟我以前的一篇論文比較接近。那個學生辯解說,因為這段話我特別喜歡,而且我也很認同,已經內化為我自己的感覺了,寫作時自然而然就出來了。老師非常憤怒,說這是 “學術不端”,雖還沒到 “抄襲” 的地步,但也很嚴重。
按照現行規定,這學生確實不對,可在古代中國,這很正常。確實是這麼回事。古代中國,讀到喜歡的東西,不妨用自己的語言再表述一遍,甚至直接抄下來。
什麼時候,我們寫文章,必須不斷地給自己喜歡的東西、自己認同的東西,加一個注?那是晚清才開始的。所以,我談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做引文,或者說引文的出現,與整個學術表達的關系。
閱讀 20 世紀前後的著作,最直接的感受,很可能就是引語的內容變了,引語的方式也變了。仔細分析,你對別人的言論是怎麼處理的,怎樣引錄、如何銜接、能否駕馭,諸如此類,都關系重大。
我談一個掌故,大家馬上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幾十年後,馮友蘭回憶他早年在北京大學念書的時候,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剛出版。馮先生說讀這書,有一種震撼,為什麼?你以為是像蔡元培說的,簡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不是的。
馮先生說,最讓他震撼的,是以前我們寫文章都是孔子說什麼,然後一個箋,一個證,再加一個按。而且,為了體現孔子的話最重要,前人的箋證次之,最後才是我個人的小小意見,字體越來越小。胡適整個把它倒過來,最關鍵的,是我個人的想法,下面的證明文字,包括孔子的話,都是用來證實我的見解的。因此,我是大字,孔子是小字。
他說,這一下子把他們給震住了。在他看來,這體現了五四時代以個人為中心、以我為主的思想觀念。我們都知道,上下文之間,舊學新知之間,其實不只是互相論述,這其中的停頓、過渡,隱含了權力,隱含了慾望,也隱含了美感。
當然,我必須做一個小小的補正,馮先生的回憶不太準確。前面說的沒錯,以我為主,孔子的話,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可以自由引用;但字體其實是一樣的,沒有說真的把孔子給變小了。以前孔子字大,我們字小,五四時期改變了,都平等了,大概是當年這沖擊實在太大了,以至幾十年後追憶,就成了我字大、孔子字小。
晚清中國,面對 “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讀書人發現,知識紛至沓來,文本斑駁陸離,如何在自己的論述裡,恰如其分地安置他人的言語,這個工作,遠比明清時要困難得多。
為什麼這麼說?凡是做學問,都得引,不是現在才有的,以前也引。所以,“引經據典” 在傳統中國,在古漢語裡,是一個很重要的修辭方式。
今天我們看元代陳繹曾的《文說》,或者是明代高琦的《文章一貫》,他們提到各種各樣的引。但是這個 “引”,主要是引事、引典,而不是直接引語。所以,今天的引用,和過去的是不太一樣的。過去的引,主要是 “事”;現在的引,主要是 “言”。下面我主要討論這個問題。
引言分為幾種,一種是明引,註明出處;另一種,不註明出處,我們叫暗引;還有,屬於正面表彰的,我們說是正引;反面批駁的,則為反引;再有,完整的引用,是全引;轉述大意的, 我稱為略引。現在,我就把這三組六類的引用略為鋪排,看看現代中國學者是怎麼寫論文的。
先說明引和暗引。傳統中國讀書人,也在思考,也講知識的傳遞和創新,但並不刻意追求。所以,“含英咀華”“述而不作”,在傳統中國,是一種美德。那是因為,古人存在著虛擬的共同信仰,似乎讀書人要做的,就是准確表述往世先賢的思想觀念,並用來解決當下的困惑,這樣就行了,沒必要再推出自己的什麼奇談怪論。知識以及真理,都已經有了,我們的任務,是怎麼樣更好地去理解、融會貫通,並落實在實際行動中。
你會發現,傳統的中國文人,包括很多勤奮的學者,會用筆記的形式,“博采眾長”,把前人各種各樣的佳言妙語,全部抄在自己的書裡面。宋人洪邁,就是這樣撰寫《容齋隨筆》的。
其實,宋元以降筆記,經常互相抄,而且不註明出處。可無論當世,還是後代,一般都不會被斥為 “抄襲”。文論裡確實有一句話,叫 “忌剽竊”,可是請大家注意,“忌剽竊” 指的是詩和文;為了一句好詩的 “著作權”,甚至可以去殺人。反而是學術著作,包括考證性質的筆記,可以互相傳示,互相轉用,互相抄襲。
到了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裡,才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說了這麼一句話:“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 希望以後我們引別人的話時,註明出處, 且不要胡亂竄改。
後來,章學誠做了一個補充,這個補充很重要。他說,著作之體,引用古書,襲用成文,不標出處沒問題;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須標明出處。也就是說,說明道理,可以隨便引;但若鉤稽事實,那是不一樣的,誰最先考出來,你必須說清楚。這個區分,他後來加了補充說明,說為了省去大家的麻煩,希望自注出處。
為什麼這麼說?傳統中國人為了文章漂亮,不喜歡注出處。
大家假想,你我都是讀書人,我用的典故,你若不知道,那你就不配讀我的文章。所以,大家看到那些不知道的典故,除非是小人物,你敢去懷疑,如果覺得對方有來頭,不敢隨便追問他 “典出何處”。因為,看不懂,那是你的問題。
舉個例子,宋代的幾部筆記如《石林燕語》《老學庵筆記》《誠齋詩話》等,都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梅堯臣做考官的時候,蘇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 卷子裡有這麼幾句話: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
這個說法,考官不知典出何處。梅堯臣跑去問歐陽修,也都不知道。等到揭榜了,問蘇東坡,請問您那個典到底是從何而來的?蘇東坡說:想當然爾,何必要有出處?
這是文人逸事,很好玩。一般情況下,不好隨便追問人家出處在哪兒,顯得自己特沒學問。你我都應該知道的,不知道,那是你的問題。所以,我不注。只是到了清代後期,才強調寫文章要註明出處。這個事情,到了章太炎、梁啟超和夏曾佑,也就是 1900 年以後,才比較正規起來。
即使這樣,中學和西學的書,加注的狀態不一樣。中學的著作,比如談論中國文學、中國哲學的,大體上,1901 年以後就逐漸這麼做了;西學的則沒有。
一個日本學者曾撰文,指責梁啟超 “抄襲”,因為他的文章裡面,有好多是日本人的說法。我承認梁啟超確實大大得益於日本人的著作,但我否定這就是 “抄襲”。因為,如果嚴格追究,晚清介紹西學的,絕大部分都有類似的問題。照這麼說,魯迅也是 “抄襲”,因為《摩羅詩力說》中的很多說法,都是有來源的。
早年介紹西學的,都是把當時讀到的著作轉譯,摘抄,或者重新組織起來。當然,到了 1980 年代以後,就不該再這樣了。今天做西學的,再這樣隨便抄人家的,或者以譯代著,在學界會受到嚴厲批評。
第二個我想談的是正引和反引。正面的引述和反面的引述, 效果有天壤之別,這點,不用多加論證。我只想提醒,引什麼?
不難發現,國學中的經典,在不同的時期,容易上下其手;至於西學,則始終被我們作為正面引述的對象。我們的學生寫論文, 引經據典,什麼哈貝馬斯、德裡達,多得很;再接下來引什麼?
古的到王國維、魯迅,今的則海外漢學家,包括鄭培凱先生的著作,張隆溪的我們也引。在座的,如果是大陸出來的,大概都會同意我的觀察:國人寫論文,不大引同輩學者的,更不引下一輩的研究成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表面上我們也有很多引文, 但要麼是老人,要麼是死去的,要麼就是遠在天邊。
最後一個問題,關於全引和略引。到底採用全引還是略引, 古人很有講究。宋人《論作文法》有雲:“經據不全兩,史據不全三。” 寫文章的時候,引經別超過兩句,引史不要超過三句。因為引文太多,文章會變得支離破碎。
這跟我們現在整段整段地引,效果很不一樣。整段整段引,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同一篇文章,糅合了三種不同文體,第一種白話,第二種文言,第三種歐化語 —— 自己翻譯的或者別人翻譯的。
你會發現,這樣的文章,讀起來很別扭,或者基本上沒法讀,只能看。這個時候,你就能理解古人為什麼對略引感興趣。這可能是不太尊重前人的 “知識產權”,另一方面也有文章美感方面的考慮。
如何既表達對前輩的敬意,同時完成自身學術建構,還保持文章的完整性,這不容易。這裡只是提出問題,沒有具體的答案。
(作者:陳平原)--文章來源:https://mp.weixin.qq.com/s/shdhsdOBBcIj4z43j8u_Vw